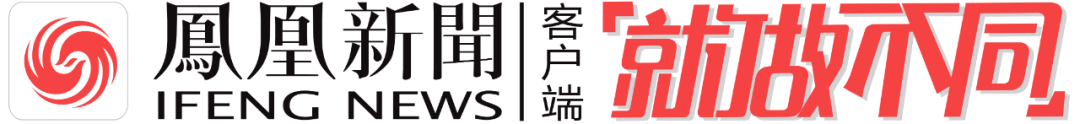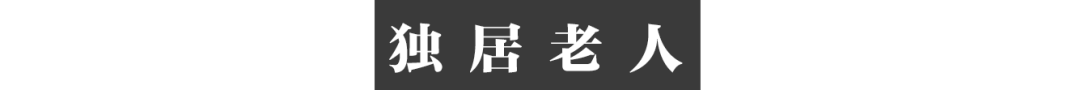10月23日,河南鹤壁市浚县北苏村的洪水已经退去。
卫河的水位下降了几米,铁路桥高高的桥墩露了出来。农用三轮车、汽车、以及运建筑材料的卡车,在跨河的单行道桥边排起长龙。村道边晾晒着澄黄的玉米棒和红色的小麦种子。有些人家的门外堆放着被水泡坏的家什。老太太们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看着孩子玩耍。连日的阳光晒着房子潮湿的外墙,水位线已经难以分辨。大门敞开的院子里堆着玉米,晾衣绳上挂满被褥和衣服。
村道边的几个建房工地上,砖头和泥土堆放在四周,却都没有人干活。一位看守建材的老人说,现在正农忙,建房的人家多,干活的人忙不过来了。
这里的生活看起来已经重回正轨。
我站在浚县北苏村的农田边,目之所及是已经完成翻耕,并被整理出整齐条纹的田野。两个月前,这里还是半截浸在水里的的郁郁葱葱的玉米地。如今,松软潮湿的泥土中埋着的小麦种,引来成群的喜鹊和麻雀觅食。
远处,几个人在田里反复弯腰、蹲下、又站起身。拉机拖着犁往返穿梭,掉头起步的时候发出哒哒的吼叫,喷出几朵浓烟。更远处,连接南北的铁路动脉上,货运列车和动车频繁地驶过,发出不同节律的鸣响。
那几个人正是郭国勤一家。郭国勤和妻子、母亲,正赶在拖拉机翻地之前收“落生(花生)”。我朝他招手,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你又来了,有两个月没见了吧!”
郭国勤50岁出头,穿着一件西装外套,戴一副白手套,足蹬运动鞋,小跑着推着一辆红色手推车,在一块花生田里撒球形颗粒的白色化肥。“看看,这是最好的大蒜专用肥!”他自豪地向我介绍撒化肥的专用推车、大蒜播种机,展示出他的专业和投入。我问他之前大堤上的那些蒜是怎么卖的。“没办法,两块钱卖了。本来想等等卖两块五——往年能到那价——可今年收蒜的时候水淹了路,大车不愿意来”,他皱起眉说,“7万多斤蒜,每斤少卖五角,少赚3万多元”。
8月初,我第一次见郭国勤时,洪水正浸泡着卫河沿岸的大片农村,他和妻子王社英在村里地势最高的堤上,日夜守护他们的大蒜。“小坡滩”蓄滞洪区启用的消息是7月30日公布的。郭国勤得知后,马上找人用农用三轮车把大蒜从家里转移到隔壁内黄县的一间库房里。7月31日,水从西南方向涌进村子,他见水位涨势迅猛,又再次雇人把大蒜转移到村北边的堤上——这是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堤上曾有一条已废弃的汤濮线窄轨铁路。当时村民大多已经撤离,他打了很多电话才找到人帮忙,两次搬蒜花掉近两千块钱。
堤上地势高,但拦不住下雨。为了让大蒜保持通风,同时下雨时能及时苫盖大蒜,夫妻俩和从广东专程赶回来的儿子日夜守在堤上。白天他们坐在在村里发的一座折叠凉亭下面,晚上被蚊子狂轰滥炸。王社英的脸上被叮了几十个包,每天都只能睡半宿觉,常坐着看太阳升起。
十几天后水位下降,村里的路能走了,王社英和儿子晚上回家住,郭国勤则坚持在堤坝上住了一个半月,直到把蒜卖掉。
尽管一家人竭尽全力,经过一个多月雨淋和地面返潮,仍有四五千斤大蒜变质了,损失一万元左右。而秋收的四十亩玉米和花生几乎失去了经济价值。
河南农民一般一年种两季庄稼,夏收冬小麦,秋收玉米。郭国勤的蒜是6月收的,随后种下玉米和花生。他剥开刚收的花生给我看,皱巴巴的果仁有些发黄。他说不清被污浊的洪水浸泡过的花生仁有没有被细菌污染。他把剥出的两粒果仁投进嘴里尝了尝,眨着眼睛表示似乎没有异常。
他说等他把40亩地的蒜播种完,然后浇水、打药、覆地膜,把蒜芽从地膜里勾出来,就快到冬至了,今年晚了一个节气。他担心播种时间推迟,洪水后土壤里的细菌和虫害都会影响产量。此外,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和电力短缺,化肥大幅涨价,去年120元一袋的化肥今年涨到165元,柴油从四、五元涨到七元多。往年种蒜成本一亩地3000元,今年会大幅度增加。“今年不赔不赚,估计明年夏收可能减产、赔钱。”
我问他怕不怕明年夏天再来洪水。“怎么不怕?现在极端天气太多了”,他说。
“明知会赔钱怎么还种?”我问。“老农民,不种地还能干什么?出去打工?疫情来了,活干不了,家也回不了,到处都要开支”,他苦笑着说。他现在努力赚钱的目标是给儿子买房娶媳妇。他的儿子已经20岁,水退后没有回广东的电子厂,而是去城里一家饭馆当起了厨师。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是时。霜降搁了误,立冬不出土。”
东苏村蒋进勇家的地和郭国勤包的地相邻。蒋进勇一边对我说这句农谚,一边和儿子在田垅上挖灌溉沟。虽然他已经赶在霜降前把麦子种完了,但是他估计发芽率没有往年高。
卫河沿岸的蓄滞洪区8月被淹,8月9月连降大雨,中元节前后,村民接到第二次紧急撤离通知。10月初到了寒露,土地还很泥泞,拖拉机无法下地翻耕。又过了一个多星期,村东边的土地终于干透,农民们才赶忙把麦子种了。村西边的农田因为地势低洼仍在水里泡着。蒋进勇认识几家人,今年秋收没有收入,现在地湿没法下种,无奈之下已经出外打工。
蒋进勇家包的十几亩地也是颗粒无收,农用工具、农用车、家具电器和房屋共计损失数万元。他盼着早点拿到补偿款。也许只有辛劳付出换来的不是一场空,这场灾难在他们的心里才能画上句号。
北苏村以南50公里的小河镇,地处共产主义渠和卫河之间,淹水时间比北苏村约早一周,土地比北苏村干得晚一些。10月23日,薄雾中望不到边的农田里留着收割后的庄稼秆或倒伏枯干的庄稼。共渠边的农田里还有小片积水。
正值农忙之际,田野却寂静无声,见不到劳作的农民。
在小河镇聂渡村,两位老人在地里干活,男的弯着腰拔草,女的用叉子把庄稼杆铲到路边。
“还有半个月就立冬了,往年这时麦子都已经忽扇扇的了,这会儿地还没犁呢!明年一亩收五六百斤就不赖了,收入至少减少50%”,71岁的和先生说。他和妻子陈女士有两个出嫁的女儿,家里没有男劳力,和先生得过脑血栓腿脚不便,种地的担子落在年近70的陈女士一人的肩上。
“要是能烧秸秆就好了,燎燎好晒地咧!”71岁的和先生望着地面上厚厚一层洪水留下的枯草,又看了看老伴一个人铲草的身影叹道。被洪水泡烂又被晒干的庄稼形成一层既遮光又不通风的覆盖层,像草席一样盖着土地。踩上去可以感觉到土地的湿软。
“谁烧罚谁,谁烧抓谁”——当地已经执行禁烧秸秆法令五六年,很多地方挂着禁烧秸秆的标语。在越来越多的极端气象灾害中,“靠天吃饭”的农民承担着气候变化最直接的恶果。
“地还要等几天才能犁”,在袁庄村的一块田边带着孙女采野韭菜的宋女士说,“因为土地湿寒,产量不会高。以前最高打到1500斤麦,现在能到1000斤就是好的”。她的预估比和先生乐观一些。宋女士家的9亩3分地的秋季玉米颗粒无收。“都烂完了,没用了”。玉米在当地一亩最低打1500斤,收购价格约1块钱1斤,她的秋季损失约有1万3千元左右。
她家的房子开始评了C级,水落后墙壁裂缝加大,村里给改成了D。C级需要大修,D级是危房,必须拆除重建。问到补偿款,她说看到过一份文件,确定12月补偿款可以发到手。虽然经受了损失,但她的心情不错。“现在国家政策好,不会亏待农民”,她说。
告别时她告诉我:“你去袁庄村看吧,那可热闹了,是我们这重点打造的样板村。”
袁庄村主干道两边的房屋外墙都被刷成了白色。带着头盔、身着工作服的工人站在脚手架上,往二、三层楼的水泥外墙刷白漆。临街的白墙下立着几块牌子,上面贴着看似奢华别墅的图片,村民告诉我那是将要重建的村民房屋的效果图。
在村子中央的一个狭长的水坑旁,一辆黄色的柴油泵车正用两条直径三十厘米的水管,把坑里的积水排向村外的沟渠。开车的师傅告诉我,水泵车已经在这里昼夜不停地抽水两个多月了。水坑深度约有三四米,是附近地势最低的位置,农田的积水下渗后不断汇集到这里。
袁庄村里的很多房子已经被拆除,其数量远远多于北苏村。在几处拆除现场,夹着金属线的水泥块和砖头被轰鸣的挖掘机装上卡车运走。村路中央,新安装的下水管道上覆盖着木板。
我在袁庄村没有看到村民自建的工地。在村委会门外贴着一张日程表:拆房、建房发放补偿,各有其时。复建房屋的日子统一定在11月5日。
水灾过后,工程鉴定人员将房屋受损程度分为ABCD四级。被评为D级的房子必须拆除重建,C级在维修前不能入住。
65岁的董女士站在一片废墟旁,看着工人拆自家的房子。她的房子是20多年前盖的一座二层楼。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村民建房普遍没有垫高地基。洪水中村里一些近年新建的房子,地基垫高了一米多都没有进水,而她的房子淹水一米多深。
“D级房子都得拆,不拆没法住”,董女士说,“可我们本来是楼房,没打算盖新房,孩子们都不在家,就我们俩人” 。眼下河南农村地区新建一座房子需要20-30万。补偿有多少?什么时候建?自己承担多少?董女士都还不知道。我问她村子里摆着的别墅效果图是不是新建房的样子,“打算是那样盖,谁也不知道。老百姓盖不起,盖点平常的就行了”,董女士说。
9月6日,河南省水利、财政、应急管理厅发布“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方案”,对蓄滞洪区水毁住房主体部分给予70%的补偿,发放时间定在12月15日前。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农民复建住房时要自行垫付。即便有补偿,自付部分对于家底薄的村民,特别是没有收入的老年人仍难以承担。
北苏村村民魏子良71岁,妻子李东云69岁,他们为了给二儿子重建房借了20多万元。他家被水泡坏的房子被评为D级,需拆除。在外打工的二儿子拿不出钱盖房,只能举债。“20多万全是跟亲戚借的。有的人拆都不敢拆,因为盖不起”,李东云说。
两人靠两个儿子供养,每人每月享受国家发放的110元养老金。对于补偿款什么时候能到手、数额是多少,他们还不清楚。
我问他们,既然儿子在外打工,为什么不等政府统一建房,而是自己筹钱盖房。他们说对外包的施工队不放心,自己建房用料和施工比较可靠。当地很多村民都在城市里盖过楼房,是专业的建筑工人。而且,统一建房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他们不想一直等着。魏子良说,对于自建房,将来鉴定人员还会进行安全检测,通过后才能发放补偿款。这一点让他感到有点不踏实,担心检测时出什么纰漏,影响放款。
和袁庄村一样,北苏村里也有几个大坑。
洪水退后,坑中央的约5米高的戏台被坑里淤滞的积水淹没,只露出一个红色顶棚。积水也淹没了坑边几户人家的地基和墙体。袁庄村水坑里积水经过两个多月持续抽排已经见底,而北苏村既没有水泵车也没有挖掘机。大坑距离卫河边几公里,积水量很大,村民自用小型油泵排水功率不够,油料也消耗不起,退水只能靠下渗和蒸发。但不利条件是水灾后地层已经蓄水饱和,入冬后水面冻结排水更难。
因被积水长期浸泡,坑旁的房屋出现地基沉降,魏子良家倒塌的房子是其中受损最严重的一个。魏子良的邻居魏联富的家在戏台后面,他的房子有一半坐落在坑坡上,屋子的地面下陷了30厘米左右,墙壁上横向裂缝贯穿西墙和北墙,被评为C。因为受损程度严重,他对评级感到不满,反复向村干部和房屋鉴定人员要求重新鉴定。但鉴定人员坚持评级没有问题。
魏联富家的旁边的大坑已持续积水三个月,不排水无法修房子,不修房子又不能住人。魏联富已经在亲戚家住了两个多月。
魏联富夏收入仓的两万多斤小麦被水淹毁,包的二十多亩玉米地往年可收3万斤玉米,今年只收了约6千斤。因为地湿,机器下不了地,6千多斤玉米是魏联富一袋袋用肩膀扛出来的。妻子李秀兰掀开一堆麦子的塑料布,腐烂成酱色的小麦堆里飘出一股酸败味。她说腐烂小麦没处弃置,放在家里邻居被熏得有意见。
魏联富想出去打工,但是他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的疫情。“别想那么多了,咱老农民就是能够咱吃喝就行了!打工现在有疫情,到哪儿也不行,都要停不让干”,魏联富说。
魏联富的邻居孔晓雪家也是C级。破碎的地板砖悬在地基上,几个衣柜倾斜。从墙角处的裂缝可以看到地基下沉约四五十厘米。她还没有维修房子,因为担心维修房子有不同标准,她想拿到补偿款以后再量入为出地修房子。鉴定人员测量了几次,还未确定什么时候补偿。
和北苏村比较,袁庄村同样评为C级的房子维修更及时。刘女士家的C级房子开裂的地方,已经由官方的施工队修好。
北苏村李鹏辉的新房里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化妆台。一组刚刚拍摄的婚纱照还没来得及挂到墙上。窗口边的化妆台上摆满喜糖和红包封。“家具是前天刚买的”,李鹏辉说。
水灾前牛素红花了两万多元装修了房子,购置了满屋新家具电器,为儿子结婚做好了准备。没想到婚期没到,洪水来了。婚礼原定在10月2号举行,但洪水退后家里一片狼藉。“原来的家具全都得换,现在这些家具、大门都是新换的”,李鹏辉说。“全都淹了,东西全都扔完了。”牛素红说着哭起来“主要是这心里真是难受,农民这一辈子就这一点儿积蓄,你说让我以后咋生活?”9月,家里的墙壁仍很潮湿,牛素红不得不第二次装修了房子。刷墙,换门,购置新家具新被褥,一切收拾停当后,两家人把婚期定在了11月3日。
牛素红家的房屋裂了大缝,在第一次鉴定中被定为B级。因为她的房子是新装修,财产损失较大,她对来鉴定房屋的技术员解释自己家的特殊情况,希望得到合理的补偿。目前,第二次鉴定的结果还没出来。她觉得损失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县城的人是人,农村的人不也是人吗?”她皱着眉头委屈地说。
八月初我第一次在鹤壁北苏村见到魏志时,他穿着一件黑色连体防水服,肩膀上挎着一个盛了鸡蛋的大篮子,拄着木棍,用脚探着水下的路面,一步一停。那时他一说话就皱着眉咧着嘴,好像有一肚子苦水想吐却吐不出来。两个月后,这个65岁、身材单薄、头发斑白的老人笑容多起来了。
据魏志统计,洪水让他损失了约1000只鸡,占总数的一半。他把一只雏鸡饲养到产蛋,成本在40多元,1000只鸡的损失约是4万多元。
两个月前,由于停电停水,井水被污染,鸡不得不喝发臭的洪水,饲料和拌料机也全泡了水。看着多年经营的心血毁于一旦,他站在鸡舍前及膝的水里,泪奔着说:“这次恐怕再也起不来步了”。
水刚来时,他打开下层笼门放走了一批鸡,让它们自寻生路。水涨起来后淹死了一批。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蓄洪期,因为喝脏水,饲料不足,潮湿高温,蚊虫病菌滋生等原因,每天都有四五只鸡因为生病被丢弃在门外的玉米地里。
在洪水浸泡下,南侧的鸡舍地面下沉,预制板屋顶和墙壁开裂,屋顶不时有砖头掉下来,他必须头顶着箩筐才敢走进去喂鸡。如果不拆除重建,就要把沉重的水泥预制板换成金属框架顶,按面积算差不多需要7000元。
魏志的压力还来自于,鸡饲料的价格每吨上涨近100元,冬季安装鸡舍用的挡风塑料布需要花800元,鸡场卧室屋顶漏了需要修……
最让魏志担心的是养鸡场的建筑损失有可能得不到赔偿。因为房屋损失的统计、评级工作已经结束有一段时间了,但工作人员从没有到养鸡场测量、登记过损失。他担心鸡舍可能因为不算住房,没有土地许可,所以不予赔偿。但他心想,养鸡场已经存在了近二十年,地租从每亩500涨到了1500,都是实在的事实。
水刚落下的时候,魏志用他的手机拍下附近的死鸡,一滩滩的鸡毛和鸡骨贴在地表。他打电话让调查人员来养鸡场等级损失,但至今没有人来过。他把照片发给负责补偿登记的工作人员,答复却是因为他没有使用某款指定的带GPS定位的相机App拍摄,所以照片不能当成证据。而那时鸡毛和骨头已经被清理掉了。
魏志的养鸡场附近有三家养猪场,损失的猪百头不等。因损失严重,短期内无法恢复生产。三家养猪场的经营者告诉我,猪场的建筑、设备、饲料等水毁损失都没有被统计和登记,保险公司只是在水灾到来前统计过猪只数量。
魏爱领的猪场有四排猪圈,原有420头猪,在水灾中全部死亡。他给31头母猪上了养殖险,每头赔了260元。他和妻子从2008年开始办猪场,把家也搬到猪场里。他告诉我,洪水后猪圈有一栋出现裂缝,已经锈蚀的猪栏、地秤、母猪育仔用的几台空调、两个化粪沼气池和设备、检测化验的电子设备、两万斤饲料和居室里的家电,合计损失在20万左右。猪的损失更大,一头成猪养殖成本2000多元,利润一千多元。他自己估计总损失在50万左右。
我问魏爱领有没有想过是气候变化导致这场水灾,有没有想过将来怎样应对。“气候变暖的事儿谁知道,这咱老百姓弄不懂。今年雨水特别大,可雨水再大我们这儿不放水都淹不了。我们这儿河道都没有出来水,就算出来河道,还有第二道几米高的大堤,根本没事儿。”关于赔偿,他和其他几个养殖户去问过村委会,村委会让他们问农业畜牧局,而农畜局让他们问村委。目前他们还没有听到具体的对养殖户的补偿方案。
李菊芳家化肥库房的地面已经清理干净,巨大的防潮塑料布被铺在地面。两个月前,仓库地面上淤积的化肥泥浆和浓烈的氨味已经没有了踪迹。四名工人把每袋40公斤的三宁牌复合肥从车上一袋袋卸下,整齐码放在地面的塑料布上。一名工人在用油漆粉刷仓库墙壁的铁皮板上的锈迹。仓库边的店面里,重新装修过的店面里放着崭新的货架,李菊芳坐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刷着小视频。
这家农资店位于卫辉市南社村北边,紧邻共产主义渠与卫河。7月22日上游水库泄洪,第二天李菊芳的店被迅速上涨的洪水淹了两米多深。店面和仓库里200多吨化肥和蔬菜种子大多数被毁,货值约100万元。水灾后,她的店得到了4万元补偿。市政府发给卫辉市工商户的补偿款按商户面积计算,以每平米40元标准发放。“淹轻了,淹狠了,都是按平方补”,她说。
南社村是蔬菜种植基地,村民大多专事蔬菜种植,对高品质的复合肥需求量较大。今年上半年化肥供货紧张,李菊芳订不到货。为确保销售,她加大了进货量,不料七月到货后不久就遭遇了洪水。
10月27日,水灾后的第一批化肥已经运到,两卡车,66吨三宁牌复合肥料。“今年化肥价高。去年这个时候搞活动时复合肥卖115一袋,今年卖到175一袋”,李菊芳说“越贵越供不上货。现在限电限产,厂家也没货。煤和油都翻了两三倍,听说油涨到8块了。”
共渠堤坝北侧的大片土地还没有翻耕。李菊芳说,九月份种最后一茬白萝卜,农民种了三次,下雨淹了三次。然后很多人就出去打工了,等到明年开春再种土豆。卫辉不属于蓄滞洪区,因此农民的水毁损失,得不到如浚县那样因为启用蓄滞洪区造成损失的补偿。
“你看我这还是个家不是?俺一个老婆儿一个老头过不了啦。”魏子用指着自己家杂乱的堂屋,难掩悲郁之情,说话带着颤音。她的71岁的老伴正在内黄县修路。现在家里只有魏子用一个人。
厨房的灶台被水泡塌已经被拆掉了,灶台上方被烟熏黑的墙上挂着锅铲汤勺。她的厨房已经被搬空了,一日三餐都是去亲戚家吃。
正房和侧房的门敞开着,门槛外各立着一块木板用来挡老鼠。地面和墙面上撒了一条条的84消毒粉。屋里湿凉的墙壁上长满了灰色和绿色的霉菌。魏子用随手一摸墙壁,手掌上立刻粘上一层厚厚的翠绿色。
堂屋里,几张桌子、床架、锅碗瓢盆,一件件间隔一定距离摆在屋子中央,让墙壁和家什保持着通风。侧屋里有一张床,一台缝纫机,床上被子用塑料布包着防潮,棉被芯上有斑斑霉点。
堂屋墙壁正中孤零零地挂着的月历牌显示8月11、12日那页。那天,水位大幅下降,离家一个多星期的魏子用穿着雨鞋回到了家里,看到家里被洪水毁掉的样子伤心至极。她把日历牌撕到那一页,取了一些换洗衣服就离开了。她至今保存着那一页,把它当成了这段逃难经历的纪念。
魏子用睡的床在西屋。白天她把被褥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晚上睡前才取出来铺床。她这么做是因为屋里很潮湿,被褥如果不收起来就会吸收潮气,晚上睡会冷。我不知道魏子用现在的生活状态该如何度过接下来三个月的寒冷冬季。但还有比她生活条件更差的人。
魏子用的邻居,83岁的蒋生云晚上睡在地上。白天他把被褥塞在堂屋里的一辆农用三轮车的车斗里,晚上铺在地上和衣盖被子入睡。他说自己铺一块塑料布在褥子底下,就不潮了。他的床被水泡坏了,放在院子里晾晒。那张床的床腿没了,床板的木条脱落了几块。我想帮他把床板搬到屋子里去,晚上至少可以睡在床板上。他说不用了,现在还不冷,等冷了会让他儿子再给他买个床。但他也说:“床还湿,还得再晒晒”。被水泡坏的家具他都没有舍得扔掉,被他一个一个搬到侧屋里。那间屋子也很潮,但如果放在院子里的话,还有淋雨的可能。
蒋生云身穿一件西装外套,带着顶带帽檐的黑色呢帽,因为耳背说话音量很大,呼吸得很用力,带着游丝样的尾音。他说自己有肺气肿、心脏病和血压高。他每个月可领民政发放的108块钱养老钱,两个儿子每年各给他一千元生活费。一个月不到三百元生活费对于一个年老多病的人有些紧张,特别是在水灾过后。“五块钱买仨白萝卜,五块钱买四斤土豆,五块钱买四斤红萝卜。”蒋生云拿着刚买的菜生气地对我说。往年他可以吃自己种的菜,今年菜都淹了,菜价却一天比一天高。这个老人靠自己完全无力置办新家具,无力维修房子,只能看他的儿子们能帮他多少。
蒋进勇和儿子蒋军磊在刚下了小麦种的土地上挖水沟的时候,蒋进勇父亲蒋凌云坟上的彩纸在他们劳作的身影后闪着白光。彩纸旁边种着一棵树苗,一根光杆上冒出几颗新芽。如果没有彩纸和小树,在刚犁过的田野里不容易发现那是个低矮的新坟。
“爷爷脾气大,心里也紧张,好好的就死了”,蒋凌云的孙媳妇马彦利说。她的眉毛拧着,对爷爷的离开感到不平。
7月29号北苏村的广播大喇叭通知人员撤离。蒋军磊把冰箱和几样家当抬到了房顶上,然后背起近90岁的爷爷奶奶上车。一家老少离开村子去了相邻的汤阴县瓦岗寨的一家宾馆。8月初汤阴发生疫情,那家宾馆不再接待外地人,一家人只好转移到内黄县的亲戚家。亲戚家不便接待老人,担心老人年岁大出意外,所以单给老两口找了一家宾馆住下。
此后疫情升级,汤阴周边地区封村封路,旅馆也都闭门谢客。他们又搬到马彦利的亲戚家。
一个月不到,这家人换了6次住处。
“他出去时就哭,住宾馆也是哭,也不吃饭。他说‘这好好的为啥叫一直跑,一直逃难?’”马彦利回忆道,“他总说‘我要回家,这一直在外住着不习惯,这是咋回事呢?’边说边哭。”我问她有没有对他解释水灾和疫情的原因。“给他讲了也不行。我都接受不了,别说他了。乡干部、村干部接连来劝爷爷,非得叫搬走,他不愿意搬,把他给气哭了。一开始不敢告诉他家里淹了,后来搬来搬去只能告诉他,他听了就着急。每次搬地方,他就问这是哪?什么时候让回家?一说就哭。”
为了孩子们上学,8月底9月初一家人搬回家里,尽管屋子乱成一团,又脏又潮,不适合居住。9月16日上午,马彦利和全家人正在收拾屋子,姑姑跑来告诉她爷爷出事了。她跑到爷爷家,看见蒋凌云躺在床上已经安静地走了。马彦利说,爷爷没病,从不去医院,还能照顾奶奶,好好的就走了。家人不敢把爷爷去世的消息告诉瘫痪在床的奶奶。
11月14日,在我离开河南半个多月后,马彦利家瘫痪的奶奶也去世了。
在我离开马彦利家的时候,她家里的墙壁还没有干透,从上到下分成白、黄和灰三层。院子里新修砌的院墙灰浆还是湿的。墙外,马彦利的丈夫和公公正喊着号子,用绳子拖动着一根先前用来支撑院墙的水泥柱。
10月下旬,河南夏季洪水对很多人而言已是旧新闻,但对经历过灾难的农民家庭而言灾后影响还在持续。水灾面前,农民和城市人的承受力不同。由于农业生产依赖天气、农民收入较低,农村建筑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一般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如城市人。而对于全球升温、极端天气频发的趋势,农民一般缺乏了解,也缺乏购买财产、农业保险的经济能力及意识。
我最先在社交媒体看到郑州地铁和隧道汽车的画面,农村的情况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不多。但从后来的报道中得知,农村比城市的灾情更严重。七月底八月初,河南卫河沿线地区开启了滞洪区后,上游灾情得到了缓解。
去年在江西鄱阳湖边,我看到对洪水稔熟的人们怎样和洪水相处,而中原地区的农民会怎样应对罕见的大水呢?
灾后的农村没有引人注目的大事,也没有激烈的冲突,有的只是庄稼和房屋的损失,拧起来的眉毛,说着说着就垂下的眼泪,和一家一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