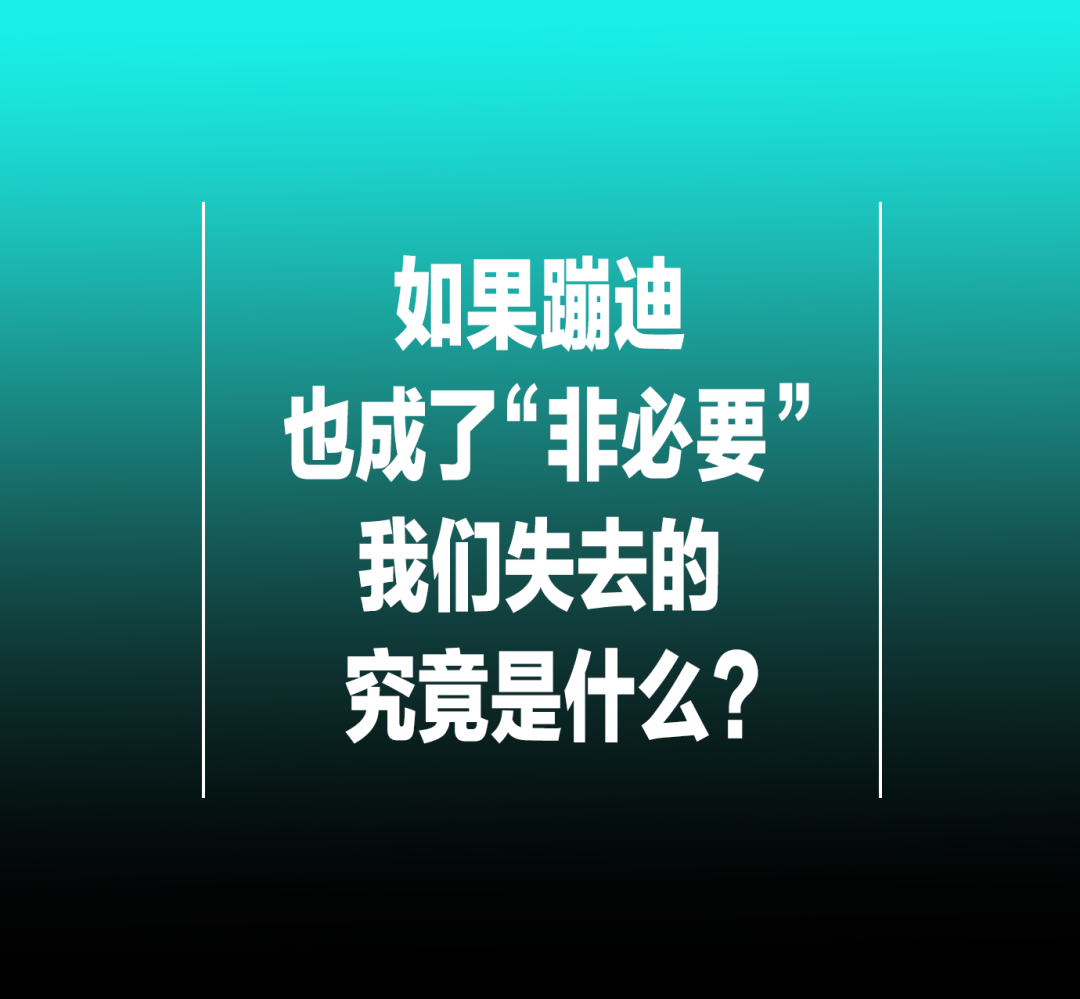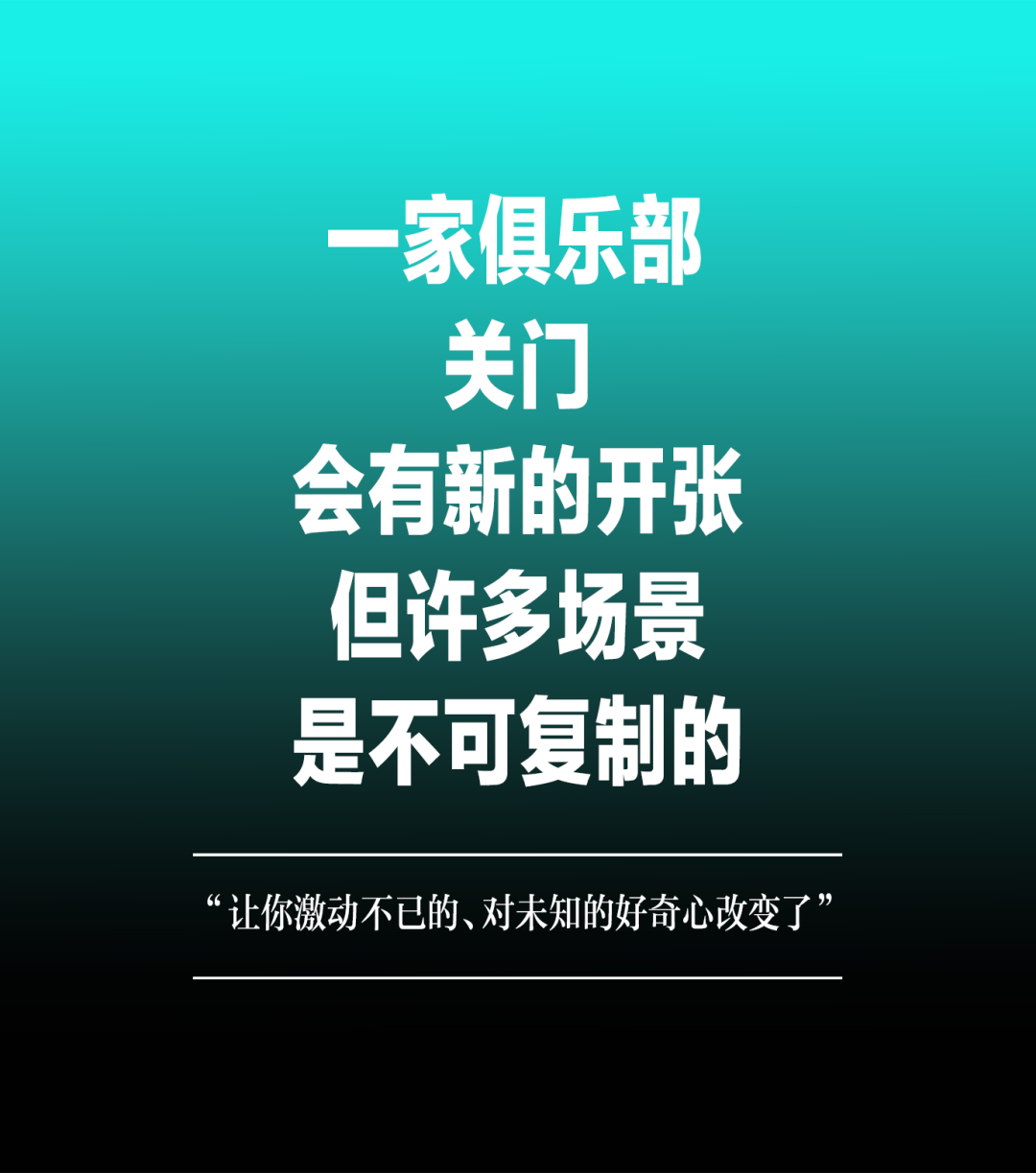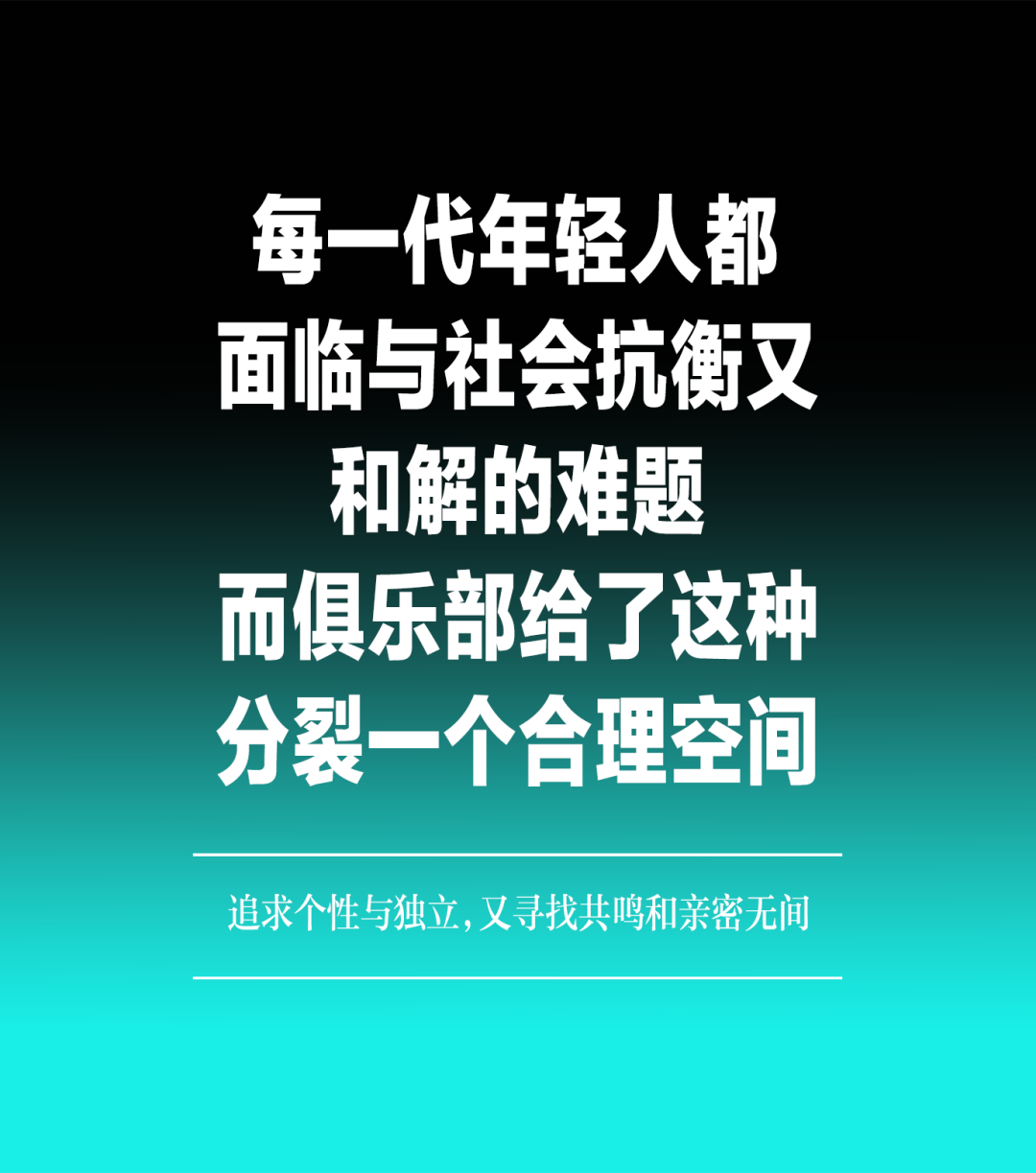信号不稳,电路不通,「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一步步失去」。疫情第三年,北京、上海、成都的地标性跳舞俱乐部(Night Club,以下简称俱乐部)陆续宣布停业,「保持期待,有缘再见」的声音最终变成了众筹网页上的文案,抑或谢幕时分的台词。告别信中,成都 Cue Club 写道,「这与冬天无关的极寒,音乐 / 像一条结冰的河 / 我们过河,被冻得直跳 / 而灵魂总是一副烧着的形象」—— 由于众筹到的金额远不及预期,今年 7 月 31 日最后一场活动后,成都武侯区科华街 2 号附 8 号 2 楼将再无人起舞,「比最冷还要冷」。
在北京,歇业 6 周后,Dada「快闪」般地开了两天,6 月 10 日又关门了;在上海,Elevator 自 3 月 23 日起暂停营业,6 月 5 日,俱乐部对外发出了「我们已经用尽其他选择,决定发起一次筹款」的声音。这场「极寒」中,上海的 44KW、北京的 Clash、成都的 Cue 均已宣布结束营业,国内 90% 的俱乐部则至今无法恢复正常营业 —— 这还只是一个圈内人保守推算出来的数字。
不好的预兆在 2020 年春节就开始了。按照北京灯笼俱乐部的传统,大年三十是免票日,许多留在北京的年轻人都会来灯笼聚一聚,但那年没有聚成。也是那一年 4 月,德国电子音乐先驱、Kraftwerk 乐队成员 Florian Schneider 因癌症去世,隔海飘来了一声几乎微不可闻的丧钟。
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俱乐部面对的,也绝非仅仅一个集体萎靡的 2022 年之春。国内俱乐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不容乐观 —— 这是长期以来各种重压后的必然。派对组织品牌 Boiler Room 中国区负责人王淼说:「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44KW 则在临别前的微信推送中说,「俱乐部和演出场地永远是第一个被关,同样也是最后一个被允许恢复营业的。」
往后将是什么?是断断续续,担惊受怕,在时不时风声收紧的环境下,「唱着关门的戏」,王淼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人们不再商量两个月之后的计划了,因为无效。今年 6 月,灯笼的主理人、DJ Weng Weng(艺名)受邀前往深圳演出,「飞机一落地,打开手机就收到短信说所有店都关了 —— 我上飞机的时候还没有这消息。后来我就没出机场,买了张机票又飞回北京了。你能有什么幻想?」
Bolier Room 使用了一种将 DJ 台置于舞池的派对形式,距离的变化,往往能引起极大的共鸣。
偶尔,憋不住的人会组织一场「野迪」,在北京亮马河、四得公园、朝阳公园,人们还能享受一种有阳光、植物、河流参与的自由摇曳的氛围。
但「野迪」同样有风险。DJ 王姐(艺名)回忆,今年 5 月 20 日晚,位于北京的某俱乐部在公园筹划了一次隐蔽的活动,只有一小部分人收到了具体的位置,想参加,要么自己找路,要么等朋友来接。然而当他摸索到现场时,音乐已经停了 —— 有警察精准地定位了这里 —— 警灯闪烁。活动取消。即刻停止。不可聚集。
他意识到,这是被举报了。没有任何犹豫,也无须确认或者争吵,连打听「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欲望都没有,王姐扭头就走:「真的是怕得要死,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危险,(而)是真的会被抓起来。」
王姐出生在千禧年,是一个自学成才的 DJ。于他而言,新冠疫情带来了一些后果难以预估的打击,被打击的包括他刚刚冒头的叛逆,以及刚刚发现的一点「个人追求」。他找到了爱好,学会了技术,却不剩什么在俱乐部锻炼的机会了。20 岁出头,不可抗力就像他每天进出小区时都会看到的,左边是一座坟堆,右边也是一座坟堆。关于那个「扭头就走」的决定,他一阵自嘲:「我是个怂人,我在国企工作,我不想把工作丢掉,没有工作我就不能出来玩了。」
但他还是忍不住问,「真的不能随地跳舞?」
除了音乐,俱乐部也在提供一种更自在和亲密的空间。
疫情似乎正在将地下文化场景乃至整个音娱产业定性为「非必要」,甚至人们的日常秩序和乐观主义也难逃一劫。在「非必要」的逼视下,俱乐部不再具备十足的合理性:「把一个社会的正常细胞,变为癌细胞,然后癌变就会到处发生,成为大家默许的事。」长此以往,「我们不是说仅仅失去了俱乐部,(而是)失去了很多。俱乐部就属于非必要吗?那我觉得我听音乐是有必要的。」Weng Weng 说。
朴树也曾在采访时表达过他的困惑,被作家王小峰记录在了他的作品集《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增订版,2019)中:「我记得从 1999 年开始,大家在听电子音乐。到了前几年我才明白,电子乐是一种享乐的音乐。我从小到大就没有放松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放松,我就觉得一肚子苦,躲在一个地方弹琴唱歌是种很压抑的状态。我不知道什么是放松,不能跟黑人似的什么都不想,晒着太阳喝啤酒。但是电子音乐就是那样享乐的音乐。」
到了 2022 年,有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 —— 小沙(化名)—— 在美国的酒吧里跳舞时,看着身边欢脱的年轻人,也在想,我们不能就只要快乐吗?
这个问题,早在电子音乐诞生前就反复围捕着中国人,按《纵乐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一书作者,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说法,持续了至少有一千年。
我问 Weng Weng:在一个紧张和有限的环境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无忧无虑的电子音乐?Weng Weng 回赠了我一个电子音乐发展早期的故事。
1989 年柏林墙被推倒,在某座坍圮大厦的地下室,出现了柏林最早的跳舞俱乐部。从美国底特律传来的 Techno —— 一种更低沉、更硬核的电子舞曲 —— 成了当地年轻人面对困苦和巨变时的一个出口。(也有说法认为,底特律 Techno 和德国 Techno 体系并无先后之分。)「Techno」一词出自 Alvin Toffler 的科幻小说《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小说中的信息化高阶叛军就名叫「Techno Rebels」,这决定了 Techno 有反骨。彼时,冷战尚未终结,但墙毕竟塌了,人们开始选择修复一些东西。而率先被修复的,便是近乎原始的、以蹦蹦跳跳为形态的希望。
新电源被插上了,因时局波动而无处宣泄的眩晕被释放了。在 Techno 的文化内核中,既有后工业时代人类对科技的怀疑与反思,又包含了人们对于庇护和享乐的渴求。只不过,它恰好是一种舞曲。在柏林的地下俱乐部,用舞步同时阐释 Techno 的两面性似乎并不矛盾。
人们享受俱乐部的类乌托邦性质:没有阶层,没有歧视。所有参与者会一起清理场地;灯光简陋?那就租发电车 —— 人人都愿意贡献力量,在「冷酷」的音乐中建立亲密的关系 —— 当然,这是文学性的回眸一瞥。DJ 10000(艺名)说,在俱乐部几十年的演化里,Techno 从一种经济下行环境中的自我麻醉,到近 10 年间对现实议题的介入,「种族、性别平权、反霸权等等,已经有了更多社会意义了。」
但实际上,电子音乐自落地中国起,就一直被归为边缘文化。今日的萎靡,不仅仅来自疫情的冲击,更在于有效经验的缺失。王淼很早就开始参与各种活动的策划和音乐节的组织。在她看来,这个行业一直起伏跌宕,短时间内的发展未能创造巅峰,但每一次「下行」都是实打实的:商业夜店的冲击、北京五环以内禁止大规模演出活动、临时出台的营业性演出条例、胡同改造、三里屯「脏街」整顿 …… 以及疫情。(但王淼强调,暂时的下行不能用来证明俱乐部文化本身的没落。)有几年,实在找不到场地,「针刺疗法」的 DJ 要么寄人篱下,要么做流浪艺人。起初王淼认为还是应当保持乐观,「我们是时候触底反弹了,」但今天看来,「(俱乐部)怎么还在说触底反弹?」
那些幸存的俱乐部和资深 DJ 往往被视为「活字典」,Weng Weng 甚至玩笑道:反正大家总问我,要不然我去开一个咨询公司吧,就算不是活字典,也是一个错题本。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
起舞的时候,也是在和自己相处。
成都的第一家俱乐部 Underground 诞生于 2006 年。创办人 Cvalda(化名)相信,如果说电子音乐是舶来品,俱乐部和派对文化需要一块本土化的土壤,那么应该没有比成都更适合的城市了 —— 但成都人对「耍」的热爱也没有帮助俱乐部活下来。Cvalda 说:「在我们之后的好几代 Club 也都很难经营得特别顺利,做地下俱乐部最重要还是人群的问题。需要大家愿意走出门,也愿意去了解,甚至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俱乐部运营者和 Promoter(推手)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把文化氛围制造出来,也要真的有料。」
就像做 DJ 需要不断自我革命一样,俱乐部的经营者也在反思。二十几年过去,除了年轻时用不尽的积极和热血,这个领域也需要更专业的厂牌、制作人和店长。Weng Weng 认为,俱乐部文化所处的「非主流」状态和相对业余的组织环境,或许就是既无真正的改变,也没能形成更好的文化情境的症结:「并不是选择了这种所谓的地下文化,你就比别人更不幸。你的运营能力和理想是没有关系的。」正因如此, Weng Weng 一手开创的灯笼,一直在稳定的生命力和较高的专业水准上饱受好评。有 DJ 曾在灯笼里看到 Weng Weng 扫地,如果问「灯笼如果不开了怎么办」,他会说「Weng Weng 还在呢」。
和 Weng Weng 这样的行业开创者不同,李匪是一个外行人。他选择在 2021 年开办 Clash 的动机相当「不纯」:大病初愈后,他感觉自己老了,「要不然就去做一些年轻人的混蛋事儿吧,我还能再躁一躁,让大家有个玩的地方。」他的俱乐部事业是一次纯粹的实验和冒险,试图借此混入一个青春的世界。但他失败了。
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对一些东西很敏感:能不能盘点库存、有没有职业化经理人,以及这帮人是不是接受商业。答案都是直截了当的「不」。他甚至怀疑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就是喝酒、玩音乐,江湖里不能讲究记账,谁斤斤计较运营,谁就会被踢出游戏。如果研究俱乐部的短期效益和商业上的可持续问题,李匪的实验很重要。他认为,倘若这个行业在运营上的专业度始终无法提升,又只培育了一个小众,且忠诚度很低的群体,俱乐部「别说盈利,连存活都很难」。
但对于 Weng Weng 这样的行业老炮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然不是经营能力和专业素养的缺席。天花板已经明明白白地暴露在头顶 —— 越来越多的不可控、不确定,以及所有人都无法独善其身才是问题 —— 局面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一共也没有多长的时间让这个(俱乐部)文化把根扎下来,现在就要逃跑了。」王淼说。已经有 DJ 朋友开始离开北京、上海,一些新的俱乐部则出现在海口、大连和西宁这样的城市。众人口中俱乐部的「纯真年代」,只能到回忆里去找寻一些踪迹。
射灯穿透的空气里,似乎有荷尔蒙散播的「孢子」。
比如北京。那时候,三环以外都是卖地的,三里屯的脏街还热闹非凡。依附着脏街,周边陆续有 Loft、88、99、九霄、灯笼、白兔、Migas 等俱乐部浮出水面,形成了一个丰富、混乱又完整的文化场景。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记得当时一场好的派对是什么样子。
就像 Weng Weng 认为好的 DJ 应当像一个巫师,好的派对往往也有「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性质。在所有文化的生命仪式中,你都能看到派对的「快乐影子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无论它是被叫作庙会、狂欢、演唱会,还是葬礼。这意味着,人类始终需要一片空地起舞。而根据法国社会学家 Émile Durkheim 的理论,集体欢腾是生产生命力和社会团结的源泉。
2000 年 6 月 17 日,金山岭长城旅游公司 —— 这是写在票根上的主办方 —— 在长城组织了一场锐舞派对,而实际策划者是 Weng Weng、DJ Yang Bing(艺名)和英国 DJ Will 三人的组合「中国打气工厂」(China Pump Factory)。Weng Weng 形容这场派对的感觉「就像初恋」:美好不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恰好在同一刻,快乐与快乐发生了共振,仿佛世界不存在什么彼竭我盈,唯一需要遵循的只有偶然、随机与巧合。有人玩得忘记了第二天还有航班。Nico(化名)记得,她回头看见 88 俱乐部的老板 Henry(化名)满脸笑容地看着众人跳舞,她说:「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
Nico 曾是一名电子音乐的重度发烧友,从一个人在家听张有待的电台节目 Dance FM 起,她就喜欢上了这种音乐。可以说,她的整个青年时代,十多年间的每一个周末,都泡在了俱乐部里。
那时候,她一瓶矿泉水也能跳一宿,仿佛不知道什么是累。从九霄玩到对面的 88,再去大成永和吃早饭;或者去三里屯 3.3 大厦地下的灯笼,穿过一家游戏厅,窜到白兔,一直到早上七八点,然后买一张「脏街」上的煎饼。「醉里不知身是客」,不知一夜几万步,偶尔喝得烂醉,她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从一家挪到了另一家。
她回忆说,那时的自己,某些瞬间真的进入了「冥想状态」。最近几年,她发现自己的膝盖有严重的积液 —— 她并不怎么运动 —— 罪魁祸首大概是那些年「跳舞太猛了」。遗憾?绝不。那是「幸福的积液」。
哪怕是「非典」那年,他们也没有停止跳舞。
2003 年,Nico 大学一年级。这一年 2 月,她和朋友一起在朝阳体育馆看了一场演唱会,主角是 Suede 乐队。(根据当年媒体的报道,演唱会堪称混乱:直至暖场嘉宾表演结束,场地中央仍空着 400 多席;约 100 位乐迷在 Suede 登场前几分钟突然拥向了舞台;现场除了乐迷,还有打瞌睡的中年男人、哄孩子的老头儿老太太,以及一直「像一块雕塑一样」站着观演,中途退场的崔健。)FM 俱乐部的老板张有待和竹书文化公司的沈永革操盘了这次演出,并将 Suede 请来 FM 做了一场余兴派对。「非典」期间,学校停课,街上的柳絮比人多,但俱乐部没有关门,到了晚上,Nico 会溜进 FM。她记得,俱乐部里总是人满为患,人们不分国籍地聚在一起,好像疫情不曾发生。有一天,张有待忽然把 FM 通往日坛公园的后门打开了,一群人把 DJ 台和设备搬到户外,爬上了公园里的小山,望着长安街,「整个北京在音乐的包裹里,安静得像个婴儿。」
音乐不光制造集体欢腾,也能塑造人对一座城市的认同。音乐即故乡。
Nico 不会忘记这样的北京。
那几年,王淼真的觉得北京有戏,她充满了希望。一代人正年轻,有活力,也有想象力,王淼「恨不得北京会是将来的柏林」。2009 年,她和电子音乐厂牌「针刺疗法」的同伴在 751 炉区广场,做出了第一届 Intro 音乐节。
751 厂区被认为是北京最适合操办电子音乐派对的场地之一,工业遗址之上,闪烁着亢奋的电子火花。在这里,你不需要读什么《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或《技术与时间》,节奏一响,就该雀跃 —— 21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下一个十年仅一步之遥,你可以听着 Techno、跳着舞,闭眼跨过去。
Intro 音乐节自立项之初就被纳入了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和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的「相约北京」系列联欢活动。「这是一种 Peace and love(爱与和平)的能力。」Weng Weng 说。他认为,好的活动与健康的文化环境很有关系,关键词是求同存异,找到共鸣。电子音乐造就的便是这样一种美好:「在 Intro 里面,每个人都笑开了花,大家喝一杯,每个人拥抱一下,各种肤色和不同国家的人,都找到那种爱的感觉,这才叫作『相约北京』。」而面对如今俱乐部文化的每况愈下,「我们越发忽略和失去的,就是人的多样性,价值的多样性。」
往事已然不可追。一家俱乐部关门,会有新的开张,但许多场景是不可复制的。「让你激动不已的、对未知的好奇心改变了,无论如何是达不到当时的那种情景和心态的。」Weng Weng 说,「真正好的状态,是自由,是找到自我。比如当我们说要『复制』一个经典,或者要穿一个什么衣服(来致敬经典),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就抑制了思想的解放。」
一句话,俱乐部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独立思考。
王淼的理解略有不同,她把俱乐部文化比作「自我和集体的一个矛盾体」:人们追求个性与独立,又寻找共鸣和亲密无间,就像王姐说的「想要一脸孤独地走到人群里去」。每一代年轻人都面临与社会化抗衡又和解的难题,而俱乐部给了这种分裂一个合理的空间。人们用「卧室艺术家」这一同时包含了赞誉之情和戏谑之意的称呼比喻一部分 DJ 及音乐制作人,在潮流品牌 Floso 的主理人刘伟看来,「卧室」代表的相对局促的空间或环境,以及音乐上更远的延伸,形成了一种只属于俱乐部的巧妙张力。他在 2004 年开办的电子音乐厂牌便借鉴了这一意象,名叫「BedZoo」。
很长一段时间,王姐都没有自己的卧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算「卧室艺术家」,但他会问很多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有一天出来玩,同一个俱乐部,同样的人,放同样的音乐,这星期是这样,下星期还是这样,那我还来吗?人们为什么没能发现有时候一个月放的(音乐)几乎一样?」
「最近大家好像都只听 Techno,有的人出门就问『有 Techno 吗?我需要 Techno』,他们是真的喜欢吗?」
「俱乐部的音乐从多元变得单一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玩露营,这个也玩腻了就玩野迪,现在野迪也玩腻了,我们还能发现什么新东西?人为什么总是需要新东西?」
「有一波人跟你说你就是你,你是独一无二的;另一波人跟你说,你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你就是普通人一个。这时候你该相信谁?还是只相信你自己的想法?」
「我发现,可能我觉得很高级的东西,有人就会觉得很低级。我其实和别人都一样,和其他 DJ 是一类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那我是谁呢?」
文艺理论家 Mikhail Bakhtin 认为,狂欢中包含着「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破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但显然,这不是一个狂欢的时代。
Nico 在另一个层面上同样经历过这些问题的拷问。她的故事或许是另一种答案:
2014 年,参加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声呐音乐节(Sonar Festival),Nico 在柏林待了一周,满街的电线杆上贴着各种活动海报。三天三夜,她忘了睡觉,逛遍了那些传说中的俱乐部 —— Berghain、Watergate、Weekend …… 还有大大小小的户外派对,每天都与奇迹狭路相逢。她跟随意犹未尽的人群,梦游般从一个派对到另一个派对,最后停在湖边,搭好 DJ 台,继续跳舞。
湖边派对结束后,已经是早晨,街上正举行骄傲大游行。她走入人群,又精神抖擞地走了好几条街。那一天没有吃到高压水枪,但后劲凶猛,猛到此后很多年她都提不起玩的兴致。回国后再去俱乐部,就算音乐再强,也只是含混的回响,相比回忆中柏林的声浪,像失了真。
大狂欢散场后,人们确实有可能这样:光芒万丈的心气停留在了某一刻,不再跟随,只是目送。年轻人总有新的玩法和他们挥霍自由的方式,而关于未来,Nico 说:「它(俱乐部文化)会自然地发展下去,会根据所在的城市,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去发展,它会变成它应有的那个形态,就是像水一样。」
今天的她眉目舒展,皱纹也妥帖,从「集体欢腾」过渡到了「冥想状态」。过去清晨 6 点还在舞池的人,如今同一时间会出现在瑜伽课教室,用新的智慧压倒乐往哀来。练习瑜伽之后,她觉得自己竟然更懂音乐和跳舞了 —— 它们是最「自然而然」的东西。亮马河边,一台蓝牙音箱,每人放一首歌,也能跳起来。音乐和环境带来的「沉浸感」就是这样:你在树边是树,在水边是水,在俱乐部里是摇晃的风景。
2022 年 7 月底,有一些派对陆续恢复了。Weng Weng 说,他对后半年仍有一丝好奇,像看一本小说一样,想知道后面的故事,比如灯笼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俄乌战争会怎么样。
王姐说,他想知道,如果现在硕果仅存的俱乐部已经把演出排到了 9 月,那他什么时候能上台?他能做出别人没玩过的新东西吗?
7 月 16 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十层,Dada 和 U2 美术馆合办了一场久违的派对活动。在名为「爱的艺术」的流动影像展旁,是一个大舞池。音乐震颤,从设备里泻出一片堰塞湖,从 DJ 台开始,上游的水坝正在解体,摇晃的人群乞求都市荒漠里的人工降雨,他们的动作被灯光反射成一帧一帧的破碎镜头,好像舞池也会眨眼睛。我开始沉入其间,时不时碰到朋友甩荡的手臂。我眨眼睛,感受到了一阵人们所说的有限的、自由的眩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