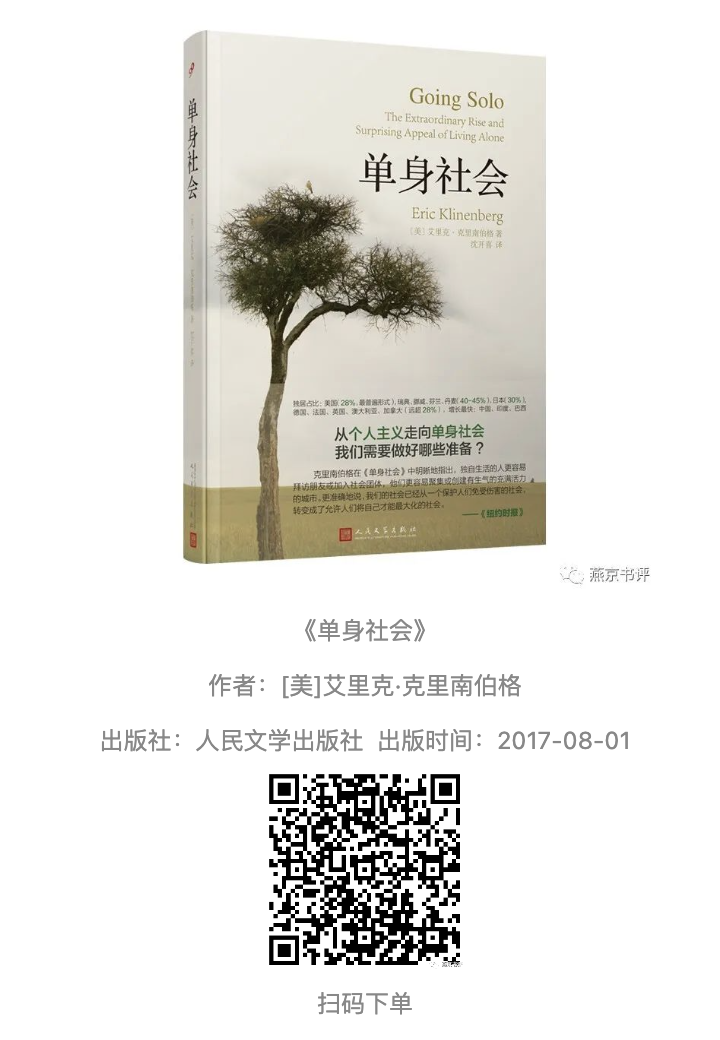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应是一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生理机制,在原始社会中受到崇拜。但男权社会通过种种架构让它成为“义务”。通过非常态化不具有母性的女人,抹除生育的神奇和独特;又通过浪漫化“新生命的诞生”(将生育的主语从女性身体置换成孩子自身,从此,孩子变成“神”的恩赐,而不是母体的创造),制造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回报,而逃避现实的和物质的支持。
《欲望都市》。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房租稳定’一词,也比‘嫁给我吧’更加让人心潮澎湃,它蕴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
传统社会中,女性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输送给男性社会,嫁人、生子,完成她对男人、家庭、孩子、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的义务。但工作,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走出流水线传输带的机会:一旦女性不再需要男性的经济支持,她就可以保持单身,从而脱离传统女性的被制定好的人生轨迹。
“女性想去工作”这件事却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批判。人们把社会问题怪罪在想外出工作的女性身上。有人说:“我们正见证着这个国家一点点走向崩溃的边缘,而这都归咎于单身母亲。”
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段漫长的女性争取工作的过程,以及男权社会提出的种种反对女性工作的理由。
但为什么要把女性留在家庭中?谁因此受益?传统社会又是依靠什么方式来将女性与家庭绑定?社会需要女性,但却不承认女性的价值,而是用话语、污名、甚至是法律实现对女性的束缚。如果一个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对某个群体的剥削之上,那争取自由的行为引发传统社会的解体,也未必是坏事。
为了阻止女性保持单身、追求理想,他们曾提出什么理由?
女性总是被提醒,一个理想的人生应该精确地被划分阶段:要在三十岁之前结婚,三十五岁之前一定要生孩子。年纪大了就会失去性吸引力,婚恋“市场”上的“优质”男性会被挑光了,还会影响生育,懊悔终生。年轻漂亮的女性永远在婚恋市场上有更大的优势,三十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是“大龄剩女”。
不过,随着性别议题的进展,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发问:为什么男性可以被认为越来越有韵味,而大龄单身女性则被称为“剩女”?——这个社会,有多少话语是被创造出来,用来“规范”或束缚女性的?
单身女性被塑造为“没人要”的。一个朋友对作者提到他向妻子求婚的原因:“你不会让那样的商品一直放在货架上。”
单身女性被塑造成“自私”的。特雷西.麦克米伦(Tracie McMillan)2012年所著的《为何你迟迟未婚》中写道:“你只关心你的大腿、你的衣服、你的法令纹。你只关心你的事业……”这些被称为是“不健康的自我关注行为”。言外之意,单身女性没有把能量花在照顾家庭和孩子上,而更多地关注自身,这就是自私。“一个真心想爱和值得被爱的女人,就应该愿意以伴侣为先。”
单身生活被塑造为“寂寞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单身女性的心境:“她害怕夜晚静临,害怕黑夜笼罩城市,害怕各家温暖的厨房里亮起灯火。”但人们总是过多关注单身女子的“寂寞”,而鲜少呈现婚后女性的寂寞。这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有多少不快乐的母亲将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有多少人生长在一个无爱、但又无法分离的家庭中的。“当你躺在理应是你最亲近的人身边,却只感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没有心意相通时,那反而是你最孤独的时候。”一名主妇整天待在方寸之间的家里,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的家务,社交只限于与邻居主妇闲话家常时,她作为一个人的情感、追求与梦想,有人关注吗?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女性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衰老。许多人害怕被叫作“阿姨”,因为这个对中年女性的称呼似乎描述着一种无所事事、不修边幅、好管闲事的不讨喜的女性形象。长久以来,这是被大众媒介呈现的唯一一种中年女性的形象。
《我的天才女友》中,主角莱农看着身边的中年妇女,感觉非常迷茫:她们的身体被消耗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让她们只关注鸡毛蒜皮、终日围绕着孩子和饭桌,消耗着自己的身体和人生?
工作有时是对主妇的救赎。书中记录一位主妇:“回归了工作以后,她身上发生的变化就像昼夜一样分明。她很忙,但她再也不用每星期擦三次地板了。她开始好好打扮自己,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表。”
一些人认为不去工作,靠男性养是让人羡慕的“女性特权”。“我养你啊”好像是一句浪漫的告白。但任何一个体验过“被别人养”与“被自己养”的区别的人都知道,看似轻松的主妇生活实际的重量。书中写道:“每买一件东西,她都要慎重地考虑权衡,失去金钱的自主权让萨拉的内心备受煎熬。”身为主妇的母亲上一次为自己花钱是什么时候呢?
历史上,女性争取工作权利是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最初,女性主义不得不声称工作有利于女性在家庭中保持平静和愉悦。为了尽量减轻男性的“不安”,她们在争取工作权利的同时宣扬女性不爱男人或孩子是可怕的激进——工作不会使女性背离家庭。
但反对的声音却说:“女性工作可能形成‘母系社会结构’,挑战父权制社会,从而‘不利于社会的长久发展’。”
继而,女性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很多需要脑力或体力的工作。同时,能够和男性干得一样好的女性则再次迎来社会上的污名。1853年《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写道:“那些不男不女、总是渴慕成为女中豪杰、绝不肯输给男人的人,她们不配做一个女儿、母亲和妻子,因为合格的女儿、母亲和妻子需要有默默奉献的精神。”
这句话非常匪夷所思,它把做母亲或妻子置于与男人一样工作的行为之上,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不是认为这个社会中女人比男人的贡献更大。如果母亲与妻子对家庭的默默奉献比让她们外出工作更重要,那为什么社会给予那些工作着的人更多的回报?
女性的工作能力到底能不能与男人比肩?能不能说女子不如男?这是个迷。因为“企图”做得和男人一样好的女人不仅不能被男性群体接纳,还会被“踢出”女性范畴。
女性的呼声很难改变既存社会,但社会的需要可以。当社会劳动力出现匮乏时,当男人因为战争离开家庭时,女性就要作为“替补”,撑起半边社会。书中写道,18世纪,由于男性西迁,东部女性结婚率下降,这时,出现一种论调:“单身是福风潮”,告诉女性即使单身,她们仍可以照顾病弱和老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中小学扩招,对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增加。“由于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天生适合养于儿童,她们自然而然填补了这些空缺。”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又启用女性从事护理行业。二战时期,男性去打仗,女性证明了她们也能让生产高速运转。
但女性又往往被“用后即弃”,社会上的用工机会缩减时,女性就又会被要求“回到家里”。
在20世纪的女性解放之后,女性在学校受教育成了社会惯例,但50年代又兴盛起“回归家庭”的潮流:无论在哪个名校接受教育,无论有多强的天赋,在毕业前还没有嫁出去的人生是失败的。1960年,在巴纳德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二的大四学生都在毕业前订了婚。“女人一旦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这个真相便会显现:她们精心打造和修护的自我身份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为丈夫和子女牺牲这所有的一切”。
才华、智力、梦想,纷纷成了让一个女孩更有吸引力的附加属性、一种得到如意郎君的筹码。在没有足够分量的“女性解放”之后,女性迎来的只能是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必须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从朴素持家到“上得厅堂进得厨房”,既要美艳又要顾家,既得能为丈夫增光添彩又不能成为“红颜祸水”。
如果女性没有足够的付费能力,如果女性创业者面向女性的的产品不能得到足够的利润——也就是说,如果女性未能把握社会和经济的命脉,那么一切文化上的性别解放最终都会使男性成为受益者。
二战中的女性
直到现代,事业仍常常被放在婚姻的反面。我们知道,事业有成的女性常常会被问:“你怎么平衡事业与家庭”,而男性几乎不会被这么问。
数据显示,婚姻帮助男性的事业,而损害女性的事业。“不论受过大学教育与否,男性结婚越早,挣的钱就越多。”“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他们的工资平均上涨了6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她们的工资会下降4%。”
“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获得了家庭生活,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一种帮助,而非障碍。’”
男性找不到配偶,往往会怪罪女性彩礼、要房和车的“拜金”行为。男性对“贫穷的人找不到老婆”的抱怨也侧面说明,男性不想保持单身,男性要求社会支持他脱离单身——也就是说,婚姻在整体上对男性是有利的。
人们可能争辩说,现代女性已经有了同时得到家庭和工作二者的自由,它们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没必要宣扬为了事业保持单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对大多数男性来说,他们愿意选择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孩,还是一个比他们更聪明、更有进取心、更忙碌的女性呢?
如果不影响事业和追求,谁不渴望爱情呢?书中几乎所有女性运动领袖都终身未婚,包括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罗斯.施奈德曼、社会活动家莉莉安.瓦尔德等。英国护士的先驱、统计学家南丁格尔多次拒绝求婚,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躲避结婚。新闻摄影师霍莉曾因“对工作的忠诚”,吓跑了许多求爱者。她说,“对很多男人来讲,强大的女性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单身不仅仅是女性要向社会争取的权利,也可能是女性为了自由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女性仍义无反顾地选择支付这样的代价。“即使女性只能做一些辛苦却不讨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或伦敦这些城市里当服务生,她们还是‘可能更愿意保持单身,因为这起码可以为她们提供有保障和独立的生活。’”
影片《小妇人》中,乔也因为她写作上的追求而拒绝了劳瑞的求婚。
女性获得更多权利会让社会变糟?**
19世纪的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这样写道:“让女性接受与男性相同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如果有一天女人误解了女性天性赋予她们的低等工作,她们就会离开家庭,加入战斗,那一天便是社会革命的开始,一切维系家庭的神圣纽带都将消失殆尽。”
是什么样的人在担忧原有的社会发生变动?女性寻求权利和解放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这将彻底毁坏我们的社会”的指责和质疑。
女性对人类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照料家庭,进行小型生产和修补,维持社会的稳定:预防单身汉犯罪等等。但女性的种种“贡献”却不被看作女性的价值,而是其“义务”——拒绝为男权社会提供这样的服务甚至一度被法律禁止。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批评单身女性“把首先要为建设人类文明所尽的基本义务扔到了一边”。男权社会亟需女性的“服务”,但绝不承认这对社会是重要的,相反,他们试图让女性相信,不提供这种服务,会让社会变糟,是自私、有罪的。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女性的生育功能。
罗斯福曾说:“如果一个种族的女性不再大量生育,那么这个种族将毫无价值。”
“别任性”播客中,嘉宾覃里雯指出,男性在神话中掠夺了女性的生育能力,比如上帝取出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男性试图把生育这样的“超能力”收为己有,用蹩脚的男神造人故事夺取属于女性的能力。
女性的生育能力本应是一种权力:它作为一种无可替代的生理机制,在原始社会中受到崇拜。但男权社会通过种种架构让它成为“义务”。通过非常态化不具有母性的女人,抹除生育的神奇和独特;又通过浪漫化“新生命的诞生”(将生育的主语从女性身体置换成孩子自身,从此,孩子变成“神”的恩赐,而不是母体的创造),制造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回报,而逃避现实的和物质的支持。
即便女性的生育如此重要,但通过让“权力”变为义务,社会可以使女性的身体独自承担生育的代价。前段时间高铁应不应该售卖卫生巾这一话题引起风波。它一方面表现出一些人坚决反对“单给”女性群体提供男性无法“享受”的“好处”:卫生巾只惠及女性群体,而对女性的补贴,就像是对男性不公平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它再次提醒我们,主流社会仍然认为,女性为了生育而必须忍受的种种生理不适,仍得女性自身去承担,社会无需对此给予帮助。
如果新生劳动力是社会资源,那政府难道不应该承担传统中“丈夫”的责任吗?
工作对怀孕女性的歧视。
为了促使女性进入婚姻,长久以来,社会没有给予婚姻中的女性更多的保障,而是挤压女性保持单身生活的选择。17世纪,“向未曾婚配的单身女性赠予财产”是一件“罪恶之事”。还有法律规定“如果未婚女性在7年之内仍未结婚,其拥有的土地一律没收。”
直至现代,社会依然害怕给予女性过多的“福利”,因为这可能促使女性进一步觉醒。施拉夫利说:“他们只把钱发给女人,所以就没有男人的事了。”2012年反女权斗士菲丽斯.施拉夫利警告说:“女性会拿政府来取代丈夫”。本来女性需要丈夫养才能生存,现在女性可以工作了;本来女性需要丈夫保护才能走夜路,现在社会保障女性不受骚扰和伤害了。
“在美国建国之初……政府通过压制女性在经济上的发展,来保障男性的经济和职业前途:不给女性同等的经济和公民权益保护,是女性被迫依靠男性;将职业做性别划分,女性只能从事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家政和幼教工作。将女性囿于家庭空间,进一步确保男性占领公共领域。”
没有女性在外出工作时想的是“我想要一份工作,目的是永不结婚”。但每当女性想追求更多自由、更好的生活时,家庭和生育就跳出来试图阻碍。是谁让女性的选择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让女性的单身成为政治问题?社会压缩单身女性的存在空间,让女性没得选,不得不进入婚姻。这非常诡异:如果婚姻不是对女性的剥削,又何必如此压缩女性的选择?
2019年,徐枣枣(化名)将拒绝为其提供冻卵服务的医院告上法庭,三年之后,这起我国首例“单身冻卵案”败诉。
女权运动让我们反思,如果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转是建立在对一个群体的压迫之上(如同古希腊的思想建立在奴隶的无偿劳动之上),那我们应该维护旧有的社会,还是建立新的秩序?女性的身体对社会和人类延续至关重要,那社会是否有权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管理甚至剥削之上?
另一方面,在女性运动的历史中,女性如此渴望被现代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工作。这其中是诸多因素的交织,但我们尤其应该思考这一问题:当我们谈工作对人的剥削和异化时,它是与性别问题对立的吗?如果女性从工作场所退场,男性的工作待遇就能变得更好吗?
由于社会并没有为女性设置任何出路,因此当女性决定反叛时,她们必须打破一切——打破社会分配给她们的身份,打破舒适的生活,打破家庭的温暖和保护,甚至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建构本身。种族、阶级等种种不平等、性取向歧视等,都是女权运动的敌人。女权联合一切社会边缘群体。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全面反叛,是女权运动或个人的女权主义实践的特色,这无疑可以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范例,一种值得借鉴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