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恐怕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在公共领域谈论任何话题都是危险的,我们似乎失去了理性交流的能力。
尤其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经常一言不合就相互攻击。有时候根本还没有仔细听对方说了什么,就根据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恶语中伤,因立场不同而扣上大帽子,最后以删好友或拉黑对方作为结局。
这种交流很大一部分依托于互联网,它的便捷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互联网产生之初,有许多理想主义者对它寄予厚望,认为网络空间可以成为一个不同思想能平等沟通的乌托邦。
它在早期的确呈现出这些特征,但是随着技术的民主化和社交媒体交流变得越来越非正式,它离人们期望的“公共领域”已经渐行渐远。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对立、回声室效应,甚至网暴等现象已经让人们对网络交流失去了信心。
公共领域概念的代表人物于尔根·哈贝马斯不久前也断言,社交媒体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半吊子的公共领域,它并不能承担人类理性沟通与交流的任务。
那么什么才是理想的沟通,它需要什么条件,理性的沟通一定是理想的沟通吗?什么是“公共领域”,网络是否有可能成为理想的“公共领域”?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聊聊上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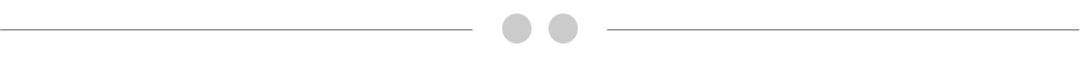
讲述 |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 | 看理想App节目《传播学100讲》
1.
什么是“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1929— )经常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这个说法或许有待商榷。
从辈分上来说,他确实是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学生一辈,后来他还做过阿多诺的研究助理。但是从研究观点和风格来看,他却很难说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员们有什么明显的传承关系。甚至,霍克海默对他的研究还有所不满,认为过于政治化。
事实证明,霍克海默看人还是非常准的,他和阿多诺等人都是反对肯定性,主张不妥协地批判社会的,他们并不认为存在着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哈贝马斯的理论是肯定的和建构的,他一直在为民主制度寻找理论依据,设计各种现实的政治方案。在某种意义上,他后来变得越来越保守,这也使得哈贝马斯离他的老师们越来越远。
哈贝马斯于1959年离开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转到马尔堡大学,并于1961年在那里通过了教授资格论文。
这篇资格论文隔了将近30年后,直到1989年才翻译成英文。虽然时间跨度长,但是发表之后就名声大噪,成为经典之作,这就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是因为这本书,最早由阿伦特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才被人们广泛接受。
和公共领域相对的是私人领域,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私人领域的特点是自治,或者说自我管理,比如家庭生活、经济活动,只要你遵守法律和道德,干什么都是你的自由,别人管不着,私人空间神圣不可侵犯。
而公共领域则意味着个人走出这样一种互不相关的私人状态,进入到了一个平等、理性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不属于任何人,却向所有人开放,并且进入后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只考虑每个人自己的私人利益。
《监视者》
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这个新兴的空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是在17 、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
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
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而一些场所比如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艺转到了政治。
而要真正追溯这种空间的起源,我们还要回到更早一些在封建末期的沙龙,那时就已经出现了公共领域的萌芽。
在封建社会末期,西欧的宫廷权力衰弱,市场文化逐渐兴起。在这样一种开放的私人小群体中,人们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理性地交流彼此的观点,就形成了“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还有带有自治性的,独立于行政国家和市场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公共领域的前提是自由参与而不是强制加入。在这里,身份平等取代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礼仪,人们由文学批判,扩展到政治批判。作家和艺术家不再只为宫廷的恩主们创作,新兴的市民社会带来了市场需求,他们可以从市场中获得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
在这个时期,刚刚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还没有严重的垄断和大规模的市场营销活动,对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维持起着积极的作用。
一些出版物和报纸把市民阶层的私人成员联系在一起,逐渐造就了一个新的理性群体——“公众”(the public)。他们在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私利,同时还遵守理性的、“大公无私”的立场。
《华盛顿邮报》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的特定历史形态,把它看作一个“理想类型”的话,只要是能够贯彻自由、开放、平等、理性精神的,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由公民参与的论坛,都可以被称为公共领域。它既可以是面对面的聚会,也可以通过各类媒体间接进行的活动。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随着资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渗透到整个社会,这些媒体和公共空间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从属于商业资本,而接下来的政治公关、民意测验等更是使公众表达的权利被代表甚至剥夺。
公众失去了原来那种平等、理性、开放的交流空间。于是发生了布尔斯廷在《幻象》一书中所描述的现象,虚假的声望、形象取代了真正的公众意见,最后导致公共领域又重新被封建化。
2.
沟通的目的与有效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及其结构转型》只是他早期的思考,还主要局限于经验现象的讨论。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公众意见是如何出现的?
现在看来,这个教授资格论文尽管具有开创性,但还是有很多不成熟之处。比如一些历史学家质疑他是不是把历史理想化了,可能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理想的阶段。
同时激进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批评他说的公共领域只包括资产阶级的男性,而没有包括工人阶级的报纸,也没有考虑女性的交流空间。还有一些人提出他没有考虑公众的反应及能动性,夸大了媒体的影响,有魔弹论之嫌。
17世纪的伦敦咖啡馆,图源:British Library
后来,哈贝马斯就在此书的修订版中做出了一些订正,并且超越了早期的研究问题,转向了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与人如何才能达成共识。换句话来说,我们能否好好说话,能否相互理解,公共领域中人们相互交流的理性前提是什么?
这其实是涉及到人类社会应该以什么秩序存在的基本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无法达成共识,那么真正的民主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哈贝马斯从经验的研究开始转向一种规范的研究,就是这个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而不是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什么。
哈贝马斯认为这个目标可以实现。首先这种共识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把人类的沟通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为了理解的沟通,二是策略性的沟通。
理性的沟通的目的是理解对方,它的动机是真诚的。而策略性的沟通又被分成两种,一种是公开地使用策略,比如威胁对方必须接受某种观点,否则让他受到惩罚。这是一种胁迫性的共识,让对方害怕而被迫和你达成共识。
和威胁相对的就是奖励、收买,给对方开出一个他不能拒绝的价格,他为了钱而认同你的观点。这就是沟通类型中公开地使用策略。
除了公开地使用策略,还可以隐蔽地使用策略进行沟通。比如有意识的欺骗或者心理操纵,我们听说过比较多的,就是通过“PUA”达到所谓的共识。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是无意识的欺骗,传播者也没有意识到在欺骗对方,因为双方都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环境之中,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共识。
组织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就有这种系统的歪曲,这就是意识形态造成的对现实的虚幻认识,或者拒绝承认某种幻觉的存在。有些被统治者因为长期生活在一个系统中,接受了某些他们本不该接受的前提,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受害者反而替加害者辩护。
还有像是缺乏制度和环境的保证,单纯强调奋斗与奉献能够获得好的结果,或者强调穷人家的孩子不配拥有梦想只能找个安稳的工作做个螺丝钉,这就是一种虚幻的共识。
这些就是在哈贝马斯看来的策略性的沟通。当然,策略性的沟通是哈贝马斯反对的,他觉得沟通应该是为了获得相互理解。
《虽然只是丢了手机》
但是,仅仅做到为了理解而沟通还不够,这种沟通还必须得是有效的,所以还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交流者的表达是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达要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你不能说一个不存在的事情或虚假的事情。
第二个要求是道德上的正确性,也就是谈话内容要符合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比如我们不能去辱骂别人,进行人身攻击,用无关的私德去羞辱对手或者PUA他人。
第三个要求是真诚或者诚实,也就是说话者的言辞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真实意图,不是言不由衷或者故意欺骗对方。
这三个有效性的要求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世界。真实性对应着客观世界,即一个言说是否可以得到经验支持。道德正确性对应着社会世界,即社会的整体要求与规则。真诚性对应着主观世界,也就是言说者自己才能够接触的经验。
《华盛顿邮报》
关于沟通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上面这些原则,尤其是道德原则,又来自何方?如果不能保证这些道德原则是正义的,则个别的沟通也可能被系统的扭曲。哈贝马斯引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他认为生活世界正是沟通的语境和所有规则的来源。
这里的“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提出的概念,它原来是用来论证“科学与人的经验哪个更重要”的,生活世界是科学等理性认知之前就存在的世界,每个人都普遍享有这个世界,对它的感知先于科学的认知。但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并不是和科学相对而言,而是和“系统”相对。
所谓系统是指社会的宏观结构,主要是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无须借助语言,甚至不需要相互理解。像政治由权力控制,经济靠金钱控制,谁有权,谁有钱,谁就说了算,并且政治和经济的运行有一些默认的潜规则,并不需要取得理解与共识。
而生活世界则是依赖沟通和相互理解。因为这里面并没有通行的规则,每个人对世界的视角和认知都存在差异。只有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协商,才能够达成共识。
哈贝马斯认为商业后来使得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他也担心政治和经济的系统指令取代了生活世界中互动的交流逻辑,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比如生活、艺术世界的商业化,学术的权力化等。
哈贝马斯认为只要保证沟通的有效性,交流双方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再加上一个理想的交流环境,人与人之间,再扩展到更大的群体,是可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当然,这个结论建立在非常理想的条件之上。但是他至少证明了一点,就是在理论上,理解与共识有可能达成。
3.
交往理性与协商民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交往理性,在现实中如何实现,或者说能够有哪些应用呢?
哈贝马斯后来提出的商议民主中,进一步地发展了他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交往行动理论》所提出的以交往和沟通传播理论,并将它们用于现实的政治规范理论之中。
他所说的商议民主,也有人翻译成协商民主、商谈民主,就是建立在理性沟通与理解基础上的民主。它是对之前人们所熟悉的自由民主和共和民主的修正,或者替代。
2001年,哈贝马斯曾来中国访问,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的演讲就是《民主的三种模式》。简单来说,自由民主就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每个人只管自己,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民主的目的也是保证个人的权利,或者个人如何利用政府来实现个人权利。当然,它的问题就是有个人无集体,最后公共利益就缺乏保证。
共和民主则比较关注集体目标和集体身份认同,强调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只有保证了集体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共和主义更强调公民如何自治。共和民主的问题和自由民主的问题正好相反,就是可能过于注重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总的来说,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民主都存在一些问题,总会面临着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现代民主制都是通过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决策,这就使得公民之间的分歧与差异通过一种粗暴的方式加以消除。最后虽然达成共识或统一,但是都是基于公开的或隐蔽的策略沟通行动实现的,人们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同意。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也就是沟通、理解基础上的协商民主就可以克服前面两种传统民主制度的不足。而且他还比较乐观地认为大众媒体在理想条件下,是能够促进商议民主的。如果大家知道阿多诺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大众媒体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有多大了。
《华盛顿邮报》
2006年6月20日,哈贝马斯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56届国际传播学会(ICA)年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媒介社会中的政治传播:民主仍然具有认知维度吗?》的演讲。在其中,他重申了处于政治系统中的大众媒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促进民主的。
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自我规制的媒介系统从其社会环境获得独立。也就是媒体不能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收买,保持自治与独立。
第二个条件是匿名的受众通过意见的发表,使知情的精英话语与有做出反应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反馈。这句话听着很绕,简单来说,就是哈贝马斯把政治传播视为一个系统,认为通过传播能够使这个传播系统保持活力与自我完善,这样就能够达成各方的相互理解。
2021年,92岁的哈贝马斯应邀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的文章提出了自己新的思考。
哈贝马斯首先承认,新媒体不是传统媒体的简单扩展,而是像印刷机的发明一样,是传媒发展中的跨越。但是他认为,社交媒体不是一个媒介,而是平台,平台不是生产者。社交媒体平等且没有制约,导致碎片化与自我封闭。
所以社交媒体虽然给每个人提供了表达机会,但它并不是一个公共领域,是一个半公共半私人的领域,更像是传统的书信。它有理性沟通的潜力,但是其特点也导致它很难真正承担这个任务。
《虽然只是弄丢了手机》
他认为平台化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在于,它们无法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足够的发行量,导致它们更加依赖市场。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工作的专业化和政治化:它们从原先政治辩论的场所变为了创作和发行的协调中心。
文化消费可能会削弱公共领域的批判性,使其变为一种表演。这种表演就会带来碎片化与封闭性,不仅是消费者的自我封闭,还会导致生产者的自我封闭,意见领袖、大V们为了自己的节目和名声竞相吸引追随者的点赞,表现出某种独异性,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解释和立场进行不断地自我确证和相互确证。
尾声.
非理性与公共交流
总体来看,哈贝马斯从博士时期就一直关注理性交流问题,直到后来的商议民主理论,交流与传播的问题一直是他理论的重要基石。也可以说,交流与传播的问题是他解决很多现代社会和当代政治问题的一把钥匙。这种交流不是普通的日常交流,而是建立在严格的理性基础上的交流行动。
也正因为此,一些批评者指出他对于非商议的内容关注不够,比如承认、叙事、修辞、表演、仪式、抗议等交流行为,也在政治传播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我们不可以像他一样简单否定。
同时,他对于反公众、情感公众和多元公众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地认识。林郁沁写过一本书叫《施剑翘复仇记》,里面提到民国侠女施剑翘为父报仇,在佛堂刺杀下野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之后,形成了一个同情施剑翘的情感公众,公众通过情感被连接在一起,形成关于这个复仇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讨论,最后没有根据严格的法律条文来处罚施剑翘。
总之,许多人认为非理性并不能被简单地排除到公共交流之外,像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同情、愤怒等情绪本身也是促进问题的知晓、讨论与解决的重要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