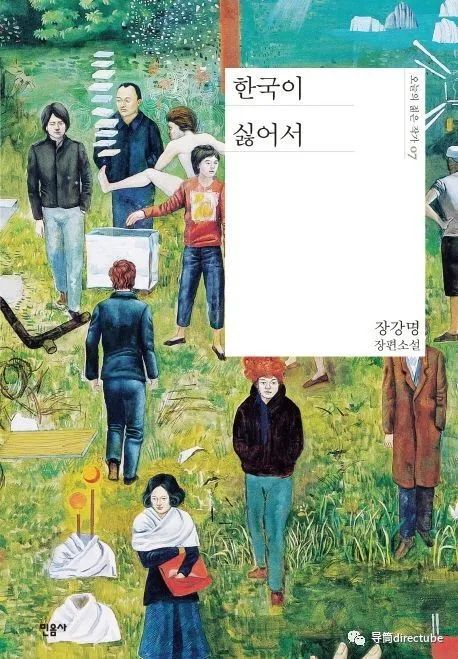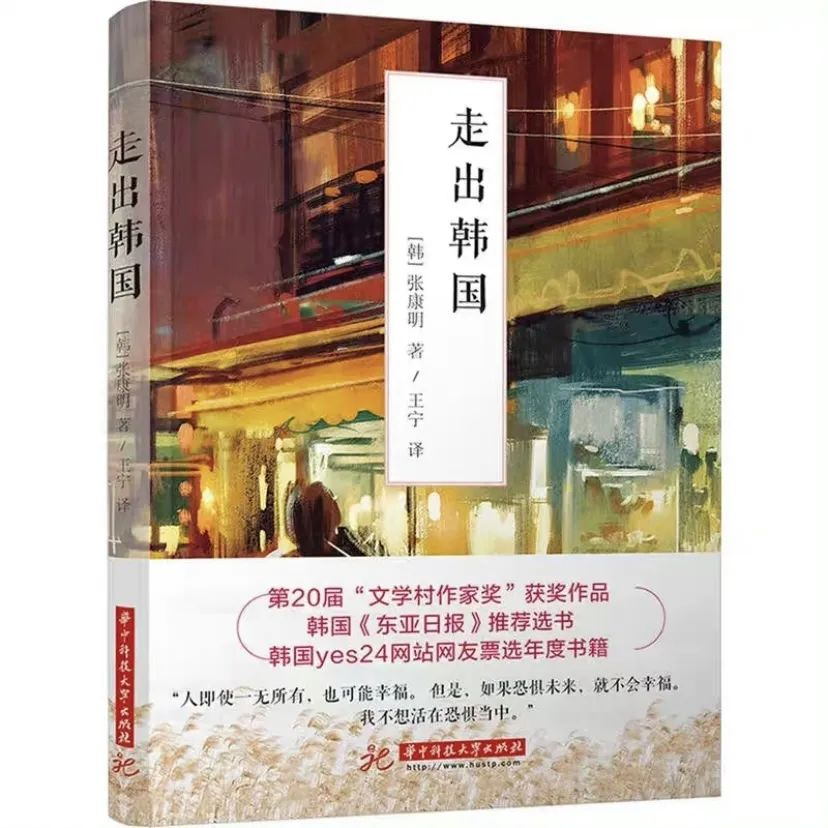张建宰执导,高我星,朱综赫的《我讨厌韩国(한국이 싫어서)》(也译作:因为讨厌韩国)将于10月4日作为釜山电影节开幕片首映。

影片根据张康明作家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20代后半的主人公桂娜(高我星 饰)抛下工作、家人、男朋友,为了寻找自己的幸福前往新西兰的故事。
桂娜觉得“讨厌韩国”,“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因此决心移民。载仁(朱综赫 饰)为了获得永久居住权而来到新西兰留学,之后和桂娜一起在澳大利亚相互依靠着生活,最终发展为恋人。
2015年出版的原著小说《走出韩国》(也曾一度译为《我讨厌韩国》,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版本也沿用了原标题《因为讨厌韩国》)曾在韩国获得第20届“文学村作家奖”,也是韩国某专业读书网站网友票选的年度书籍。
张康明,1975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延世大学工学院,曾供职于建筑公司,后在《东亚日报》从事记者工作十一年。2011年,凭借长篇小说《漂白》荣获“韩民族文学奖”,从此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严禁痴迷,EVA ROAD》获“秀林文学奖”;《网军部队》获“济州4.3和平文学奖“;《晦日,你记忆世界的方式》获”文学村作家奖“。著有长篇小说《主宰者》、系列小说《努米埃尔人》等。
韩国,从外远观,因为韩流明星、因为财团经济实力,显得光鲜亮丽、令人羡慕,但身为韩国人,从内而观,却是身处无法指望公平正义的阶级社会,苦于永无翻身之日,青年们难以生存。
挣扎着想靠自己努力生活,却怎么也看不见希望,最终只能屏弃一切的逃离,用一句话简答:「因为讨厌韩国。」
详答则是:「因为没有办法再在这裡生活。」
「5弃时代」青年放弃爱情、友情、亲情、婚姻,放弃了国家,仅为了求一个可以好好呼吸的生活。
女主人公不喜欢韩国,她也清楚的认识到,以自己的学历、家境、外型等诸般条件,如果留在韩国,未来的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她想改变命运,于是放弃了所谓的稳定现状,转而去澳大利亚寻求更幸福的未来。在那里,她经历了澳洲人的歧视和韩侨的欺生待遇,辗转于各种条件恶劣的合租屋,结交过奇葩男友和害她家产散尽的朋友,也通过努力找回了自信,最后终于成功入籍澳大利亚。
喜欢书中对于迪士尼动画片《怕冷的企鹅》的引用,如果你是只怕冷的企鹅,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像其他企鹅一样一辈子固守在南极。走下道德制高点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寻求幸福的权利。有感于作者在小说最后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出的那个“资产式幸福”和“现金流式幸福”的理论—"我突然觉得,也许幸福是种跟钱一样的东西。幸福也分’资产式幸福’和’现金流式幸福’。
有的幸福来自于对于某些事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一直存留在记忆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点点的让人觉得幸福,这是资产式幸福。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幸福资产的利率非常高,比如志明。‘我突破重重难关当上了记者’这份记忆当中,每天都会析出一些幸福感,所以他即使每天工作到很晚,即使疲惫不堪也比别人更能坚持。有的人却正好相反,他们的幸福利率很低,幸福资产几乎不产生任何利息,所以他们必须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式幸福。艾莉就是其中之一,她是靠每个瞬间活着的。"
女主角没有可以长久支取利息的“资产式幸福”,也意识到在韩国很难创造她所需要的“现金流式幸福”,所以她像那只怕冷的企鹅一样,选择离开南极,远渡重洋,为自己搏一个阳光普照椰林树影的未来。
下文选自张康明作家的小说《走出韩国》 译者为王宁老师
去澳大利亚的那天,我和志明在仁川机场正式分了手。那天,志明开着他爸的车,把我送到了机场。我家穷得要命,全家五口人,连一辆车都没有。要是没有志明,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鼓鼓囊囊的移民行李包和拉杆箱拖到机场。
志明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我爸妈坐在后面,行李包都塞进了后备厢,这一程诸多尴尬。"桂娜,累了就回来,注意身体,别光想着省钱,吃饭别对付。"这些话像保留曲目一样被我妈在后座上重复了三遍。
办理登机牌的时候,行李超重了,我只好拆开行李包,把放在最下面的几本书拿了出来。我爸脱下防风外套,把那些书像打包裹一样一层层地裹起来,抱在胸前。
"你肯定会回来的,这个我最清楚,我等你。"志明在安检口前抱着我说。我爸妈站在几步外的地方吃惊地看着这幕。
我从他怀里抽身出来,我这还没走呢,他就说这种话,真够讨厌的。"咱俩从此一刀两断,正式分手。"我边想边走进了安检口。
排队等待安检的时候,我往后瞄了一眼,只见我妈正站在玻璃窗的另一侧不停地对我挥着手。跟我的目光一相接,她赶紧开口说着什么,估计还是"累了就回来,注意身体,别光想着省钱,吃饭别对付",我爸抱着那摞用衣服包裹的书不自在地站在旁边,一脸伤感。
志明在一旁抹眼泪。
你问我为什么要离开韩国?简单说就是“因为讨厌韩国”,说长点就是“因为不想在韩国生活了”。拜托,不要因此就劈头盖脸地骂我,尽管我生长在这个国家,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可以讨厌它。这难道是什么弥天大罪吗?我现在又没煽动谁去杀韩国人或者去大使馆放火,也没发动抵制韩货的运动,甚至连面太极旗都没毁坏过。对那些声称厌恶美国的美国人和声称为日本而羞耻的日本人,不是有很多人都频频点头赞许他们三观正有良知吗?
我之所以不想在韩国生活,是因为在这个国家,我实在是个没有竞争力的人,就好像一个应该灭绝的物种。我特别怕冷,做不到为了某个目标而拼命争取,也没有半点家底等我去继承。自身条件不怎么样吧,偏偏又挑剔得要命,工作地点要离家近的,租房子要周边文化设施齐全的,找工作要利于实现自我价值的。
有关非洲草原的纪录片里不是经常出现瞪羚吗?就是总是被狮子吃掉的那种动物。每次狮子一来,肯定有一只瞪羚跑偏落单,最后落得被狮子逮住吃掉的下场。我觉得我就跟它一样,不跟群行动,一会儿喜欢这边有阴凉,一会儿又嫌那边的草不嫩,于是自己跑单帮,最终成了狮子的目标。
话说回来,虽说我是只瞪羚,可眼看着狮子来了,总不能坐以待毙,还是得拼尽全力地逃命,所以我才要离开韩国。
我也知道,相比于逃跑,奋力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这才是更体面的选择,所以呢,你让我怎么办?联合其他瞪羚小伙伴跟狮子肉搏?
在澳大利亚机场接受入境审核的时候,我来月经了。之前排队的时候我就犹豫着要不要去趟卫生间,但为了节省时间,最终还是忍着没去。生蚝一样的东西从我身体里滑了出来,到卫生间一看,内裤上已经沾了很多血。我的包里倒是有片卫生巾,可惜没有替换的内裤。我用卫生间里的纸巾最大限度地擦去了内裤上的血渍,然后把卫生巾粘在了上面,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精神压力,月经比平时来得早。其实从坐在飞机里的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十分畏怯了,因为我没听懂那句话,“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空中小姐问了三遍,最后干脆给我放下杯可乐走了。
我强忍紧张的心跳,打着腹稿,准备应对诸如“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否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等问题。没想到移民局的职员什么都没问,他只是看了看我护照上的照片,又看了看我的脸,然后毫无诚意地说了句“Thank you”,就把护照递还给了我。我接过护照走出去几步之后才想到,他应该对我说“Welcome”或者“Have a nice day”。于是我低声对自己说:“Have a nice day!”
就这样,我流着血跨越了国境。
我的行李包似乎马上就要被撑爆了,从行李转盘上往下拿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拎动,反倒差点被拽上传送带。旅行箱的滑轮也松动了,在地上滚动时我的行李包似乎马上就要被撑爆了,从行李转盘上往下拿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拎动,反倒差点被拽上传送带。旅行箱的滑轮也松动了,在地上滚动时声音大得那叫一个刺耳。
我本想从箱子里找条内裤去卫生间换上,可惜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箱子太大了,没法拿进卫生间的隔间里,又没有同行的人帮我看行李。没办法,我只能穿着被经血浸湿的内裤通过了海关。我正边走边反复练习说“Nothing to declare”,海关工作人员指着我的行李包直接问了这么一句:“Kimchi(泡菜)?No Kimchi?”
来接我的留学中介公司的夫妻已经在机场等着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当着他们两人的面从行李包里翻内裤。于是内裤最终也没换成,我就这样上了车。夫妇二人把我带到了一个临时住所,供我度过在澳大利亚的第一周。这是一栋带有小花园和车库的二层洋房,这一带都是这种红色屋顶的小洋房,看起来就像画儿一样。
“漂亮吧?你要是找不到其他住处,可以继续住在这儿,到时候租金可以给你算便宜些。”有点话痨的女人下车的时候跟我说。我的心情这才有了些许好转。
可是她并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打开了旁边的车库门。原来这个出租间是由一个大概十五平方米的车库改造而成的,里面放了书桌和床。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临时住处的日租金比一般的商务酒店都贵。
在动移民这个念头之前,我经常幻想等五十岁退休之后,就去济州岛度过余生。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用一辈子攒下的钱在济州岛买上一间旧公寓,每天规律作息,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睡觉。每天自己在家做饭,饭菜可以很简单,两三样小菜就好,但一定是自己做的。当然了,想吃炸鸡的时候也可以吃,并不用活得像修道士一样。每天吃了早饭,喝杯咖啡,看看书,然后到海边跑步。估计到时候我也没什么多余的财力去健身俱乐部,还是自己到室外做做拉伸、跑跑步吧。之后去图书馆借书,读很多书,还要学习乐器演奏。到时候时间多得是,可以学两种乐器。而且肯定能经常练习,毕竟时间充足。
另外,我还想在自家的田里种点生菜什么的,想想看,你在自己家里头给植物浇水,这种植物就会长大,然后结果实,多好。都说回乡务农不容易,那是因为得把种地当成事业来干,但自己在家种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不过是每天弯上二三十分钟的腰铲铲地罢了,这不成问题。我还要学游泳,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每天长在游泳池里,像美人鱼一样潜水。
一年回一次首尔,每次待上一个星期左右。见见家人,买些必要的东西,看看演出,会会朋友,活到六十岁就可以死了。活那么久干吗呢?这样的日子能过上十年我就知足了。静下心来想想,现在这么辛苦的工作,还不都是为了从六十岁到八十岁过得舒服点吗?可是其实越晚退休越费钱,因为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各部分都开始出问题,要去医院看病,还要接受物理治疗。而早点退休,就可以在健康的状态下享受自由生活了。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最后肯定选择自杀。我可不敢想象自己一直活到九十岁、一百岁,到时候颤颤巍巍的,站都站不稳,所以呢,八十岁的时候自杀还是六十岁的时候自杀,有什么分别呢?或者索性再提早五年退休?从四十五岁开始自在地生活,活到五十五岁就死,多美好。
我在韩国工作的时候,没有一天不抹眼泪。倒不是工作多辛苦,而是上下班的路程太艰难。你曾经在早上搭乘地铁2号线从阿岘站出发,经新道林站转车到驿三站吗?如果经历过,你就会切身体会到别管什么人性还是尊严,在生存问题面前全都是摆设。
从新道林站到舍堂站,在车厢里被挤得锁骨都疼。每次搭乘2号线的时候,我都想知道我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难不成是叛国?或者卖假保险诈骗?看着身边同样被挤的那些人,我也常想,你们又造了什么孽?
那些号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应该在早晨上班高峰时间去搭乘地铁2号线试试。从新道林到舍堂来回坐几次,他们就不会再嚷嚷什么出生率过低的屁话了。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挂在嘴边的人并不用搭乘地铁。
我当时在一家叫W综合金融的公司上班,大学毕业找工作那会儿,我去所有想去的大公司应聘都没成功,于是就开始随便投简历,最后进了这家公司。我在的时候它叫W综合金融,后来改叫W证券了。没错,就是几年前好多员工自杀的那个W证券公司。
很多朋友都问我:“你连张资格证书都没有,是怎么进到金融公司工作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选中的。不是吗?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应聘成功,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落选。会不会是老板看脸随便选的呢?
这个W综合金融说起来虽然属于金融圈,其实薪酬特别低,在业内的口碑也不好。对于有志于进入金融圈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地位也就仅仅高于互助储蓄银行吧。但是对我来说,能进这种公司工作,简直是求之不得。坦率地说,我这种人在街上一抓一大把,没一样能特别拿得出手。
总之,大学毕业以后能直接开始工作,我总算松了口气。估计就算不是这家公司,换成其他地方要我,我也会去。如果那样的话,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我从来没考虑过什么长期的职场生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待业,每个月有工资可拿。
我供职于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W综合金融和外国公司合作发行信用卡,年费高,但是可以无上限透支,因此很受有钱人的青睐。
其实这完全是骗人的,我们公司发行的信用卡是有透支额度限制的,只不过卡主本人不知道而已。如果有人突然要进行高额结算,在结算的瞬间,核准中心就会决定要不要给他结算。但并不是所有结算事宜都会报告到我们这里,对于小打小闹的交易,系统会自动给予处理通过,但是如果一个每月只花三千元的人突然要买一颗价值六万元的钻石,系统就会把信息传达给我们。此时信用卡合作商铺的人就会跟卡主解释说“系统有点慢,请稍等”,等的时间长了,当事者就会心里发慌,不是直接离开就是改刷其他信用卡。
也就是说,当系统给我们发来相应的结算请求时,我们要在五分钟之内决定要不要同意。那么怎么来判断该不该给予结算呢?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操作指南可循,整个过程非常主观,因为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即使是同一笔交易,卡主如果是无业人员,就不予通过,而如果是医生就没问题,因此,我们要调查卡主之前的还款记录中是否存在逾期还款,还要看他现在住的房子是自己买的还是租的。职业、年龄、生日、地址、上月消费记录、在哪个商铺要买什么,等等,都会自动出现在显示器上。如果商铺位于江原道的某个休闲度假村,可是卡主要买的却是黄金或者汽车,那我就做不了主了,得向上级汇报。
交易无法进行,卡主这才知道自己的信用卡是有额度限制的,于是他们就会打电话来投诉,投诉电话先由客服中心处理,客服中心处理不了的电话会转到我们部门。应对这种电话是很痛苦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会劈头盖脸地大发雷霆,质问之前明明说的是没有额度限制,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这时,我们通常会这样解释,这次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比如,“您两年前曾经有过逾期还款的记录,得过几年才能享受额度不受限的服务”。可是这种解释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有的客户会纠缠不休,有的则会破口大骂。
在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整天都浑浑噩噩的。其实就算我只是某个组织的附属品,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齿轮,我也该知道我这个齿轮是被放在哪里,怎样滚动的,这台巨大的机器又是朝哪个方向运动的。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也不知道我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总之就是一片混乱,或者应该说我根本就不想知道,我那时的心智成熟程度只相当于一个高中生的水平。
所以,这样的工作自然无趣。有人说工作很有意思,我实在不理解这句话,是说他所做的工作正是他喜欢的吗?这是什么话?我不愿意听客户投诉,也不喜欢我所在的公司,所以坐在那儿整天板着脸。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那些同事真够善良的。作为一个新员工,我应该爽朗和气,主动亲近职场的前辈们才是,可我却一言不发,非要别人先问我才肯开口。这样居然还有人肯跟我一块儿吃饭,简直太神奇了。我这样的人活脱脱就是职场中最容易被孤立的典型嘛。
不过也有一件好玩的事,当时很多艺人都用我们公司发行的信用卡,毕竟用这卡看起来有面子。我可以看到这些艺人的消费明细,只要把名字输入系统,所有个人信息都会显示出来。我在门户网站先查出这些艺人的本名,然后在公司系统里查他们的信用卡消费明细。看看这家伙,简直花钱如流水啊。XXX爱买这个品牌的奢侈品,XXX喜欢用这种化妆品, XXX在结婚前一天去了有陪酒女的KTV,XXX几天前是在情人旅馆过夜的。这些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他买这干什么?难不成是有女朋友了?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三年多,到后来每天只想着早点离开。
首先是工作内容没什么技术含量,靠这个不可能升职。如果我自己喜欢,辛苦点也无所谓,偏偏我又不喜欢,而且工资也不高。
可那毕竟是个规模不小的公司,再加上有的同事在核准中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转调到别的部门去了,所以我也寄希望于此,工作了两年之后,跟上司提出换部门,上司口头上答应了,可是过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于是我明白了光说是没用的。
当时我是跟组长说的,只要求换部门,也没说想去哪个部门。其实,我并不知道其他部门都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当时组长说:“桂娜,对于女孩来说,核准中心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很容易就能把你调去做销售,你想去吗?”
我当然不愿意,我本来一遇到陌生人就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怎么做销售?听我说不愿意,组长说:“你再等等,等人事部或者行政部有了空缺,我第一个推荐你。”
可惜这只是空头支票,后来我要辞职的时候,组长单独请我吃烤肉,让我再坚持两个月,因为下属毫无缘由的辞职会影响他的工作绩效,所以他才希望我坚持到绩效考核之后再辞职。其实再坚持两个月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当时的我心里很不舒服,凭什么?我的要求你从来不答应,现在反倒让我成全你?所以我就冷冷地说了句“我不愿意”,然后就走人了。现在想想,当时真应该再坚持两三个月,毕竟这对他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
其实组长也为我做了件事情,因为我总是抱怨,所以他给我换了一个班组。当时我们分白班组和晚班组,上晚班身体很累,但也有相应的好处。首先,晚上的交易量不多,工作相对轻松,而且上晚班的时候不用穿工作服,感觉特别好,于是我就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去上班。上晚班的时候闲暇时间很多,真应该自学个会计师什么的。可惜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会计师,迟钝得要命。
晚班还有一样好处,从小到大我都跟姐姐慧娜和妹妹艺娜住一个房间,三个大姑娘共用一个房间,这可不是一般的不方便。可是上晚班后,白天我就可以一个人睡了,这也不错。而且无论去银行办事还是买东西,时间都很方便,好处多多。
对了,还有一样,上白班的时候,中午都要跟同事们一帮人去吃午饭,每天不是泡菜汤就是酱汤,腻味得要命,可是再不愿意也得随大流。就在我对这几种汤已经絮烦到极点的时候,正好换到了晚班组,这样我就可以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可以从家里带便当,也可以叫外卖送到公司来。
但是上晚班最不好的一点在于,金融公司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意志培训,就是喊口号表决心的那种。这些培训都在白天进行,每当我上完晚班,白天又要去接受培训的时候,总恨不能有辆车突然冲到人行道上来,把我撞个断胳膊断腿,这样我就可以休息了。
也正是在一次培训结束之后聚餐的时候,我突然决定以后不去济州岛了,而是要移民。
在核准中心工作的大多是女员工,核准中心一共有二十个人,其中十五六个是女的。可谁知道这天聚餐的时候,组长满嘴黄段子,估计是想在下属面前表现得更平易近人一些,因为就在那之前的几个小时,外聘讲师让我们画表格来表示对同事的信任程度,结果显示组长是所有下属都不信任的人。他肯定也觉得特别没面子。
组长在调来核准中心之前,负责领导那些做销售的中年大妈。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了那么多的黄段子,难道是那些做销售的大妈喜好这一口?可对我们来说,这无异于性骚扰,我们都犹豫着要不要说点什么。现场气氛很尴尬,再加上不愿意看组长一个人耍猴,于是第一轮早早结束,第二轮来到了练歌房。
寥寥可数的几个男员工之一拿着麦克风唱起了《告解》。
“这歌词像不像一个和有夫之妇搞外遇的男人跟人家的丈夫求饶?‘请宽恕我明知道这个位置不属于我,却依然想拥有她’,‘请宽恕我,我愿意接受惩罚’……”
坐在我旁边的后辈表示不理解男人们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听了她的话,我嘴里的啤酒一下子喷了出来。接下来,组长唱了《Bingo》,这是首大叔们都喜欢的歌。比我入职早的姐姐们都起身走到前面给组长伴舞助兴。
“以赤诚之心!从头再来!愿望必将达成!”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上台去助兴,但最后还是坐着没动。不过坐归坐,总不能假装听不见组长唱歌,于是我一边摇着铃鼓,一边跟着唱。
“我热爱脚下的土地,从未想过移民!”
我似乎明白年轻男人们为什么会那么痴迷于《告解》的歌词了,漂亮女人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们肯定很受挫,在这种挫败感的折磨下,他们战战兢兢,最后终于选择了自恋。这总好过那些心理扭曲的男人骂女人虚荣,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吧。
至于中年男人为什么都喜欢唱《Bingo》,是不是因为他们活得太累呢?每个人都觉得活在这个国家很累,心里都暗暗盘算着移民,可是又不想承认,于是就用这首歌来催眠自己,说“事在人为”,说“活得太轻松反倒没意思”。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就不可以移民呢?那一瞬间,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
几年之后,我在澳大利亚听到了创作并演唱《Bingo》这首歌的那个歌手的消息。当时我跟另外两个女孩共住一个房间,澳大利亚没有宿舍和开间公寓。韩国留学生通常都会租个大房子,十个人一块住,每个房间住三个人,这叫作“合租鸡笼”。
“桂娜姐,你听说了吗?Turtle Man死了。”
趴在我旁边床上用笔记本电脑上网的女孩抬起头来说。
“Turtle Man?谁呀?”我问。
“Turtle Man,就是那首歌,‘Oh Yeah,又是我!心情好,高歌一曲,一二三四!’”
“这是《Bingo》,唱这歌的人叫Turtle Man吗?不是叫乌龟吗?”另一个女孩抬起头来插话道。
“乌龟是组合的名字,组合里的男主唱是Turtle Man。反正就是那个Turtle Man死了。”
“怎么死的?”我和另一个女孩同时问道。
见成功吸引了我们两个的注意,笔记本电脑的主人很兴奋,有板有眼地复述起刚看过的新闻。比如,Turtle Man因为心肌梗死猝死在自己家中,之前他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而生活窘迫,以及他和经纪公司因为经济问题产生了矛盾,后来自己成立了演艺公司,可惜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最后只好给其他艺人做助理,等等。
“他那时候的歌那么充满希望……”睡在最外侧床上的女孩觉得有些荒唐。
中间床上的女孩继续说着Turtle Man的轶事,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Bingo》的歌词,那首歌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在我生命的最后瞬间,希望我依然带着笑容。”我很想知道Turtle Man在最后的瞬间是否含笑闭眼,恐怕不是……
当时,和Turtle Man的死讯一样让我震惊的还有一则新闻,那就是W证券公司员工的自杀事件。其中一个人留下这样一份遗书:“董事长,您不能这样,请把我客户的钱还给他们。”
W集团的经营陷入困境,于是给员工下派任务量,让他们兜售子公司的企业债券和本票,并保证这些都是安全没风险的。安全个屁,没过几个月,那些公司就都倒闭了。这等于让员工去诈骗,简直是耍流氓。
这则新闻之所以让我觉得很震惊,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还留在韩国,还在W综合金融公司上班,那么我很可能也卖了那些东西。W综合金融的信用卡部门取消了,因为当初与之合作的那家外国信用卡公司自己进驻了韩国市场,因此公司的名字也改成了W证券。听说之前信用卡部门的员工都转做了证券销售。
如果我现在依然留在韩国,我是否能抗拒这个巨大的齿轮呢?我想,恐怕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