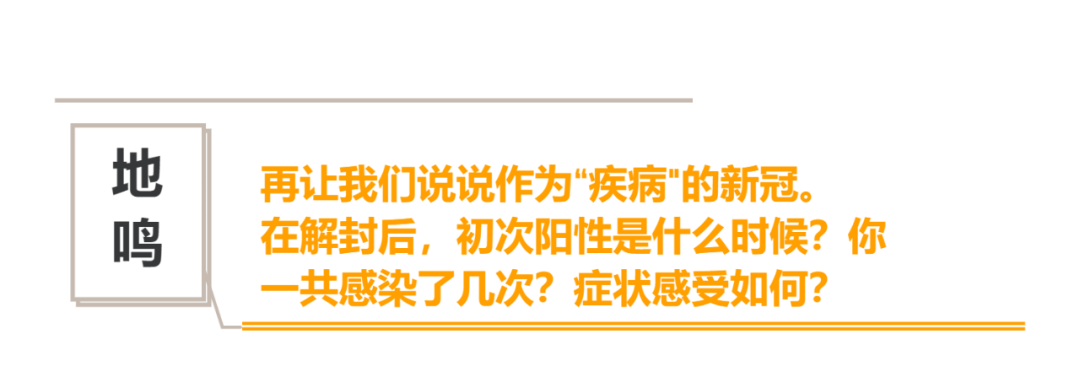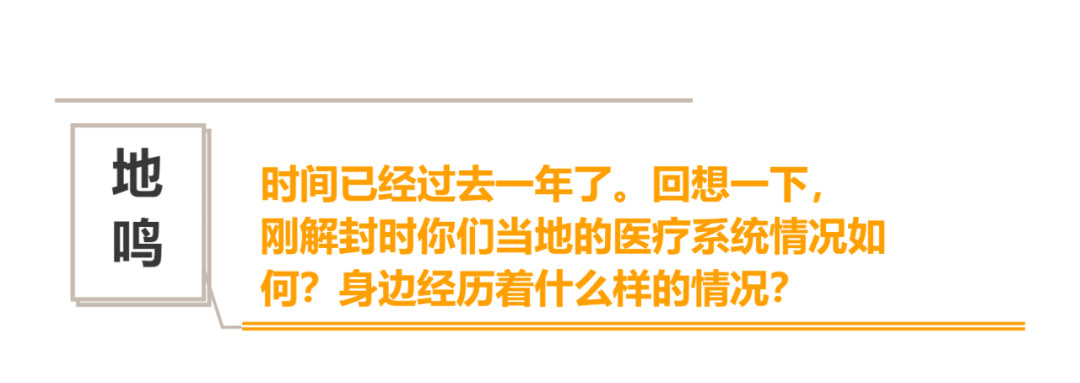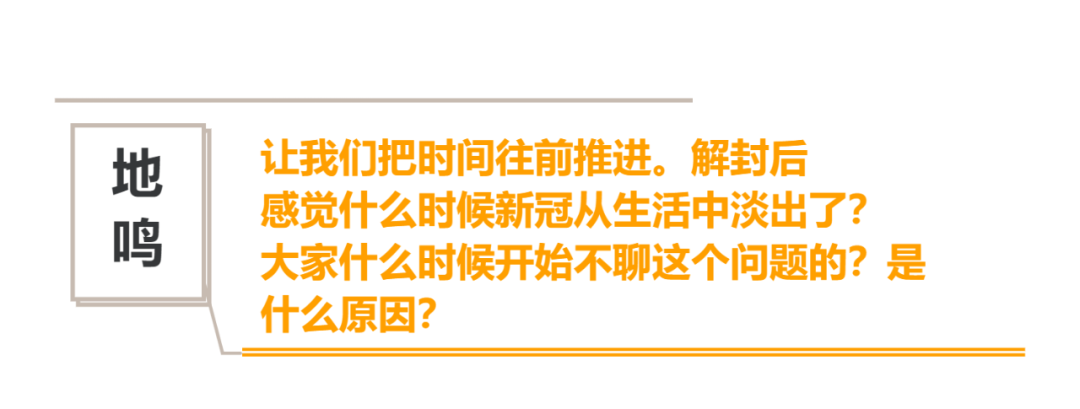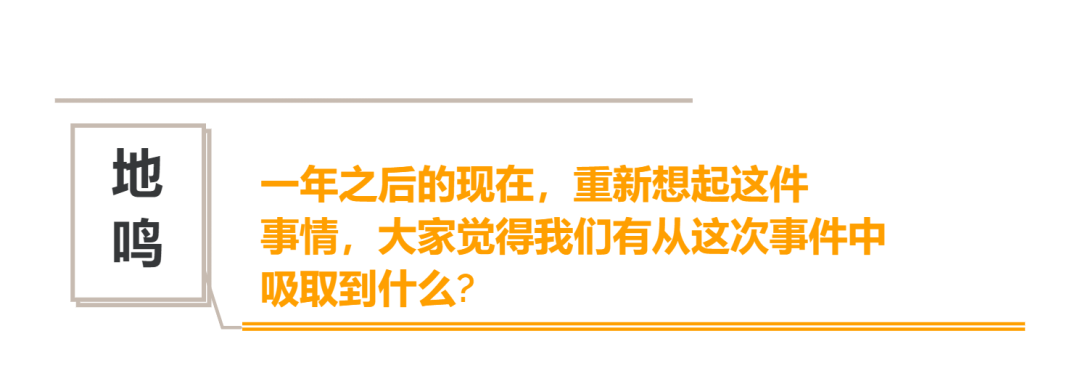编辑:芥芥子、虾
主持:地鸣
与谈:羊堡、奶昔、堪、小、木雁、小林
插图:地鸣、陶然、羊堡
引言
在去年刚刚解封的时刻,我们做了一期推文:

在当时,我们采访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大学生,试图连接个体的叙述,看见各地,看见彼此,加深对他者和时代的理解。
距离政策转弯的日子,已经过去一年了。这新的一年的日子里,年轻人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是有了新的开始,还是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里徘徊?回想起当时,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与周遭的一些年轻人又进行了一场跨越空间的对谈,回忆过去的一年,谈谈解封之后的生活,谈谈过去的与当下的。以下是我们的对谈。
与谈者
羊堡
奶昔
木雁
小
堪
小林
木雁:虽然只过去了一年,但是又感觉好像过去好久好久了。有时候在一些偏僻的地方路过一个还没被拆毁的核酸亭,有时候偶尔看到戴口罩的人,都会闪回到封着的日子。会想起很多那时候的事情,感觉记忆还是很清晰的,虽然不好讲述出来,但是都记得那些片段和故事。
记忆 图源:地鸣
小: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奶昔:我的感觉,说是恍如隔世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我确实觉得过去一年的生活密度比过去的三年都高太多了。重获行走自由的感觉真好,因而也快忘了生理与心理双重被囚禁的滋味。现在提起“新冠”这个词,我居然都没什么反应,不管是愤怒也好恐惧也好,真的都会慢慢消失。
木雁:听你说的,会想一些作为词语的新冠,和作为一个事件的新冠之间的区别。
小:我从作为一个词语的角度说说。作为一个词语,作为一个与这个词语的所指深刻交互过的人,对于它的语义的变化史也有很深的体验。一开始它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词,背后是人类对于瘟疫忽然降临的恐惧以及对此毫无抗击之力的整体的无力感。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病,比感冒要严重一些的疾病。当然,它又像是一个开关,迅速连接到过去那三年,连接到封控、和平年代的饥饿、火灾、反抗……但是可能我们在讨论具体的事件中就会讨论具体的事件,而不一定会使用新冠这个词了。
记忆 作者:陶然
奶昔:这段时间常看到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想起最终没能走出新冠的普通人的故事的时候,对我震动还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是对那些事件本身的触动,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遗忘得这么快感到惊讶。
小林:对我来说,现在的新冠,更像是一个符号,是记录了生活被彻底转向的一个路牌。当再提起它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哦,我已经处在后新冠的时代了,似乎现在的一切都和那几年有一些联系但又没有那么明显。
木雁:作为词语、事件、符号。
羊堡:我想谈谈时间。每次和朋友们提起新冠,一开始说“新冠”——然后说“那段时间”,好像不知道该如何界定那段时间,具体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有时候我们也说——“被管控的时期”。跟着就是大家发出的一声声叹息,最经常出现的感觉是:那时候到底是怎么过的,新冠居然过去了吗?不敢说一切真的结束了,而是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卷土重来。有一种持续的不安感,但因为经历了地狱般的时期,又觉得卷土重来是一定的。
木雁:词语、事件、符号和时间。
堪:我的体验的话……现在聊起这个话题,还是会很痛,需要深呼吸几次才能继续聊。
奶昔:还有痛苦。
堪:嗯……是的。会想起我彻底被那个时期改变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被植入的恐惧和易怒,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现在仍然对我发生非常大的影响。成都的冬天空气很差且湿冷,我过去在成都的冬天一直有出门戴口罩的习惯,我的工作其实也需要我在很多时候戴口罩,以及在一些时候口罩也能缓解一点点我的性别焦虑⋯⋯但是在解封之后,除了两三次发烧咳嗽时出门戴过几天口罩,其余时候我再也没有戴过,再也没有办法去戴上口罩。
记忆 CC BY 4.0
羊堡:我也想说说关于口罩其他的感觉!想到,年中的时候去曼谷,三年后的第一次——以为再也无法到达的地方,和伙伴搭乘BTS的时候,很多人戴着口罩,我们非常惊讶地说“为什么这里并不强制戴口罩,却还要戴口罩呢?”
三年的封闭,眼前的苦难应接不暇,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脱下口罩,获得喘息的、抵抗的瞬间。过去三年里,我们在几乎无人的影院里、街道上、公园里偷偷摘下口罩。在那个环境,违反强制定下的规则是一种反抗。但就在对新的环境感到奇怪的同时,我意识到这三年我对其他地区的疫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当我觉得戴口罩就意味着不自由的时候——我同时意识到我思维中被塑造的,也可能是惯性的,那个缝隙,那个正义和非正义的模糊的缝隙。
木雁:我觉得口罩也成为一种符号了。
羊堡:是的,但这个符号的意义也是复杂的,并不单纯指代疾病。当我在反抗时,我在反抗什么?我希望自己可以更灵动地反抗,但在随时陷入极端的环境中,随机应变是需要消耗精力的,它需要分辨,需要思考,在那个思考的时间被一刀切吞掉的阶段——漩涡更容易将我吞噬,或许已经被吞噬过无数次。甚至反省也成了滞后的。
我怕我无意识中也把人当成了靶子——口罩在某种场景中,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人们能选择的不多的方式,而口罩在被掌控的语言中又成了什么?七八年前雾霾被讨论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围在一起看柴静的纪录片,我长时间戴着N95口罩,提醒家人佩戴,一天下来口罩都是黑色。那时候,我痛恨戴着口罩的难以呼吸,事情居然成了这样,它看上去不会变好。口罩用来防止呼吸道疾病加重,防止颗粒物进入,我们总是不得已的。
现在,一种象征压住了另一种,新的事情强有力地压住我们,我们总在面对眼前的、数不尽的苦难。它真的层出不穷。在这样困难的互相驳斥的语境中,作为一个行动艰难的反抗者——有时候也忘记了,每个人的境况和动机并不相同。不同的反抗方式可能会经过同一个位置。在当时,有基础疾病的人就是该被更关注的,不同语境/国家中的人们有他们的特殊处境,这是需要被留意的。它封闭,它放开,无视所有人,让人们互相攻击,想让我们说极端的罔顾个体生命的语言——我不愿意。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公平和不公平的尺度难以把握,有人只是想把自己能赋予的意义夺回来一些。
堪:除了口罩,我还想说另一个点,关于手机。现在的我,已经不再习惯不带手机出门。
木雁:疫情让我们与手机绑定的程度明显更深了,已经陷入到了离不开手机的新时代里。
记忆 图源:地鸣
堪:是的。在19年之前,大多时候我都会这样做;我现在没办法再像过去一样和小区、医院、公园或者其它任何地方的安保人员轻松地聊天,关心ta们在下班后是什么样子,和ta们分享当天买到的食物,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容易的连结,在跟ta们接近时我只会和过安检时、遭受临时手机检查时一样自动进入极易被激惹的对抗姿态⋯⋯还是会在提到时小心避开“疫情”“阳”这样曾在宣传中被大规模使用的词,在提到“感染”“核酸”时还是会。一直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和所有人所遭受和承受的,同时又有太多语词和场景会让我们闪回到那种绝望、无力和愤怒的感受当中,它们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出现,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提醒,那些日子和所有的这一切从未离我们远去。
羊堡:去年十二月底感染过一次。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发烧头痛到难以忍受,今年也生了更多病,不知道是否是感染新冠,也不再去确认,自我感觉是感染了新冠之后免疫力下降,以前比较容易过去的感冒症状也更严重了。
堪:去年十二月初连续高热了几天,浑身疼痛,咳嗽了一周,被激发牙龈炎,之后又嗜睡了两周。自己测新冠抗原是阳性。强迫自己吃东西和喝糖盐水,每天除了吃饭以外都完全在床上度过。之后也有发热或头痛或者睑板炎耳道炎症之类的情况,但是没有再做过病原检测。比较严重的一次是今年五月,也是连续高热浑身疼了三四天。
记忆 图源:地鸣
奶昔: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三次左右。第一次就是圣诞节前后——最大规模感染的那次;然后是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很难受,烧到37.5左右(算低烧吧哈哈),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还吐了一次,然后头特别疼,打电话给妈妈诉苦。过了一周我的室友说他测出来是阳了,我感觉那次就应该是感染了。
还有一次是七八月份,我的室友病了一整周,也是测出来阳性。我测出来没有,但是也有流涕咳嗽之类的轻微感冒症状,也许是因为浓度太低了。
在第一次放开之前就一直在说首次感染大概三个月的保护期,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挺正常的,周围也陆陆续续有听到人说二阳的事。我自己的二阳的感染症状就是肠胃不适,上吐下泻的,第一次当天烧到38.5,然后第二天就退烧了。
小林:我可以明确的有两次,用试剂测过的,但大大小小的感冒倒是有个几次;初次阳性是在去年12月,在那之后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了,症状较轻,头疼流涕了几天后就恢复了。
木雁:我要比大家少一些,只有刚解封之后,十二月份的时候感染过一次,之后似乎没有再次阳性过。但周围的朋友在今年以来很多听说有再次阳性的。五月份的时候,两个室友再次阳了,听其中一个人讲症状依然比较重,依然发了高烧,十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室友第三次阳了。想到这两天,我的另一个室友感染了最近流行的肺炎,他也形容自己“阳了”,感觉到一些词语就是这样时刻复活着。
小:我也比较幸运,应该是一次。初阳是去年圣诞期间。但是即使是在症状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我用试纸测出来也是阴性。我的重症应该是两天到三天,我记得最难受的那天在外地,当天起不来床,发烧了,但是当天要赶高铁,在高铁站几乎站不起来,只能勉强蹲在椅子旁边,吃了一点点粥就再也吃不进东西。然后就躺了两天,第三天就好一些了。主要吃布洛芬,当时还有一些备货。
新冠后大概一个月都没办法做剧烈运动,呼吸比较短促,身体虚弱。后面就基本恢复了感染前的状态,虽然有脑雾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本来就脑雾,分不太清了。
堪:当时还在医院里打白工,整体感受是一片混乱,感觉有点幻灭:过去三年无处不在的都在试着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在努力为这一天做准备而不得不被迫着“牺牲”我们的生活、语言、本应和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或者是朋友本身⋯⋯然而当我们为之准备的“这一天”到来时,却发现仍然没有任何人做好了准备。
奶昔:想起来了,当时全国有很多医院都处于类似的情况里,很多医学生、规培生都面临着相同超负荷的情况。
堪:是的。医院尝试让更多学生继续留下打白工,却连“防护物资”和药品都无法供应,需要学生和病人自行筹措。每到一批药品就被“消息比较灵通”的医生在半小时内全部开完,医院的抗原检测包也依赖和大家一样的、价格按分钟变动的个人采购渠道。在平日和过去三年中存在感无比巨大的东西突然销声匿迹,留下的空隙再次被大家用自组织的互助群聊、在线表格、志愿劳动以及亲友之间的互助所填满。
我发热第一天的布洛芬是一个朋友小心藏在化妆品包装中寄给我的——害怕走投无路、无法获得药品的运递人员会直接拆开药品的包装;帮好几个朋友在有人临时做起“拼团”的规培群聊中代购了抗原检测包;替在北京旅游,买不到药品甚至电解质饮料、找不到住处的朋友联系可能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参与药品互助的在线统计⋯⋯好像在那一两周里,除了吃饭每天睡很多觉以外,所有的时间都是缩在狭小的房间里,抱着手机在一个个表格和聊天窗口里穿梭,和朋友聊天、为朋友亲戚和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用药咨询、做各种各样的统计和资源链接⋯⋯
木雁:虽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也对当时医院的情况记忆犹新。突然放开之后,到十二月底的时候每天都在听妈妈讲,家乡县里的医院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包括过道上都塞满了病床,站满了人,那时听妈妈说,医院里收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有不同程度的肺部感染,没有熟人根本不会收,没有床位,都会让人回去等着,医院里其他科室的人,甚至包括妇产科的,都来支持新冠病人的工作。
奶昔:我再补充一些我家里的亲身情况。我外公是肺癌中晚期患者,所以那时候受到的影响其实非常大,他是去年八月份确诊的,一直在试用新药物,效果还不错,本来控制得挺好的。但是在12月初那段时间,因为医院特别乱,新冠感染病例最多的就在那个地方,治疗也是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木雁:当时外婆也新冠阳了,一直好不了,后面做CT检查转成了肺炎,好在最终熬了过来。爷爷会每年统计他们单位去世的人,过年的时候,他表示,今年开年走的老人特别多,是往年的好多倍。想起妈妈也说,那段日子去世的中老年人很多,大都是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火葬场生意都忙不过来,原来都是上午运转,那段日子改成了24小时不停的运转。
记忆 图源:地鸣
羊堡:奶奶家在村子里,当时每天都有哀乐响起。
木雁:城市里和县城,乃至和农村里的面临的情况差别还是蛮大的。
奶昔:我外公就住在乡下,我们城里主要都是在圣诞节前后感染的,他在乡下等到了元旦才感染,刚好错开了一周时间,其实医疗系统相对宽裕一些了已经。不过人手还是短缺,他之前没有接种疫苗,医生不确定说会不会对肺癌有负面影响所以也不敢给家属建议,因此第一次感染相当严重,本来身体就虚弱,直接烧到昏迷了。后来外公送去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床位,就是在人挤人的过道里输液,就这么在轮椅上过了两三个晚上。后来差不多过了一周之后病情有所缓解,但从那之后,他就需要依赖轮椅才能出行,记忆力也严重衰退。
羊堡:我再说说在城市里的感觉——才解封的时候在武汉,感觉是完全没有缓冲的时间,街上的人很少,医院人很多,去了以前李医生所在的医院,急救车的声音依旧不断。感觉非常恍惚。大街上的药房买不到布洛芬和体温计,黄桃罐头被抢购一空。整个城市都病倒了,但没有任何提前的提醒购置,分配足够的药品,只是突然的一句话:新冠就和感冒一样,全靠身边的朋友家人们互助。
小林:其实说刚解封的时候,对我来说更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时刻。刚解封时的医疗状况我其实也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刚解封迎来一波大规模感染,那时提前备好了一些退烧药,后来不用去做核酸了,更减少了外出,感染后也是居家隔离,病好了以后似乎也没有太关注医疗方面的内容了,印象最深的是刚解封那会布洛芬和感冒药一票难求,都是靠家里寄给我。
小:我其实都不太清楚……当时我人在城市里面,那段时间我几乎不出门,不太清楚当地的情况,也不太清楚家乡的情况。但我有近亲是因为新冠引发的心肌炎去世的。
小:非常快,无论是骂声(骂那些年轻人)还是描述症状的声音,顿时消失了,就和封控的退场一样快速而猝不及防。
记忆 图源:地鸣
木雁:我也感觉过了春天之后,疫情就迅速地从生活中退场了——从各个场景之中。但不再聊的时间可能更早吧,一方面是解封后事件本身的报道更少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急切的想开启新生活的意愿。年中的时候二阳一度上了新闻,但热度其实也并不是太高,再后来,基本就看不到新冠的新闻内容了。
奶昔:是的,在周围有人开始二阳的时候话题稍微有点起来的意思。
羊堡:回想起来真是恐怖,我其实完全想不起来是什么节点。解封的一开始我还处于一种惊讶的感觉中,就像是溺水还没有缓过来,也不知道如何缓过来,不想去任何地方,在管控期间梦寐以求的旅行地,在解封的一开始,变得不敢触碰。好像一个被禁足太久的人不知道如何移动——和朋友打电话时,她也有这样的感受。
2023的新年 图源:羊堡
堪:可能是大家有太多的创伤和伤痛和那个话题、那段时间有关。对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来讲,比起自然的淡出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避开。但是仍然有太多东西会不断地、一遍又一遍提醒我们:街边的废弃核酸检测亭、墙上未被拆下的标语、从身边消失的人们、路上行人的口罩、或是每一个吵过架的地铁站和路口⋯⋯
木雁:我又想起来,下半年来网上也陆续看到一些清理旧时代相关标语的通告,以及清理各个商店还贴在门口的告示的要求,或者清理当时的宣传画,核酸亭之类的消息。好像从上到下,都被一种刻意忘记的氛围所主导了。雪是一点点褪去的,新冠是一点点被淡出的。
奶昔:可能也有人试图在刻意冷化,乃至回避这个话题。
堪:是。这种“淡出”同时也是在某种“遗忘”的命令下发生的,就如同之前那些讯息和信号在同样的命令下侵入我们生活的每一处一样。是的,我们的生活仍然在继续“向前”,也有新的事情在不断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继续”的方式和这一切发生之前没有任何不同,不意味着所有的“我们”都还在“向前”——我感到我身上的一些部分已经被撕扯下来,永远停留在了那段时期,和其它部分一起“向前”的,只是被撕扯后重新长出的狰狞疤痕。更何况,还有些整个人都还在被力量捆绑着停留在某处的朋友,我想念ta们,想抱住ta们,可是ta们在哪里呢?
小:有些东西已经作为创伤烙印在我们的身体上了,等到时机出现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会复苏起来。我有一种感觉,即人们,至少和我一样的人们,没有忘记,可能忘记了一些东西,但是不会完全忘记。
小林:我再补充一个,工作原因,新冠后接触到还是会有很多的案件和新冠有关,比如说商家因为口罩试剂的问题产生纠纷,因为新冠出现了大量的赤字,纠纷索赔的案件数量激增等等,会时不时让我重新想起来那些发生过的。
奶昔:又想到去港澳旅游的时候。我在深圳,之前那时不是一直封关着,一种物理上的隔离在生活中提醒着它的存在,今年终于松动了。我八月过关的时候去港澳的申报码查验已经变得挺松的,我回来的时候甚至因为人太多(我坐的最后一班回落马洲的地铁),工作人员直接示意我不要过安检了,往前走就行。
木雁:今年10月底去香港的时候,过海关还要扫健康申报的黑码,但是11月初的时候,已经彻底不再需要这个东西了。
羊堡:香港变得近在眼前,终于通关的时候,怎么都兴奋不起来。一开始想的也不是清算——那这几年到底算什么?谁来负责?不是愤怒的心情,只是非常无力,非常疲乏。看着有一些朋友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很为她们开心,大家报复性地感受过去不被允许的,再也不想围坐在一起细数我们在那时候感受到的疼痛。谁都知道一说起来就无穷无尽。我也慢慢地想起医生不再全身发抖,也渐渐感觉到耻辱柱上的姓名早已满得超出我能记住的,感觉到自己能力有限,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又被带进自己的生活中,可能也是从一次出国旅行吧,管控三年让我思考问题有时候非黑即白,而去到另一个地方,感觉到从多元的世界中经过的轻松的感觉。我们互相知道创伤在我们的身体里,那是我们共有的,不提可能也是一种心知肚明吧,不提也是我们还有现在的生活需要经历。
奶昔:经济问题肯定是绕不开了,年纪越大越会被拉扯到现实问题中去,也没有疫情这种例外状态作为转移痛苦的表面矛盾了。我体感本土的新闻讨论度越来越小了,大家投入奶头乐的时间越来越多。不过往好处说,“你最近去哪玩了”这个消失一年的话题也回来了。我今年去了十几个城市,放去年真是想都不敢想,几乎是以一种流窜的姿态在各地奔波,很狼狈但也很自由。
记忆 图源:羊堡
木雁:我觉得,今年更多的在聊经济和工作吧。刚解封带来的经济转暖的乐观好像没有被现实印证。周围被裁员的故事发生了很多。最近的就听到了三个——一个某互联网公司写代码的朋友,年初被裁员,找了半年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在新能源领域某公司当工程师的朋友最近公司效益也急剧下滑,工厂停产,给他们开出了长达半年的假,但是没有工资;
还有某次,是路上听到一个滴滴司机讲的自己的故事,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10年进的某大厂,辗转深圳和北京,曾达到过五万月薪——他讲到,疫情三年都过去了,想着没事了,结果今年年初公司却裁员上千人,把他裁掉了,现在仍背着房贷,刚出来开了两个月滴滴,才晓得生活如此艰难。
小林:感觉聊得多的除了就业形势严峻、消费降级等等,还有最近的巴以冲突吧
奶昔:今年的地区冲突好多啊……多少让人感觉不安。
木雁:是的。内在的经济下行,加上今年外界的战争冲突,可以说是两个很能引发人焦虑的因素了。世界真的在变好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年来,前方并没有一个乐观美好的未来等待着我们,只有一团迷雾。
羊堡:我和朋友也普遍会聊到失业问题,经济下行,悲惨世界里数不尽的悲惨故事,但今年感觉也总和朋友们聊到自我关怀,聊到更细节的情感关系的建立和处理,这种思考变得更多了。还有从小事情再次建立起生活的可能性,今年也是意识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的一年。朋友们做的活动类型更多了!可以来回走动。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感受到一些在贫穷中探索另外的生活的可能性,旅行目的地也更多偏向远离城市,一些更自然的目的地了。
小:今年我自己主要关注的首先是解封后遭到算账的人的状况,还有其他的身心障碍、社群的建立和社群的暴力等等,前段时间我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有没有新冠和封控,我应该都还是会走到这里,封控更像是一种忽然降临的障碍,对于它的关注对我来说始终是暂时的。然后今年也算是逐渐摸索到自己的方向的线索。
小林:在我看来当我们意识到群体免疫是必然的时候,就应当转向了,至于为什么停滞了这么久,我想原因见仁见智。
奶昔:我觉得像在国外,或者说境外吧,他们比我们更早的进入所谓的post-covid时代,然后有了不少相关的文艺作品,无论是反思性的也好,记录自己期间感受的也好,这些都有,港澳地区也会有很多,像今年金马最佳影片提名就有那个讲SARS的《疫起》。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最大的公共事件的亲历者,而且中国应该说在社会生活上受到新冠的影响是最大的国家,也许没有之一,我们哪怕连情绪化的作品都很少见到。
木雁:在解封一年后,这两天北方再次出现的呼吸道疾病流行和儿童肺炎聚集病例增加其实提醒我们,历史没有走远。那种最高主权构筑的例外状态下所作出的行为,封控,隔离,物资限制,大数据,密接连坐所造成的阴霾,不会真正远去。
羊堡:不知道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反而在一年后,我又察觉到更多各种身份在管控中被挪用,被他们当靶子的做法,想起很多,比如老年人,表面上是“封控是为你好”,实则也是随时可以被放弃的,不管是封控还是放开,人们永远遭殃。
小:我也不确定这个“我们”是指?如果是指的他们,我完全不抱任何“吸取经验”的期望。如果指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我觉得我也不确定是否吸取到经验和教训,我只能说我感受到这件事对很多人的伤害,所谓的教训它好像有一个指向性,我不确定。
羊堡:是的。一种共同的语言容易让人们忘记在其中更加弱势的人的遭遇,而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用”他的“语言去攻击那套语言的。那我只能提醒自己:一件事情的光谱是可以很宽的,我希望可以在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中创造可以表达更多想法的空间,总而言之,就是连最细微的地方,都想要留意到,和“他们的”语言不相同的语言。又想到去东南亚的时候,看着口罩在这里和另外一个地方的象征意义完全不同:自我保护工具/权力的具象表现,可能也想去多了解一下疫情期间别国发生了什么吧。不要让蚕食我的也成了我的安全区,要继续有勇气去面对不能被概括的困难的现实吧。另外,不要放弃记录,呜呜,你的现实你所经历的都是重要的。
奶昔:虽然我自己是变得忙起来了,能花在关心外部的时间在变少。但是今年经济下滑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比去年的长期封控对人带来的影响小多少, 见到太多同龄人在家里蹲了……我觉得减少对外界关心不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觉得经过去年年底那样草率的、反复无常的、无理无据的政策变化之后,大家都或多或少会对宏观的叙事感到厌烦,这也能理解。
小林:对我来说,新冠和我自身生活还是紧密相连的,新冠后我从一个无业的毕业游民变成了打工人,实话说有些怀念那个一切停滞不前的时间段,我找到了爱情,我们也度过了一段灾难中相互扶持的蜗居生活,那种全世界都在停滞中而你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呆在一块的感觉有一种安心感,但事实上生活在向前,我们也不可能一直脱产,现在的生活节奏无疑是更合理更有未来的,但末世情结似乎从未逃离于我的感情观里。
木雁:感觉今年以来周围朋友向内的倾向更加明显。一种是对经济的焦虑所造成的,更加关注于自己的生存,以及眼前所能得到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在反复被疫情和封控折磨的三年过去后,有了一种更多的过好自己小生活的渴望,希望去旅游,希望去养一些植物和猫猫,希望去见见朋友,这些更加自我的需求,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注意到,这也是这一年来一个最大的感觉。
羊堡:情绪,身体状况,与人的连接也是重要又重要的!救人先救己,照顾自己没有错!感觉今年自己可以理解的状况更多了,不再随便说别人不关心政治岁月静好了!也更细心地去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通过一些自我训练来为自己声张正义,抵抗不公咯。
小:我有种补偿式出走的感觉,但是国内其实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甚至出国也有种伤感萦绕着我,不存在一个更好的中国等待着我。这让我伤感,而且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一年我真正接受了我自己可能迟早会成为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上的流民。它导向一种虚无,而到现在,12月,一整年过去了,人活着就会重建,我还算是重建了一些吧,无论是自我还是和他人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