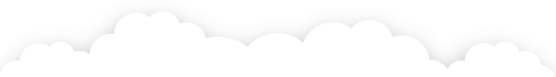作者简介
潘若天,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史。
摘 要:在前近代时期,“先生”概念谱系已经隐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前者占主导地位,称女性为“先生”在古代社会中广泛存在。近代之际,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前者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后者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两者的角力长时间内相持不下。新中国成立后,“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成为对党外人士不分性别的称谓。改革开放之后,被西方语言体系改造后的“先生”概念再次凭借西方话语权力席卷全国,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被迫居于支流。女性是否适宜称“先生”的社会性争议,本质在于西方称谓体系挟话语霸权“侵入”中国传统称谓后强行植入新的性别含义。新含义固然使旧的称谓概念焕发生机,但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称谓概念的内在完整性,由此造成内部新旧含义的剧烈冲突。
“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称谓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日常社会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颇为吊诡的是,对于这一使用频率如此高的概念,其确切内涵却存在巨大争议。一方面,大众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有称谓,并认为此乃不言自明的“常识”;另一方面,在一些正式场合,“先生”成为部分杰出女性的称谓。由此常常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男性天然可称“先生”,而女性只有杰出者才有资格称“先生”,这岂不是性别不平等的重要例证?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是否称“先生”就曾引起讨论。1986年,阿甲在《写在〈四世同堂〉获奖时》一文中称老舍夫人为“胡絜青先生”,这一用法就引起部分读者的疑惑[1]。21世纪,语言学界围绕此问题展开讨论。周有光指出,称女性为“先生”存在混淆性别、重男轻女、用词混乱三大问题[2]。李远明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应在《现代汉语词典》的“先生”义项中增加“道德文章兼备而年寿已高的知名女性”[3]。邢福义同样对女性称“先生”持正面意见,他认为称女性学人为“先生”是对男性本位社会形态的冲击[4]。陈慧通过调查统计指出,国人对女性称“先生”的分歧较大,呈现出文化程度越高,认可程度越高的趋势[5]。陈满华、陈光指出称谓背后的“性别尊卑感”,并强调称女性为“先生”破坏了当代汉语称谓系统内部自足和自洽[6]。时至今日,对于“先生”概念在使用中的困惑日益蔓延,相关讨论更是甚嚣尘上,莫衷一是。既有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讨,但对于“女性称先生”的历史发展脉络却缺乏系统梳理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意欲从概念史和性别视域出发,梳理“先生”概念传统和近代中不同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的内在理路,辨析近代“先生”概念在跨语际实践中与英文“mister”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女子称先生者,古已有之”
在汉语称谓体系中,“先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先秦时期,《诗经·大雅》中就有“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之句。《论语·为政》中也有“有酒食,先生馔”的表述,朱熹认为,此“先生”乃“父兄”之义[7]。《孟子·告子》中的“先生将何之”,赵岐注云:“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8]《礼记·曲礼上》中的“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郑玄注曰:“先生,老人教学者。”[9]从以上案例可知,“先生”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首生”“父兄”“学士年长者”“老人教学者”等核心含义。自汉迄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先生”概念以核心含义为中心,不断辐射性地向外延展,由此衍生出了更丰富的含义。俞理明指出,六朝之前,“先生”含义较为稳定,“唐宋以下,它指称的人物范围扩大,在一些环境中,可以称某些职业或类型的人”[10]。根据《汉语大词典》统计,到目前为止,“先生”概念的主要含义有:“1.始生子;2.称父兄;3.称年长有学问的人;4.称老师;5.称先祖;6.称致仕者;7.文人学者的通称;8.称道士;9.旧时称相面、卜卦、卖唱、行医、看风水等为职业的人;10.称妓女;11.旧时称担任文书或管理职事的人;12.妻称丈夫;13.一般人之间的通称;14.用以称地区或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男子。”[11]
显然,随着时代递嬗,不同的衍生含义纷纷附着在“先生”概念谱系之中。与此同时,因社会使用频率的日益下降,部分含义逐步消解,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例如,原本属于核心内涵的“首生”“父兄”等含义,在当代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已然销声匿迹。这一“附着”与“消解”的过程,也贯穿了“先生”概念谱系发展和衍变的整个历史。
若从性别的视角出发则可发现,“先生”概念最初的“首生”含义,主要指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性别层面的区隔。这也是民国之际部分女性知识分子倾向于将“先生”作为自己称谓的重要原因,“先生两字最好,就那字义上讲,就没有什么男女分别”[12]。此外,除“父兄”“丈夫”之外,“先生”概念的其他含义往往也与性别无涉。
那么,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中,是否存在女性称“先生”的案例?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国人就开始密切关注到“女子称先生”这一问题。“天地吾庐”在《申报》发表文章,以秦桧妻称“冲真先生”和女冠耿先生为例,强调“女子称先生者,古已有之”[13]。也有人强调,“先生两字,男女可以通用”,并指出“广东戏班,称女性则用女先生三字”[14]。当代学者也关注到古代社会在称女性教师、女性道士和妓女等职业时使用“先生”[10] (PP189-205)。但是,这些案例是否仅是个例?它们是否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普遍状态?要梳理并探讨上述问题,就不得不以“先生”概念下列含义为中心,系统梳理中国女性称“先生”的案例及其产生的历史情境。
(1)老师
传统“先生”概念的主要含义之一为“老师”。称男性老师为“先生”的例子兹不赘述。而称女性老师为“先生”存在诸多史例。如《新唐书》记载宋若昭事迹:
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嗣若莘所职。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15]
宋若昭乃唐代宋廷芬之女,唐宪宗、穆宗、敬宗皆称之为“先生”。显然,女性是否可被称为“先生”,在此案例中与性别身份并无关联。
在明清时期的乡村还存在一些女塾师,人们往往以“女先生”称之。《孙贞节妇传》中曰:
余少时见里中有一老妇,冬夏一蚕丝旧衫,俛然似有道气者,人皆呼之曰女先生。询其故,知其通于句读,贫家子弟多从之受业者。[16]
从此例可知,称女性教师为“先生”并非上层社会的个例,在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实践中也是广泛存在的。
晚清之际,这种称谓方式并未消亡。晚清士人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称:
五儿超侯二月二十五日随女先生戴娘娘由沪赴英肄业。戴先生年近六十,来沪已三四十年。[17]
“戴娘娘”为徐润为其子聘请的西文女教师,徐润也称之为“戴娘娘”“女先生”“戴先生”,此处的“先生”也是指“老师”。
另外,1916年京师学务局发表一则悼文,追悼的对象是一位名叫继识一的女校长,悼文中对死亡者称呼为“继女士识一先生”。这一称呼的结构为“姓+女士+名+先生”,巧妙地将“女士”和“先生”同时纳入其中[18]。继识一乃清末民初的著名女性,甚至有传教士称其为“20世纪初北京著名的女性改革家”。京师学务局于1912年成立,乃北洋政府管理北京地区学务的重要政治机构。京师学务局的这种用法,反映了将女性称作“先生”受到当时的官方机构的认可。
综上可见,性别并非称“先生”的核心因素,人们往往使用“先生”“女先生”“姓氏+先生”称呼女性教师。
(2)医生
“先生”在部分方言中是医生的称呼。宋人周守忠在《历代名医蒙求》中记录了一位被乡人称为“女先生”的女医生:
相妻方氏,明识人也,亦精幼科。……计所全活,岁不下千人,遂致道路啧啧,有“女先生胜男先生”之称。[19]
这一则史料中称男医生为“男先生”,称女医生为“女先生”。它主要反映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先生”作为医生称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未考虑性别因素;其二,“性别+先生”的称谓模式男女皆可使用。
同样,在明代戏曲《燕子笺》中,也存在请“女先生”诊病的段落:
(小旦):是一位女先生,奴家请来看霍郎病的。[20]
《燕子笺》乃晚明传奇的经典之作,在当时社会风靡一时,几近狂热(3)。其中称女医生为“女先生”,也折射出晚明都市社会中的一般状态。
另外,在清季《申报》上刊登有一则“女先生”张椿英的广告:
启者:余贸易申江,悮入烟花,忽患杨梅结毒,屡医无效。幸遇世医张椿英女先生,专治一切外症,余之毒往医不日痊效。先生设局在陈家木桥北堍。特此扬名。[21]
这则广告称张椿英为“女先生”“先生”,与前几则史料一脉相承。由此可见,自宋至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称呼女性医生为“女先生”“先生”的情况。
(3)道士
以“先生”称道士,早在东晋之际就已存在。道教典籍称:“先生位重,不可妄称,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夫先生者,道士也。”[22] (P107)而道士称“先生”者,同样无性别之分。史籍中曾记载多名被称为“先生”的女性道士。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女道士“耿先生”:“女冠耿先生,鸟爪玉貌,甚有道术,获宠于元宗。”[23] (P19)“女冠”即是指女道士,这里使用的是“姓氏+先生”的用法。
有宋一代,君主赐女性“××先生”道号者不乏其人。例如,宋高宗时期的秦桧之妻王氏“乞改赐一道号,诏特封冲真先生”[24] (P2274)。根据《朝野遗记》记载,在宋宁宗时期,婕妤曹氏受皇帝宠幸,“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为女冠,赐号虚无自然先生”[25]。
即使在近代社会,依然存在会道门组织中的女性称“先生”的案例。例如,在一贯道中,“未敬礼前,不算正式入道,直称其名。敬礼后,不论男女均称先生”[26](P33)。正式加入一贯道后的信徒“不论男女均称先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道士无论男女皆称“先生”的遗风。
(4)算命先生、占卜先生
称呼以算命、占卜为业者为“先生”,源流甚久。汉代《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先生相人何如”之句[27](P2623)。其中“先生”即指相面者、占卜者。女性占卜者称“先生”的案例也并不少。例如,《西游记》中描绘孙悟空占算的场景:“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28] (P166)其中的“桃花女先生”即指桃花女。桃花女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经典女性角色,她擅长占卜、解禳,与周公斗法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西游记》中称“桃花女”为“先生”,也是明代社会以“先生”称呼女性占卜者的真实反映。
清代小说《忠烈全传》中也有称女性占卜者为“女先生”的文本:
大姐不要哭,女先生算你该做妾,虽不是顾家,也是本府太爷一个黄堂的公子,到不如一个穷酸吗?都是一样做妾,哭做什么。[29]
女性算命、占卜者称“先生”或“女先生”在明清社会中并不少见,且在民间社会颇为根深蒂固。据笔者所见,直至改革开放后,还存在以“女先生”指代女性算命、占卜者的情况。例如,新华社在1999年的新闻报道《算命透视》中有:
另一位“女先生”指着自己招牌上“抽签、算命、看手相”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说:“这也是请人写的。没文化就不行?刚才你不是看见我把那个小伙说入了迷?” [30] (P294)
显然,此例中的“女先生”与明清小说中的情况无异,称占卜者为“先生”同样不存在性别区分。
(5)女说书、女弹词
旧时对于评弹艺人,俗称“说书先生”,对于女说书、女弹词,亦称“先生”或“女先生”。《红楼梦》中有:“女先儿回说:‘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31](P746)其中的“女先儿”即是“女先生”。此类称谓在晚清之际更为普遍。持平叟在《接女弹词小志》中指出:“上海风俗,称女弹词为先生,称弹唱处为书场。”[32] 王韬在《海陬冶游录》中称:“沪上女子之说平话者,称为先生,大抵即昔之弹词,从前北方女先儿之流。” [33]
(6)妓女
称妓女为“先生”的用法常见于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字林沪报》在1893年有报道称:
至于歌妓则公然称之曰先生,而狎客之媚妓者,又不第以先生目之,而竟称之曰某翁。
直至民国之际,此风依然存续。据民国报人包天笑称:“堂子里他们决不以称女人先生为特异。因为他们的制度,也是称女人为先生的,又分出什么大先生、小先生、尖先生之类。”[12]至于称妓女为“先生”之原因,有研究者认为“也许源自附庸文人风雅”,并猜测此用法与“以卖唱等为职业的人”有关联[4]。此说可谓精到,但并未举出具体证据。据民国时人观察:“上海在同光之间,盛行女弹词,亦有许多女书场,因为说书者,都呼作先生,所以女弹词家,亦都呼为先生。后来女弹词,即蜕变而为妓女,故其所居之处,则曰‘书寓’,招之侑酒,则曰‘堂唱’,都留有女说书先生的残痕。”[34]由此可见,妓女称“先生”肇始于女弹词、女说书之说,并非无根之言。
上述“先生”概念的诸多含义,除“妓女”这一含义外,无论是老师、道士、医生、占卜先生、说书先生等,皆男女通用。那么,是否存在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属物的例证?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耳目所及,有下列两例较为典型。
其一,南宋时期秦桧之妻王氏自称“冲真先生”,王佐驳之曰:“妾妇安得此称!”[35] (P285)王佐因秦桧之妻的性别身份,对她是否有资格称“先生”表示强烈质疑。但关键问题是,王氏的“冲真先生”乃皇帝亲自颁赐的“道冠师号”[36] (P288)。如前文所述,宋代政府还有赐予女道士“虚无自然先生”道号的记载。质而言之,性别并非政府赐予“××先生”称号最核心因素。王氏最终被剥夺“冲真先生”之号,南宋初年的高层政治斗争或许比性别身份更为关键。
其二,晚清之际,“湖上稚云”在《书说书女先生合传后》一文中称:“盖先之云者,长老之称也;生之云者,男子之谓也。”[37]此处强调“先生”之“生”,乃男性之义,由此视“先生”概念为男性独有的称谓。不过,此文叙述的主体就是被称作“女先生”的女性说书人!
以上两例皆反映了一个核心问题:尽管部分士人强调女性不能称“先生”,但这恰恰又证实了古代社会存在女性称“先生”的具体实践。
综上可知,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概念并非男性独享的话语空间,它在性别层面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老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等职业中,无论男女,皆可使用“先生”之称。其使用方法包括“先生”“性别+先生”“姓氏+先生”“××先生”之类,与男性并无本质区别。毋需否认,由于古代社会中老师、医生、道士等职业,男性从业比例高,在浩瀚无垠的古代文献中,留存下大量男性称“先生”的案例,部分士人或由此产生“妾妇安得此称”的错觉,试图强行将“先生”和“男性”之间建立起关联。不过,这一认知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更未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付诸具体的语言实践。进而言之,在古代中国,男女两性身处不同的公私空间,也相应存在不同的社会规范和话语场域,女性称“先生”或许在部分职业领域或私人空间广泛使用,不过一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它在某种程度上给“约定俗成”的语言惯习带来冲击与威胁,这或许正是女性称“先生”引起部分士人不满的原因之一。
二、民国之际女性称“先生”的进一步发展
在民国建立之前,女性称“先生”存在一定的职业局限,一般只有作为医生、教师、道士、占卜者、说书人、妓女等含义时,“先生”概念才会出现在女性称谓中。而男性可使用“先生”作为日常交际过程中的一般尊称,这种使用方法一般较少覆盖到女性群体。1912年之后这一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作为对女性的一般尊称逐渐走入国人的日常交际之中。
推动这一变化的关键性制度文件是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大总统令内政部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在该法令中,孙中山要求革除前清官厅中的“大人”“老爷”等称谓,以“先生”和“君”两种称谓取而代之:
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38]
当国家政体从“君国”向“民国”跃进之际,称谓革命也被纳入新政权关注的重心。国家权力强行进入私人场域,利用语言、称谓等日用而不知的惯习,试图将君权制下的“臣民”改造为共和制下的“公民”。“老爷”“大人”等称谓因“盛行于官僚社会,显然分着尊卑的阶级”而被政府摒弃[39]。“先生”和“君”两大称谓因其内在的相对平等性,被南京临时政府赋予了合法地位。袁世凯当政之际,曾短暂恢复清代官场称谓,禁止互称“先生”。焦菊隐曾讥之曰:这与孙中山下令以“先生”和“君”作为社会通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40]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先生”和“共和”深度绑定,社会上甚至有“共和先生”和“专制老爷”的戏称[41]。这反映了民初国人在“先生”概念上赋予了政治平等的时代含义。
不过,南京临时政府的相关法令并未指明“先生”和“君”所使用的性别范围,而是将两者视作“民间普通称呼”。那么,“先生”作为通称可以涵盖女性还是仅仅指代男性群体呢?
1918年,刘哲庐观察到:“惟近日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称者,此系共和告成一种普通之词,亦颇通用。”[42]在这里,女性称“先生”的含义,已经不再仅局限于过去的教师、医生、道士、占卜者、说书人、妓女等,而变成可以指代包括全体女性和男性在内的社会通称。刘哲庐称此乃“共和告成一种普通之词”,显然“共和告成”在“先生”概念变化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先生”概念中所蕴含的性别平等,在民国初年的共和潮流中日益滋长,与共和体制背后的政治平等同频共振,政府在通过称谓革命改造国民的同时,也从性别层面不断拓宽“先生”概念的性别所指。
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后“女界每多以先生相称”乃共和政体下政治平等之风激荡的新生事物,那么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平等社会风潮,则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称“先生”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沃邱仲子在其小说《新官场家庭繁华史》中的下列描述,集中反映了“先生”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不分性别:
女士谓邹曰:“余与子夫妇之关系业已断绝,他日相遇,我呼子以邹先生,子亦当称我以某先生,毋作女儿态也。”邹唯唯。女既从余时,或相遇,二人必互以先生相称谓。[43]
离婚夫妇互称“先生”,凸显了新文化运动之后性别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在此社会风气的席卷之下,人们将女性称“先生”赋予了男女平权和女性独立的时代含义:“在现代中国,抹煞丈夫的姓名,正足以表示她的独立性,再在她处女姓名之后,殿上一个先生的字样,于是乎她在社会上,便完全与男子平等了。”[44]由此,不同性别在称谓层面的统一,被视作性别平等的关键标志。还有人认为:“民国以前,‘先生’一词是男士的专利品,妇女是‘无福享受’的,民国成立以后,女同胞跟男同胞争‘平权’,部份得到‘成功’,从此‘先生’之尊称,女同胞也可以‘分享’了。”[45]显然,她们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的特权或“专利品”,而女性称“先生”正是女同胞争取自身权力的一种成果。还有人认为:“现在的新思潮,妇女不是要解放吗?妇女既要解放,和男子平等,那么文字上的界限,不要打破吗?”因此,“改‘先生’为通性名词,岂不便利?而平等的形式,也很合于新思潮呀!”[46]民国小说家包天笑就描绘了一位提倡“男女平权”的女性任佩真,“不喜欢人家呼伊女士”,更愿意别人称呼她为“先生”[12]。称谓作为社会日常交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权力结构外化的自然表征,故而称谓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既有权力结构的松动、崩解或重组。在此基础上,人们往往赋予称谓变革超越其本身的社会性、政治性意义。强调女性拥有“先生”概念的使用权,是性别平等这一文化口号在称谓上的标志性呈现。
不过,尽管民国时期政府高唱以“先生”取代“大人”“老爷”,但实际效用则并不理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建立已越十余年之久,而“老爷”“大人”“太太”等称谓依然大行其道。时人指出:“不特缙绅阀阅之家沿用而不改,就是党治下的官吏和民众,也都照旧的称用而不废,甚至于自命为革命救国的而在党部里边充当委员或者工作人员的,他们的家庭之间,也和缙绅阀阅之家一样地沿用这种称呼。”[47]1929年,有人提议废除“老爷”“太太”,无分性别“一律称之为先生,以符男女平等之旨”[48]。有鉴于此,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一则通令,要求取缔腐化称谓:
嗣后有官职称其官职,无官职者,一律称先生,不准再用旧日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腐化之称谓。
这则通令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对于社会称谓的认知。从“先生”概念变迁的角度而言,这则通令虽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政令一脉相承,但也具有其独特的关键意义。首先,这则通令不再提及“君”这一称谓,由此可见,在与“君”的较量中,“先生”占据上风,并成为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称谓。其次,这则通令取缔“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而一律改为“先生”。“老爷”“少爷”乃男性称谓,“太太”“小姐”乃女性称谓,政府却不分性别一律改为“先生”。由此可知,政府首次官方确定了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先生”概念,并无性别之分。
此后,社会上使用不分男女皆称“先生”的情况愈发普遍。1934年就有人称:“‘先生’之称,习惯上本不分‘男’‘女’‘老’‘幼’‘童男’‘处女’的。”[49]1939年,一位署名“画虎生”的作者观察到,女性称“先生”一事“频接于耳目”[50]。1949年,张亦芳给《亦报》编辑“白荷小姐”写信,询问如何称呼女性,“白荷小姐”回复道:“写信时为省麻烦起见,在性别上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写‘先生’为最佳。”这也反映了“先生”作为一种全体公民的通称,日益受到社会的认可。
不过,将“先生”视作不分男女老少的通性称谓仅仅是理想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以“先生”称呼女性往往还存在一定限制。其限定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先生”主要用来称呼未婚或无丈夫的女性。芦焚在小说《鸟的归来》中描绘了女性被人称作“先生”后的复杂的心理:
“先生到什么地方?出门久了罢。”
老人虽然上了几岁年纪,眼光还不差,他看得出女人是应该称先生的。然而这简单的问话使易瑾发慌。……起初他称“先生”似乎看准易瑾没有丈夫。“难道我就不准有一个合意的丈夫吗?”她这样想,还非常难过。[51]
“先生”在此主要是指“没有丈夫”的女性。相似的用法在其他文本中也有体现:“有的女人,她已结了婚,你如果仍称呼她‘小姐’‘先生’,她又会勃然大怒,认为你不把她和丈夫的夫妇关系当做正式的。”[52]称呼已经结婚的女性为“先生”会引起被称呼者的勃然大怒,这也可以反证,在部分场合中,“先生”主要是针对未结婚或未有丈夫的女性。
第二,主要称呼知识阶层或新式女性。当代学者也关注到,民国之际存在女性读书人、女性学人称作“先生”的用法。对此民国时人也有所论述。他们指出,“先生”称谓局限在知识阶层女性的原因在于这一称谓本身的特殊性:“对新式女子呼‘先生’,本来很冠冕,但对乡下女子也这样称呼,就要叫他惶惑起来而不敢答应了。”[49]还有人强调知识分子女性称“先生”是常态:“现在妇女虽亦可称为先生,但大抵都系对知识份子而发,如果对一个毫无智识的妇女,或智能比较低级的‘老粗’,仍一律称以先生或老先生等名称,有时不但不很相宜,而且还似乎有点不伦不类。”[53]
无须讳言,民国时期也广泛存在着反对女性称“先生”的舆论,其反对理由如下。
其一,女性本已存在“小姐”“太太”“夫人”等称谓,无须再增加新的称谓。钱歌川指出:“我的主张,是以先生称呼女子的办法,非到万不得已时顶好不用。对于未婚的女子,称为女士或小姐,对于已婚的女子,称为夫人或太太,似属正道。”[44]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皆有相对适合的称谓,增加“先生”称谓反而造成冗余。
其二,妓女称“先生”,故而称女性为“先生”是不尊重。时人认为:“若男子亦呼女子为先生,颇不雅听,且沪俗对于妓女称先生,似未便以先生加一般普通之女子。”[54]显然,“先生”概念衍生出来的“妓女”含义,影响了时人对此称谓的观感。
其三,日常使用中存在不便,特别是亲子关系中。署名“塞外”的作者称:“管她妈叫先生,管她女儿也叫先生。譬如姓张,母亲女儿都叫张先生吗?他父亲是称先生,哥哥兄弟也都是先生,一家子老老少少都是称先生,一家子先生,未免滑稽!”[55]一家之内,人人皆为“先生”,往往给日常交际带来困难。
其四,“先生”为男性之通称,不宜用于女性。黄希声曾指出,“先生”二字“久已习用为男子之通称,今女子亦袭之,由以男子之衣衣于女子之体,虽童子亦知其不称”[56]。强调“先生”为男性之通称,并非黄希声一人所持有的观点。也有人称“先生”在民国诞生之前乃男性之“专利品”[45]。因此,“先生”已经久为男性通称,如今女性再使用它,无异于“以男子之衣衣于女子之体”[56]。
三、“先生”概念谱系危机及其性别含义
在前近代时期,“先生”概念谱系已经隐然存在“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但前者完全占主导地位,称女性为“先生”在日常交际中广泛存在。在20世纪,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在民国之际,部分国人已将“先生”概念视作男性“专利品”[45]。类似表述连篇累牍,不胜枚举。不仅如此,当代学者也存在类似的观念:“在当代广大老百姓的心目中,‘先生’就是男子。你可以抱怨他(她)文化不高或孤陋寡闻,但你绝对不能改变他(她)的这一母语者的语感。”[6]那么将“先生”视作男性“专利品”的“母语者的语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国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先生”与“mister”之间的对译关系被反复强调。有人称:“密司忒Mr是先生的代名词。”[57]还有研究者指出:“Mr一字,既为男性名词,那么‘先生’两字,也就是男性名词了。”[46]也就是说,“mister”中包含的性别因素,也“必然性”地呈现在“先生”概念中。那么,为何“先生”的性别指向无法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反而需要借用“mister”才能推演?显然,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起点在于,坚信“先生”和“mister”之间存在对译关系。不过,两者来自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其内涵虽有相似、契合之处,但也并非完全吻合。那么,“先生”与“mister”对译这一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进入国人的思想世界并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常识的?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就有必要系统梳理“mister”概念在跨语境旅行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称谓体系的挑战与改造。
1911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指出,“mister”源自“master”,“master”作为男性名字的常用前缀,最初限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受“mistress”的影响,它在发音上变为“mister”。其中还举两例“Mr Justice”和“Mr Speaker”,前者称高等法院法官,后者指下议院议长[58] 。在《巴恩哈特词源词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中称“mister(Mr.)”为男性尊称[59] 。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mister”义项下有两条:“1.Mr的全写,书写时不常用;2.儿童常用,称呼不知姓名的男子。”在“Mr”义项下有两条:“1.用于男子的姓氏或姓名前;2.称呼要员。”[60] 综上可见,在英文语境中,“mister”作为男子之称,性别含义颇为明显。
英文“mister”在中国的跨语际“旅行”,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存在密切关联。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之际,英文“mister”便通过音译方式开始出现在中文典籍中。在《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中,将“mister”“mesrs”翻译为“米斯”,苏楞额特别解释:“米斯是赞美之词。”[61]作为“mister”的翻译,“米斯”在1884年的《申报》中还在使用。在《申报》广告栏申隆洋行产业招租的广告中有“申隆洋行米斯格劳司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粤语中文文选》(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中还提到“mister”的另一种音译——“美士”[62]。
此音译至少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中英双方的部分使用。例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42年出版的《拾级大成》中以“美士哋”来翻译“Mr.T”[63] (P92)。广东行商伍绍荣等在致英人函中也有“上美士滑文、美士颠地、美士查典、美士拜、美士化林治暨列位真地文”的文本[64] 。
其中,“美士滑文”即“Mr.Whiteman”,“美士颠地”即“Mr.Dent”,“美士查典”即“Mr.Jardine”,“美士拜”即“Mr.Boyd”,“美士化林治”即“Mr.Framjee”。除此之外,“mister”还有“未士打”“未氏”“未士”等音译。例如,行商伍浩官在致英国大班的信中称其为“大班未士哈”或“未氏哈”,即为“Mr.Hall”的音译[65]。唐廷枢在《英语集全》中以“未士”“未士打”翻译“mister”[66] 。邝其照在《英华字典集成》中也使用音译“未士打”[67] 。
以上诸多音译,固然保留了英文“mister”的特殊内涵,但在具体跨语境实践过程中不免有佶屈聱牙之感。那么究竟如何借用汉文体系中的固有概念作为“mister”的对译呢?表1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编纂的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
表1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英辞典和教科书中对“mister”的中译
表1中的13种中英辞典与教材在清末民初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中关于“mister”的中译共计15种,其使用频次如下:先生(13)、公(4)、相公(3)、老爷(2)、老师(1)、官(1)、师爷(1)、君(1)、大人(1)、事头(1)、司务(1)、头家(1)、老将(1)、家长(1)、美士(1)。从统计中可以看出,上列各辞典的作者无一例外皆将“先生”视作英文“mister”的中文译名之一,远远高于“相公”和“老爷”及其他译名。
正如前文所述,“先生”概念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下男女皆可使用,而“mister”乃男性称谓,两种概念在性别指代层面存在无法忽视的割裂式差异。那么,为何西方汉学家“异口同声”地选择使用“先生”来翻译“mister”呢?是西方汉学家们不了解“先生”与“mister”之间的不一致性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866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在《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中将英文词汇“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70];波乃耶(J.Dyer Ball)在其著作《粤语速成》(Cantonese Made Easy)中特别强调中文“先生”概念适用于所有性别[80]。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对英文“teacher(a femal)”词条的翻译也是“先生”和“女先生”[77]。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上海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中将“schoolmistress”翻译为“女先生”[71]。启尔德(Omar L.Kilborn)在《华西初级汉语课程》(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中同样指出在中国“先生”概念可以指“女性教师”[81]。以上种种表明,早期的西方汉学家并非没有关注到这批被赋予“先生”或“女先生”称谓的中国女性教师群体。
既然西方汉学家了解到中文“先生”概念并不存在性别层面的特指,为何普遍采用它来翻译“mister”呢?其原因在于,首先,“先生”概念在晚清之际开始逐步呈现出超越阶层的普适性特征。其使用范围日趋泛滥,“至若捕房之包探,戏馆之伶人,洋行之侍者,沿街之巡捕,亦称之先生、老爷”,时人将此视作“称谓之滥”“名器扫地”。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称谓“代际性贬值”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先生”突破了知识阶层的局限,进一步辐射到“包探”“伶人”“侍者”“巡捕”等平民阶层。这一平民化趋势自然为民国时期“先生”作为全体公民通称奠定了基础。其次,与“相公”“公”相比,“先生”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层面更具有广泛性。启尔德(Omar L.Kilborn)特别指出,这一概念“几乎是全中国通用的名称,它可以用来称呼生活中任何地位的人”[81]。显然,在普适性和广泛性上,“先生”与“mister”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强调“先生”是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75]。博良(Robert Thomas Bryan)也将“先生”视作“mister”的对应词[82]。显然,在西方汉学家笔下,“先生”与“mister”因拥有相似的内涵而建立起了互译的关系。
“先生”与“mister”的互译关系,毕竟是来自西方汉学家在跨语际实践中的集体性建构。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植入”国人思想世界之中,并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呢?
据笔者所见,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国人较少将“先生”与“mister”互译。以唐廷枢1862年出版的《英语集全》为例,该书将“先生”翻译为“teacher”和“doctor”,又将“mister”音译为“未士”“未士打”[66]。全书中皆未出现用“先生”翻译“mister”的情况。据周振鹤考释,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中“先生”的英文翻译为“school master”[83]。冯泽夫的《英话注解》中“先生”同样翻译为“teacher”[84]。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先生”和“mister”此时在国人的思想中还未建立起互译关系,人们在使用“mister”及其音译时,往往将它视作对西方男性的称谓,而在使用“先生”时,则视作对教师、医生等职业人士的尊称。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1855年初版、1860年重版的《华英通语》一方面在词汇条目中将“先生”译为“teacher”,另一方面在会话中将“mister”译为“先生”[85]。《华英通语》的相关用法,很可能与作者“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有年”[86]、深受西方汉学家熏陶有关。
质而言之,“先生”是否与“mister”互译,反映了中西方话语权力在中国语言体系场域的角逐和竞争。从西方语言的角度来说,它亟需在中国语言体系内找寻西方语言的中文对译,从而降低和减少中西交流中的沟通成本和语言障碍。“先生”被视作“汉语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mister的语言”而受到西方汉学家的青睐。从中国语言自身的发展脉络而言,“先生”并无与“mister”建立互译关系的必要,两者固有相通之处,但皆存在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在性别层面的尖锐矛盾更是难以调和。与其深度捆绑,不如各行其是,采用音译方式翻译“mister”,可以避免两者建立互译关系后产生的后续纠纷。这或许正是唐廷枢在《英语集全》中仅采用“未士”“未士打”而非“先生”来翻译“mister”的深意所在。
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势逐步发生变化。处于“船坚炮利”威慑下的中国在东西方话语权力角逐中日益弱势。而这种权力关系的变迁也相应地反映在东西方语言之中。由此,汉学家建构起来的“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堂而皇之进入国人编纂的字典和日常使用之中。1868年,邝其照在《字典集成》中已将“先生”作为“mister”的中文翻译之一[87]。1879年,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了关于“mister”的记载:“始跪时犹称密思得,一加宝剑其肩,起则名色克。密思得,译言先生,官人通词也。”郭嵩焘还强调:“密斯得,犹中国尊称曰先生。官及有学问者名之曰密斯得。”[88]此处的“密思得”“密斯得”皆为“mister”的音译。1908年,颜惠庆在《英华大辞典》将“mister”作为“先生之浑称”[89]。1913年《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中“mister”的中文翻译为“先生”和“老师”[90]。1915年甘永龙等编纂的《英华日用字典》将“先生”作为“mister”的唯一翻译[91]。在各种辞典的引导下,“先生”与“mister”互译开始在部分国人的思想世界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mister”的音译词——包括“未士”“密四”“密司忒”“密司特”“密斯特”“密司脱”等——也逐步在上海、北京等地扩散,并逐步渗透至都市社会的日常语言实践中。1973年,杨少坪在《申报》发表的《别琴竹枝词》中有“如何密四叫先生”之句[92]。所谓“别琴”即洋泾浜(pidgin),“密四”即“mister”的音译。“解虚”在《露天通事生意之寥落》中也有“尾逐洋人呼密四”之语,并注释“密四”即“先生之称”[93]。1900年在《申报》的一则广告中,同时使用“括打先生”和“未士括打”两种称谓(11)。由此可见,“未士”作为“mister”的音译依然在清末存在影响力。到了民国之际,部分趋于时髦者甚至不再使用“先生”,而是改用“mister”的音译词作为对方的称谓。据当时国人的观察:“现在中国的人凡是认识几个英文字的,与人谈起话来,总要把他所认识的几个英文字嵌入话去,譬如称呼男子必曰密司脱某某。”[94]显然,使用“mister”的音译词作为日常交际的称谓俨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甚至在上海还出现乞丐以英文“密司脱”乞讨的案例。
当“先生”与“mister”互译这一观念被部分国人接受之后,英文“mister”的含义也逐步渗透到“先生”概念谱系之中,并形成一个新的义项——“对一般男性的通称”。这种渗透看似悄无声息,实则波涛暗涌:毕竟传统“先生”概念男女皆可使用,但“mister”仅男性使用,两个在性别层面截然对立的含义如何共处于一个概念谱系之下呢?
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可从新文化运动爆发前陈衡哲与胡适二人关于“先生”称谓的诗文往来中窥见一斑。陈衡哲在回复胡适的信中称其为“先生”,这不禁引起胡适的注意。关于“先生”称谓,胡适寄送一首打油诗给陈衡哲: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而陈衡哲回复称:
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_
对此,胡适答之曰: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95]
胡适与陈衡哲之间关于“先生”的诗文往来,从近代中国称谓体系转型的角度而言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此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先生”与“mister”互译关系,导致“先生”概念谱系滋生出性别层面的尖锐矛盾,并已经给国人之间的日常交际带来事实上的困惑。胡适所理解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先生”含义,并无性别指涉,而存在被呼者为尊、呼者为卑的习惯。故而当陈衡哲以“先生”称呼自己时,胡适表示极力推辞。与此相对,陈衡哲使用的“先生”概念则截然相反,其本质是英文“mister”的中文翻译。正如陈衡哲所言,“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密斯忒”即“mister”的音译词,其本身即是指男性而言。从这一角度而言,胡适称陈衡哲为“先生(mister)”并不恰当。显然,胡、陈二人观点互相对立,但皆有所本,关键问题在于现代“先生”概念已经杂糅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含义,由此这番造成“驴头不对马嘴”的诗文对话,其背后折射出是近代以来强势入侵的“mister”与传统“先生”含义之间的激烈交锋。
胡、陈二人关于“先生”的诗文交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初年“先生”概念谱系内在传统含义与“mister”之间的缠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不过,在东西方交流碰撞的近代中国,在不可译的语言之间究竟选择如何翻译,本质上是由强势语言决定的。
如果说,传统“先生”含义此时还具有与“mister”缠斗的资本,那么,新文化运动爆发及其彰显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成为压垮传统“先生”含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时,“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例如,1924年由教育部审定出版的《新法英语教科书》中在英文“mister”词条下唯一的翻译为“先生”[96]。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讲义》也将“先生”作为“mister”的主要翻译之一[97]。陈平编订的《日用常识·英语无师自通》也称:“英文名称,“mister”,中文译义,先生,中文读音,密司脱。”[98]“先生”与“mister”互译观念在社会中不断强化,并日益成为国人知识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何龚登朝强调:“Mr一字既为男性名词,那么‘先生’两字也就是男性名词了。”[46]“先生”概念源自中国传统,但其内涵竟然需要用“mister”的含义来推断!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传统“先生”的含义沦落边缘,“mister”的含义日益强势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趋势在鲁迅1933年的一则书信中更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信中,鲁迅尖锐地指出:
其实,“先生”之称,现已失其本谊,不过是英语“密斯偷”之神韵译而已。[99]
“密斯偷”即“mister”的音译词。在鲁迅的认知中,“先生”概念丢失了“本谊”,沦为“mister”的附属物。质而言之,“先生”和“mister”的权力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文体系内,“mister”本需依附“先生”概念而存在,而如今“先生”反而成为“mister”的“神韵译”了!
诚然,鲁迅认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韵译”这一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传统“先生”概念固然遭遇到“mister”及其音译词的不断侵蚀,但并非完全处于劣势状态。一方面,国民政府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从官方层面确定传统“先生”概念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国人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认知日益深入,社会逐渐开始出现对西方概念音译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批评。人们观察到“社会中无不满口英文称呼”,不禁感慨系之:“中国固有语言文字早已先国而亡矣!”[100]刘半农极力呼吁取缔“密司特(mister)”“密司(miss)”等音译称谓,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何必用不中不西的称号来混淆”。在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触痛之下,部分国人开始反思:中国需要“欧化”的语言、语法体系吗?显然,此类对西方语言在中文体系中过度扩张的警惕也给传统“先生”概念提供了一定的喘息空间。但在“先生”概念谱系内,“mister”日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传统的“先生”含义虽背靠政府赋予的合法性勉强与“mister”抗衡,但逐步走向式微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四、余论
综上可知,传统“先生”概念在历史衍变过程中呈现出“男女皆可用”和“仅男性可用”两种含义的矛盾。至少在明清之际,前一种含义在社会上居于主流地位。到了近代中国,由于概念的自身衍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由此,两种含义的“先生”概念产生竞逐,前者挟西方话语霸权而被社会广泛认知,后者因政府“钦定”而具有合法性,在两者之间白热化的角力中,前者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
1949年,新中国“革掉了先生、夫人、太太、小姐的称谓”,论者将此视作“中国百姓的自由、解放、平等和主人公地位”建立的标志之一[101]。新中国摒弃“先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内在的阶级意识。民国之际有人指出:“这称谓含作极浓重的阶级意识,贫穷的人对一个比他有钱的人,以前叫做老爷,现在改称先生,反之,有钱人对一个贫穷的人呢,则可直呼其名,不用与之客气,不必称什么先生与不先生。”[102]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将它视作“国民党的气味与旧社会的习惯”,强调在私人来往信件中取缔包括“先生”在内的一系列称谓,代之以职务或“同志”[103]。随着“先生”概念的失势,“同志”这一具有政治平等性和无性别区隔的称谓开始占据社会主流。
由此,“先生”概念的含义大幅度萎缩。在官方表述中,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代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等。此风气实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例如,谢觉哉在1944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凡党外人士皆称先生”[104]。到1957年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中,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对称其为“先生”提出异议。葛剑雄也在回忆中指出:“在报纸上偶然见到有人被称为‘先生’,除了像享受殊荣的鲁迅外,其他肯定属于统战对象,是不能称为同志的人。”[10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这一含义在这一时期还在延续,不过指代对象被大幅度压缩至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或海外华侨这一群体,不再成为社会的通称。
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在1949年之后虽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我国港澳台地区回流。据时人观察:“先生的称呼像是翻了个身,逐渐吃香起来。口头上、请柬上、文章上,先生二字越来越多。”[106]受时代惯习影响,国人一开始主要使用这一“洋味”语言来称呼我国港澳台同胞和西方游客。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了”[107]。“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108]。需要指出的是,仅男性可用的“先生”称谓,本质是英文“mister”的翻译,西方语言的话语权力与“先生”称谓的风行并非毫无关联。
除此之外,“先生”还有两重含义也在不断发展与传播。其一,用“先生”称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等,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是1949年之后“先生”概念衍生含义的时代性延续;其二,用“先生”称年长而有威望者,这与自先秦以来用“先生”尊称“学士年长者”相关。目前以上两种用法皆不强调性别因素,并且在政界、学界的部分特殊场合得到广泛使用。不过在现代“先生”概念谱系中,以上两重含义仅居于支流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当代社会关于“先生”的争议与讨论,凸显的是自清末以来“先生”概念在演变过程中一直潜藏的价值危机。传统“先生”概念谱系中,“男女皆可用”占据主导地位。自19世纪中期西方汉学家强行将“mister”和“先生”建构起互译关系开始,“mister”作为一种特殊含义开始悄然“寄生”在“先生”概念的躯壳之中。最初它仅位于边缘位置,无法对“先生”概念的核心含义造成威胁。但在近现代社会,西方语言、文字、观念、文化等被渲染上了一层“天然的合法性”,“mister”藉此“合法性”的庇佑不断挤压其他含义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男女皆可用”的含义逐步边缘化,“mister”及其背后的性别因素在不知不觉间从“寄生”转为“主宰”,一跃而成“先生”概念谱系中最核心的含义。
鲁迅提出“先生”已成“mister”的“神韵译”,在民国之际看似有所夸大,但对当代“先生”概念不啻为一则精准预言。如今广泛使用的“先生”,早已与前近代时期的“先生”无甚关联,两者虽使用同一个“皮囊”,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质与内核。从这一点而言,女性之所以不宜称“先生”,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侵入”后对中国称谓体系的改造与重构。如今,被晚清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先生”在未来究竟应如何演变和发展?这或许值得当代国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展开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2期
《妇女研究论丛》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中国妇女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期刊。1992年创刊,1999年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HSSCJS)、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JC)、中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本刊主要栏目有: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法律与政策研究、妇运观察与历史研究、文学•文化•传播、国外妇女/性别研究、青年论坛、研究动态与信息、图书评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