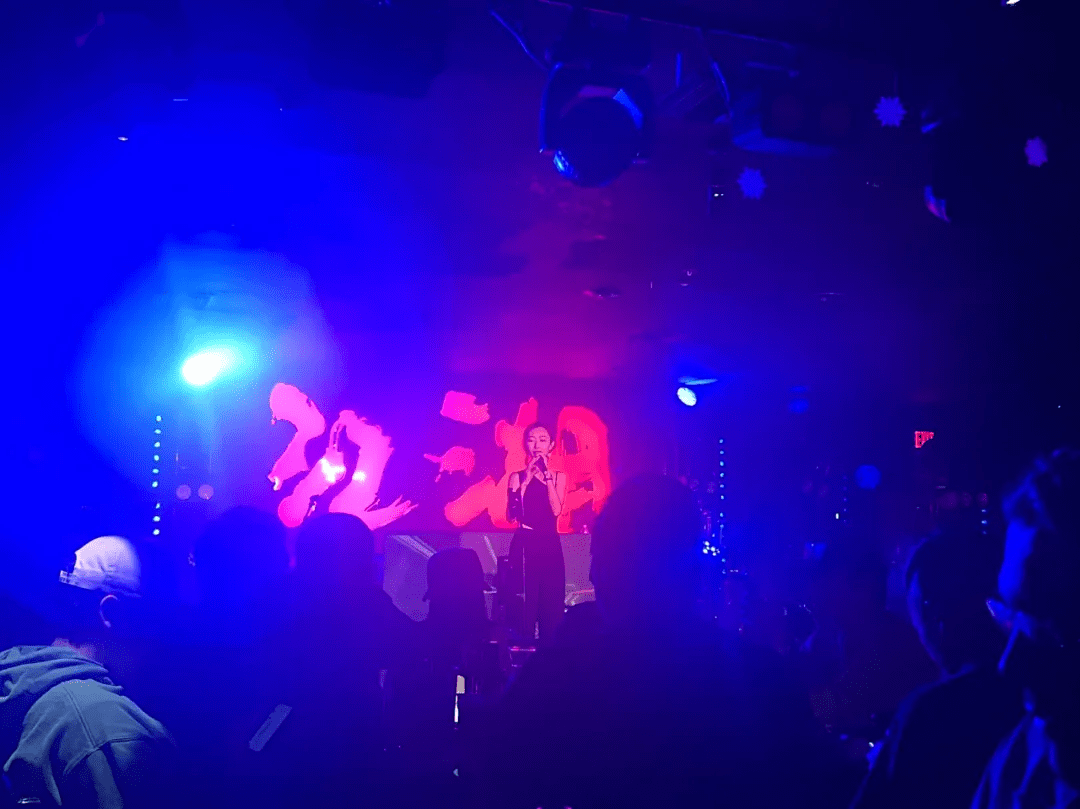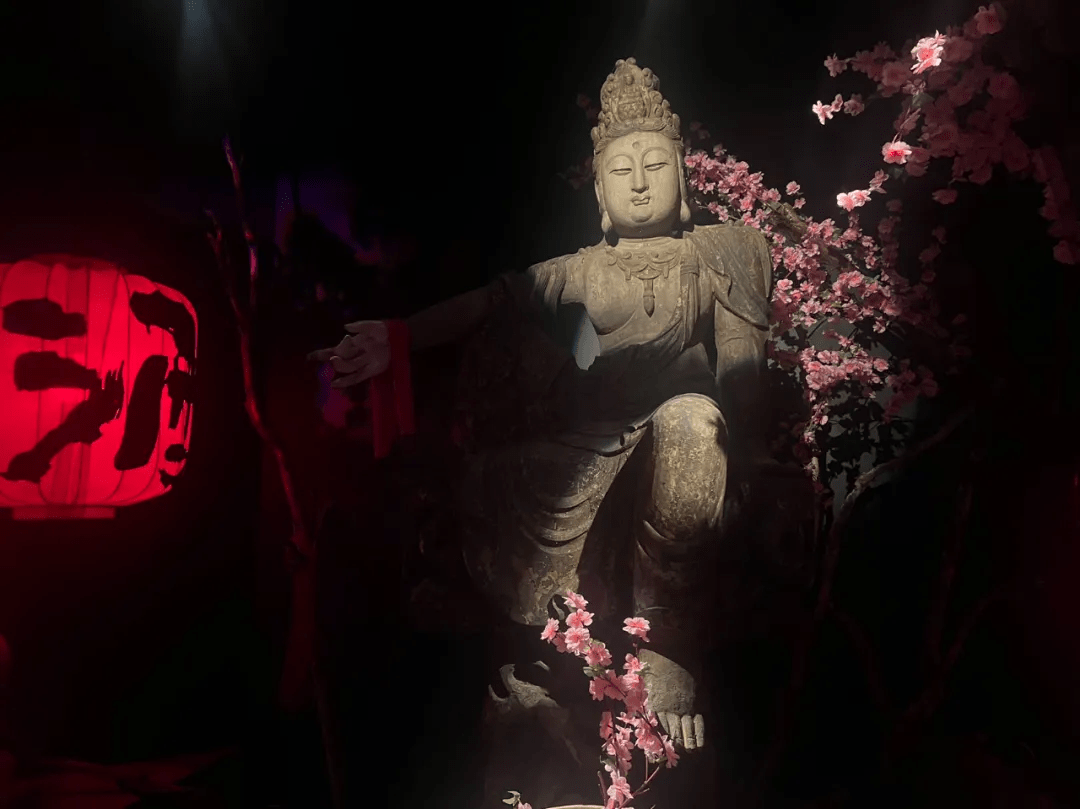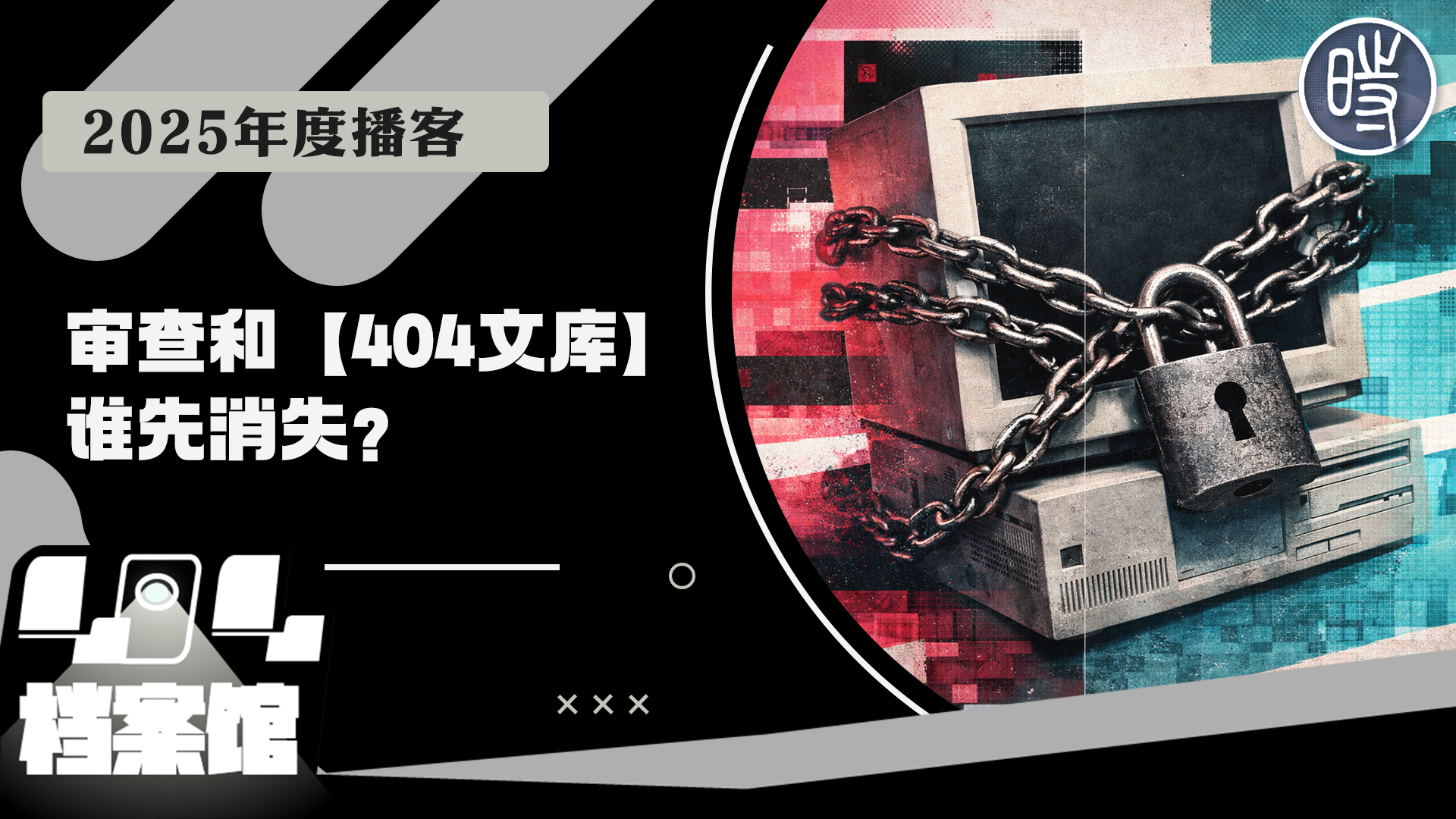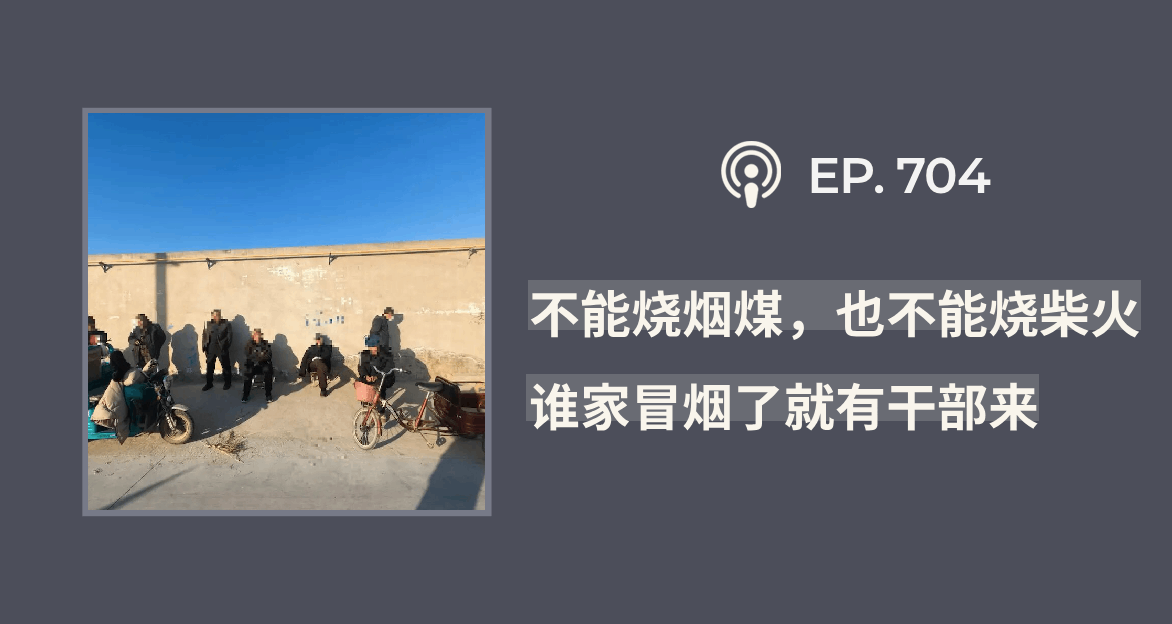当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我下个月底就会结束访学回到成都。
1
在洛杉矶吃了两次中餐。一家是川娃子川菜馆,一家二娃冷锅鱼。
看名字就知道它们来自成都。在这里不用说英语,甚至不用说普通话,讲四川话就行。
请客的朋友说,打电话给川娃子,接电话的不是普通话,他有点担心换老板,菜就不地道了。老板说,还是那个味道。
2012年我来过一次美国,一路吃的都是洋中餐。现在,在纽约和洛杉矶,有些中餐馆味道已经和中国一模一样。藤椒鱼里,用的是地道的青花椒。
“脱钩”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人正在把一切生活细节都搬到大洋彼岸。
中餐馆追求味道的绝对还原,这是因为有更多中国人来到这里。过去的“洋中餐”,目标群体是本地人,现在似乎服务华人就够了。
2
见了好几个“走过来的”朋友。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家庭。男主人在2022年疫情严重的时候出发。他告诉妻子,自己要去南方打工。此后电话很难打通,再联系到他,人已经在南美。在热带雨林徒步的时候,他阳性了。
几个月后妻子带着孩子出发。从深圳到香港,然后到英国,再到墨西哥。这次旅途之前,她不但没出过国,甚至没坐过飞机。他告诉她,“和坐高铁一样。要相信别人,会有人帮你。”
真是了不起的旅途。
路上当然充满未知和危险,浪漫化这个过程是不应该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在法律和语言都不通的时候,还是能看到人性的力量。翻墙的时候,人们会先保证小孩,其次是妇女,然后才是男人。
经常有人抢劫。“他们只要钱,不会伤害你。他们也不会把你身上的钱都抢光,会给你留一点。”
3
纽约不是天堂,洛杉矶也不是。
如果在国内就很艰难,在这里会更有希望感。餐厅、仓库的工作不难找,熟悉一点可以送餐,再进一步可以开Uber 。
如果在国内的时候处在比较好的位置,反而大概率会感到失落。见到几位做生意的朋友,疫情的时候受到重创,但是洛杉矶的生意也不好做。
如果是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则不太可能从事原来的工作。如果你很有钱,每天享受阳光,也会厌倦。
偏文化和创造性的工作,更难转型,这时候就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经验、思想和体系,都更依赖“环境”。
4
丁胖子广场是很多人来洛杉矶的第一站。
这里非常简陋,不管是建筑还是那些小店的装修,都有点像国内县城老城区的汽车站。
这是洛杉矶的“最底层”,附近有二三十美元一晚的民宿,也可以解决电话卡等各种“第一天的困难”。
这里非常中国,包括各种套路。它也非常美国,因为法律在发挥作用。有救济(偶尔免费提供盒饭),也有各种“表达”。
这是国内没有的经验。它是一个“开始”的地方,可能有90%都属于“过去”,只有10%是新世界。
5
走进洛杉矶江湖酒馆,就像是回到了成都。进门的地方有竹椅,那是从成都运过来的。
周六晚上,我去了那里。前半场很中国,有好吃的东北烧烤。驻唱女孩选的歌单,是最近几年中国电视剧主题歌。后半场是电子音乐和蹦迪,也许“更欧美”。
一个白人小伙,据说祖上曾是在成都的传教士。他不懂中文,但是却喜欢中国的文化,那是遥远的、美的。
一位前竹联帮的大哥,从台湾来洛杉矶已经38年了。我问他什么是江湖?他说:江湖就是家。
他讲的第一个故事,是38年前的某个晚上,临行前和妈妈的谈话。“妈妈,我真的没什么别的办法了,要坐船出海。”不忍心问他,上次见妈妈是什么时候。
很难向外国人解释“江湖”这个词的意思。在洛杉矶,“江湖”既不是武侠小说里的那个“社会”,也不是过去国内的人脉和权力关系,它是个人从零开始的、新的社会联结。
一瓶科罗娜之后,我就回到了成都。这样说其实有点矫情,因为即使在成都的时候我也很久没有去酒吧了。
那些客人也一样。来江湖酒馆就是怀旧之旅。有一位朋友说,他有一阵子几乎每天都来,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美好的过去”。
一半是怀旧,一半是新生。“一切都在酒里”,这个“一切”是过去的一切;“新生”终究是困难的,
二娃冷锅鱼我是和两个读者朋友一起吃的。此前,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山东,却因为写作和对公共问题的关注而成为朋友。
我们想喝两杯,店员有点尴尬,过几分钟告诉我们,店里没有啤酒。
这里终究不是成都。成都的冷锅鱼,啤酒可能是利润率最高的商品,而在这里要卖酒需要专门的酒牌。这就是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