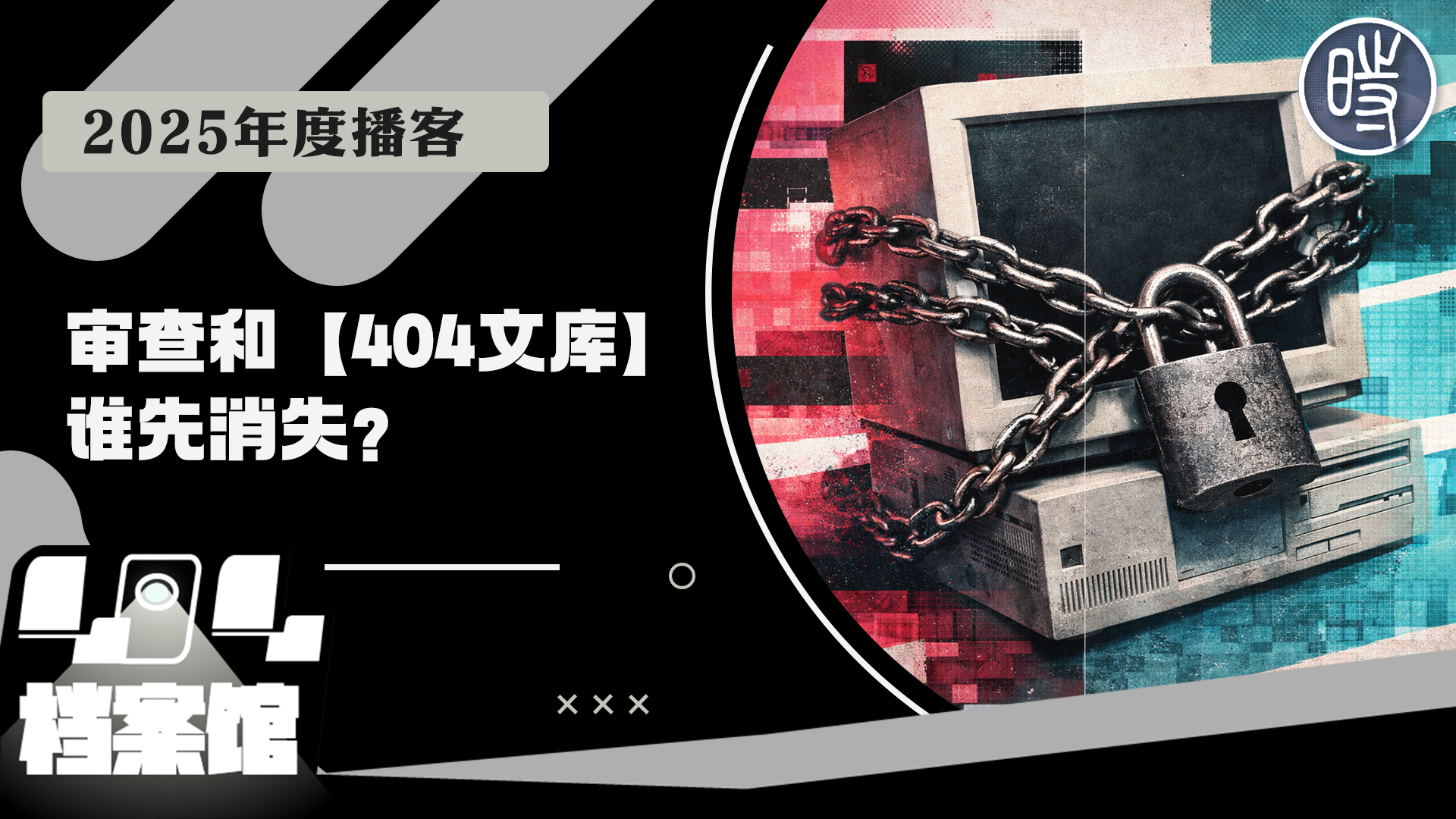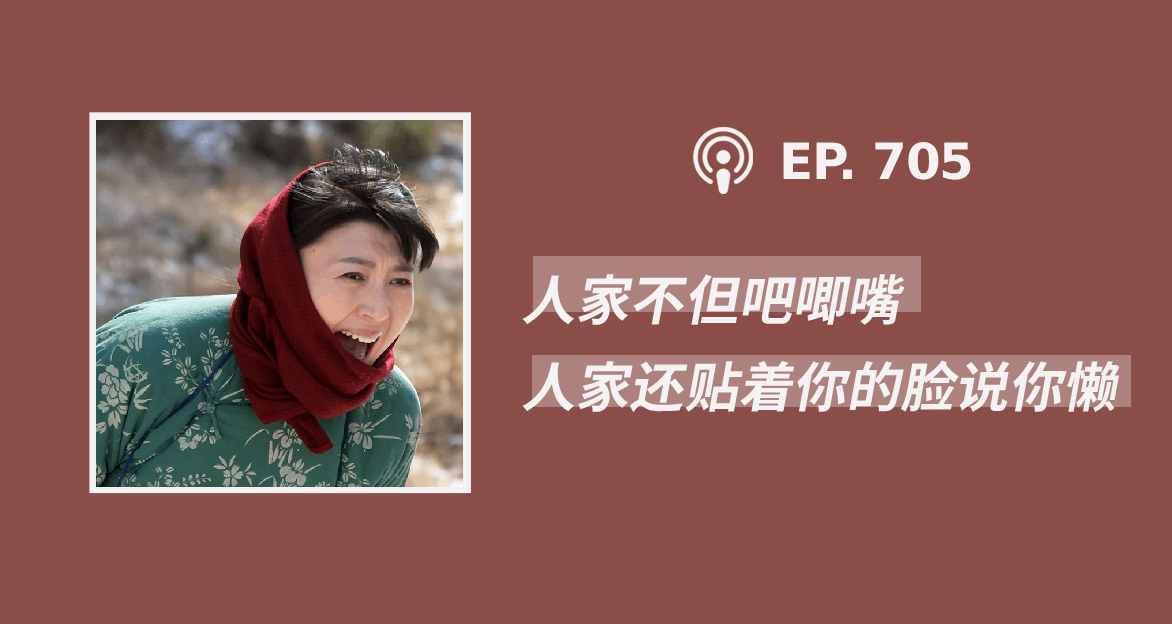成为一个口不出恶声的文明人是我对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似乎无法达成,几乎每天,都会跳出来一些忍不住想骂的人和事。骂人或许是一个人的本性,但却违背了我提高自身素质的意愿,这是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记录在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小说中的王二狠狠揍过他亲爱的朋友毡巴后,有些后悔,转而又想到:“但是他实在太可爱了,不能不打。”我引经据典的用意非常明显,是为本文接下来有可能出现骂人的话提前做铺垫和辩解:打人和骂人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实非我的本意。
在烈日曝晒的正能量荒漠上,总会有一些砂砾在能量下爆裂。5月28日,上海有名保安同志就突然爆裂了。是日早晨,他拦下了一位正在公园里朗读外国诗歌的青年,质问人家“中国五千年文化没有诗了?你为什么不读呀?啊!你为什么读外国的诗呀?”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责难,那位青年有点猝不及防,辩称他拿的诗歌集中“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保安训斥道:“我就没听到你读一个中国的,你为什么中国人不宣传中国的正能量……大家说中国有没有诗……你为什么抱着外国人来宣传呀?”
在我的想象中,上面的事发生之前,保安蹑手蹑脚跟在沉迷于诗歌的青年身后,跟踪了很久,希望得到文化的熏陶,但那位青年没有朗诵一首诸如“鹅鹅鹅”这样浅白的句子,这让保安同志感觉受到了智力上的侮辱,于是勃然大怒……至于“中国诗”,以他说话的水平,量来他也不懂,只是在不愿承认智力弱项的情况下随手捡起来的一顶帽子,意在打倒对方。以我这些年跟人“交流”的经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好比伊斯兰原教旨社会的石刑,越是在智力上一无是处的人越喜欢以“文化”的名义捡起石头,然后残忍地砸向让他们无法容忍的人。因为,只有在民族和国家的名义下,蠢人才能找到属于他们的精神归属感,借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人生。
借这个话题说说五千年文化的事。可考证的华夏文明史其实只有3600年,从《诗经》或《楚辞》开始,诗歌的历史满打满算3000年左右,有一些年代不可考的“远古民歌”,如《击壤歌》,看其写作手法,几乎可断定出自汉代。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中国诗歌的意思,事实上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诗歌,很多诗歌中都体现出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这一部分也是中国诗歌中最精华的构成。惜乎千载后的今天,这种超越的人文精神反过来被民族主义压制,甚至成为蠢货们反人文的武器。
《竹窗随笔》中有则故事: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广也。胡不曰:人遗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孔子“人遗弓,人得之”是一种的去国家化的人文精神,上海公园的这位保安同志虽然异常执着于中国文化,想必也无法理解。
正因无法理解,保安才会站在国粹的立场上频频使用“宣传”这个词。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宣传是一个需要战斗争夺的阵地,这意味着只要在争论中把“宣传”两个字抬出来,认知矛盾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事实上也是这样,视频中,朗诵诗歌的青年战战兢兢,活像软弱的敌人,而我们的保安同志则化身为雄赳赳气昂昂的斗士,气焰蒸腾,步步紧逼。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但照此敌弱我强的态势发展下去,那位青年大概率会丢下他的诗集,狼狈逃窜。
宣传的阵地在哪儿呢?前段时间跟一位旧友通话时,他认为我完全被“西化”了。我不接受他的说法。说句自大的话,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至少那些认为我被“西化”的人不可能胜过我。在今天,衣食住行等等,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已“西化”,不能“西化”者,唯意识形态与文化而已。其实儒家文化圈“西化”成功的例子不少,在这些例子里,传统文化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反倒是拒绝“西化”的地方,传统文化屡经意识形态的改造,变得面目全非。是的,传统文化这一块就是阵地之一,典型的战役是许多年来曲解国学的“国学热”。
我对保安这一职业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但这些年——尤其是疫情后,一些保安的气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蛮横自负,在管控过一段时间别人的人身自由后,如今又来染指别人的阅读自由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当历史机遇到来时,他们会像疫情期间随意闯入民宅的大白那样,随意地制造文字狱——以他们能搞明白的“文化”为名。
202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