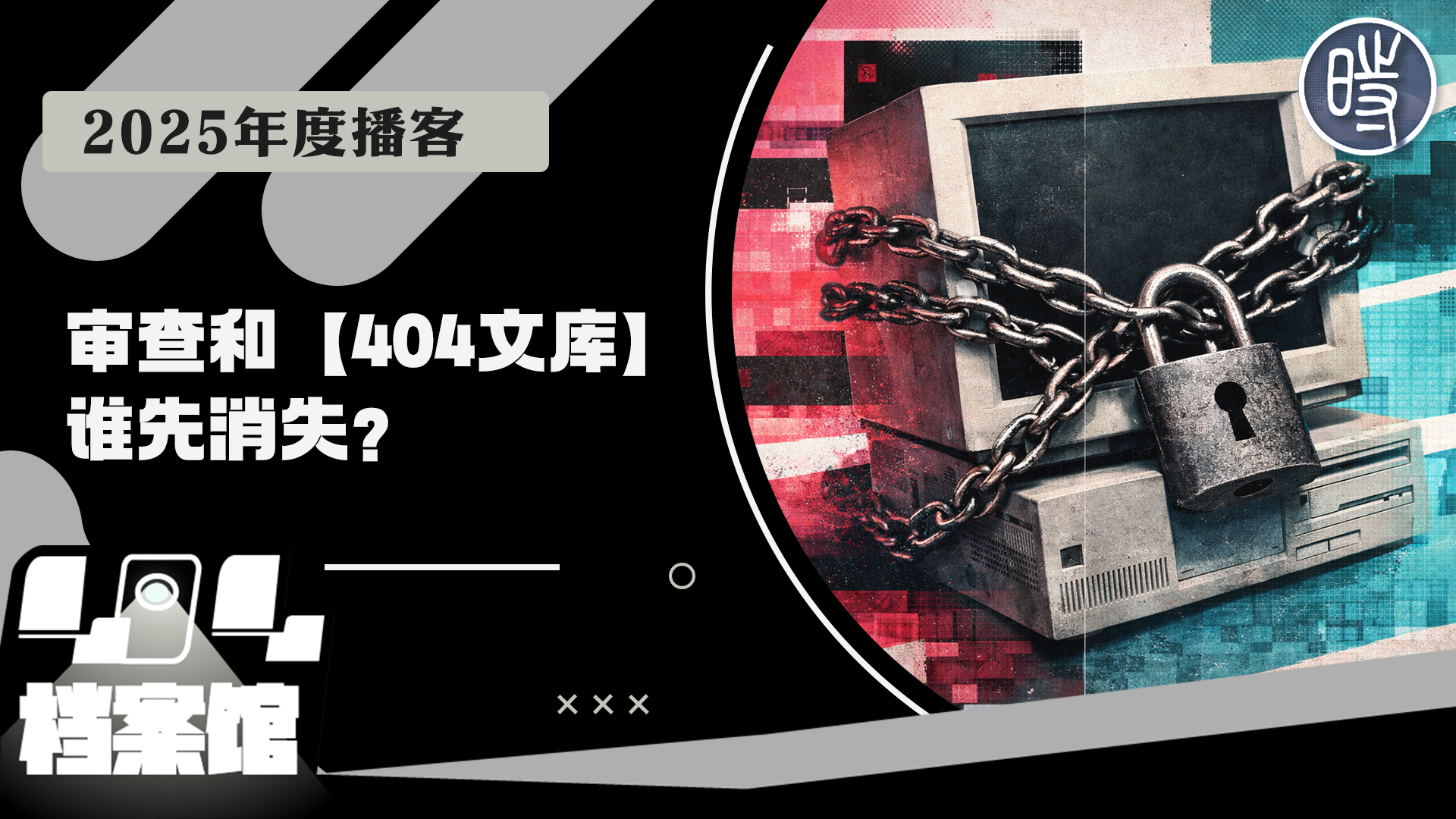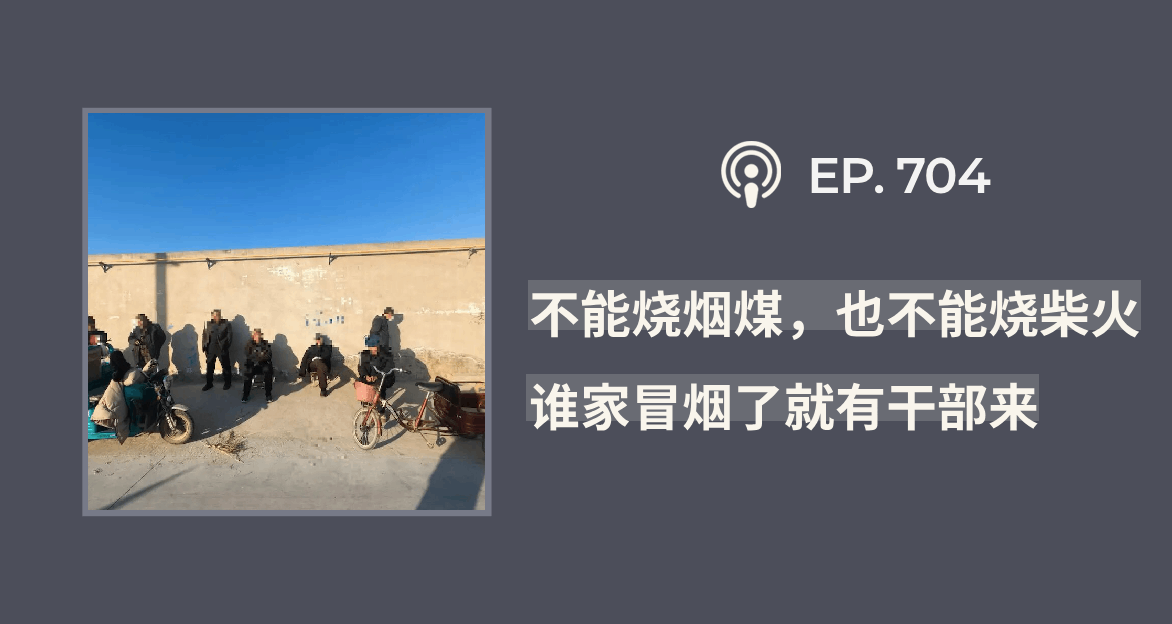编者按:2014年,美国记者、作家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在《剩女时代》(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一书中记录了中国女性面临的性别歧视。在随后的十年里,虽然中国废除了独生子女政策,但出生率和结婚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针对活动人士的打压持续不断,特别是针对女权主义者;针对女权的言论管控升级,线上空间缩小。为提振出生率,习近平在去年提出“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鼓励年轻女性结婚生子。为记录和分析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性别领域发生的变化,洪理达于2023年底出版了《剩女时代》修订版。本文是CDT英文记者对洪理达专访的翻译稿,原访谈发表于2023年12月。
洪理达是第一位从清华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除了《剩女时代》,她还著有《背叛老大哥:中国的女权觉醒》(Betraying Big Brother: The Feminist Awakening in China)一书,记录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她目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CDT此前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对洪理达进行过专访。
记者:Sophie Beach
翻译:AY
美国作家、记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
中国数字时代(CDT):《剩女时代》出版十年来,你在书中指出的新趋势或多或少都已发展为羽翼丰满的社会变革,因此新版《剩女时代》的出版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要特别指出,在第一版书中你谈到了中国女性开始恐婚恐育这一点。过去十年来,结婚率和生育率都急剧下降。人们对婚育态度的转变之快,是否让你感到意外?
洪理达:这种趋势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对书里写到的每一个部分都非常有信心。我当时就知道,并且在书中也写到了,那就是如果中国女性权利没有改善,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回避婚姻。仅从回避婚姻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对全国人口出生率和结婚率的影响,都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剧烈确实让我感到意外,它甚至让中国在去年第一次经历了人口缩减,现在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这个变化本身是巨大的。我对变化到来的速度和幅度感到意外,但对趋势本身并不意外。
在初版的写作中,我采访了许多20多岁的女性,其中包括2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拒绝进入婚姻的态度是十分激进的。当时与这些激进的年轻女性接触时,我感到非常吃惊,她们说“我绝对不可能结婚,婚姻在中国就像地狱一样”等等。我记录了她们很多人的故事。因此,我知道十多年前就有年轻女性持这样的观点了,只不过在统计数据里还看不出来。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初婚的平均年龄有所上升,但几乎所有的中国女性最终还是会步入婚姻的。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拒绝步入婚姻的现实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我的第二本书《背叛老大哥: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觉醒》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对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的真正觉醒,我称之为重大政治女权运动,我的书探讨了这项运动的诞生。这种对性别歧视的新觉悟、对自身权利的意识,以及想要为自己发声的欲望,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因此我写了第二本书探讨这个问题。
但当统计数字摆在眼前,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女性确实在明明白白地拒绝婚姻和生育,这仍然令人大为震惊。这让我感到振奋。在新版《剩女时代》中,我写到了十多年前进行采访时,我曾觉得心灰意冷。当然,当时就有受访女性说出“我绝对不可能结婚”这样的话,但我采访的大多数女性都没有这样的表达,她们在被动接受一种显然不平等的关系,一种在许多方面都不平等的关系。
这些受访女性都非常年轻,都是20多岁到30岁出头的年纪。她们告诉我,婚前就对自己的感情感到不满意,却还是选择步入婚姻,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或者她们会把自己的积蓄交给男朋友,用来购买婚房,而房产证上却没有女方的名字,房产通常是当代中国人手里最大的一笔资产,而这些女性被完全排除在这笔巨大的财富之外,她们接受了这种极端不平等的条件。我的书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这确实让我感到难过。我多次尝试问她们这样的问题:“你真的觉得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公平的吗?”“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段婚姻呢?”
但是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并不是她们的朋友,而是访谈者。我经常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想对她们说:“请不要按部就班举行婚礼,你不必这样做,你还很年轻。” 但许多受访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说,她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要她们步入婚姻。她们还告诉我最终选择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回到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前后,当时并没有一种主流的女权主义话语。这些女性私下里感到非常绝望,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不愉快,对这种不公正感到非常不满,但她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当然了,她们也有一些选择,比如有的女性一开始会选择反抗,与男友、未婚夫或者丈夫争执,希望房产证能写上自己的名字,但最后她们会因为各种社会压力而放弃,包括来自政府的压力,来自父母的压力——女方的父母在很多方面都对女孩不公平;最终,重压之下,这些女性只好放弃。因此,在后来重新审视这本书时,尽管女性权利有所恶化,特别是在婚姻制度内的女性权利总体上有所恶化,但我却感到更加充满希望,因为我看到个体女性真正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里,她们说:“不,我不必结婚。我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 尽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发生了很多负面的事情,但这一点还是给了我很多希望。
CDT:说到女性感受到来自社会、父母和政府的压力,你书名中的“剩女”一词就是贬低女性的词语,特别是政府也用这个词来形容快要满30岁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作为一种羞辱。过去十年里,国家宣传对女性和婚姻的态度是否有改变?此外,你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些,那就是更广泛的社会看法是否有改变,特别是女性自身的态度?
洪理达:(“剩女”)这种说法仍然在国家宣传中广泛使用。虽然在新闻标题当中不那么常见了,但我认为那是因为这个词已经太老了。最早在2007年,政府就开始推广这个词,那已经是16年前的事情了。因此,这个词本身作为一种负面的标签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当我去查阅最新的推动婚育的宣传时,我发现我书里记录下来的例子几乎无一例外仍然在国家媒体上流传,其中许多几乎是原文照搬,只是标题和内文的个别词汇有修改,这是国家宣传当中让我感到意外的部分。也就是说,推动人们步入婚姻的宣传仍然非常非常强大。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说中国需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这是习近平的原话。实际上,从2007年我最初进行记录到现在,这种趋势就一直存在。政府宣传的目标是一样的,但除了强力推动婚姻之外,今天的宣传还在强力推动生育。
我刚开始写这本书并且进行相关访谈时,中国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宣传的重点是推动女性走入婚姻,其中也有推动生育的部分,那就是一旦女性进入婚姻,就应该孕育一个孩子。但在我进行采访的那段时间,从2011年到2013年,政府宣传并没有说“你要生三个孩子”,而是“你必须在‘最佳生育年龄’期间生一个孩子”,宣传所说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4岁到29岁。也就是说,这种宣传已经在制造焦虑,用这种传播焦虑的手段吓唬女性,让她们觉得必须要抓紧时间结婚,不然就没有男人要她们了。还有就是制造关于小孩先天缺陷的焦虑,就是说如果你不在20多岁的时候抓紧时间生孩子,那你以后生的孩子就会有缺陷。到了今天,由于中国已经实行三孩政策,政府宣传在非常强势地推动生育。而推动婚姻显然是现行政策中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的人口工程计划仍然完全不鼓励单身女性生育。一个人必须进入婚姻,因为婚姻被认为是一种维持政治稳定的体系。而且这种婚姻仅限于异性的结合,同性婚姻仍然是非法的。推动男女进入婚姻关系是政府促进政治稳定的一种方式,只有在婚姻关系当中,人们才有生育的自由,而且现在还要大力推动人们生三个孩子。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宣传。
总的来说,我认为现在的宣传语调的厌女程度仍然是惊人的,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正面”的宣传,宣传一个年轻女性能够过上怎样的快乐生活,这种宣传是非常荒谬的。《人民日报》有时会刊登一些报道,说年轻女性在上大学期间就可以生孩子,这简直是荒唐透顶的,“看吧,趁早当妈妈是多么快乐的事啊,你可以边上学边当妈妈!” 同时这里面还有惩罚性的元素,那就是“你最好抓紧时间,不然就赶不上了,你就永远嫁不出去了”。但因为“剩女”这个词本身已经太老了,放在新闻头条里面已经失去了引发焦虑的作用,人们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了。
从惊人的统计数字当中可以看出,出生率和结婚率多年以来在持续下降。从2013年以来,结婚率在逐年下降;从2017年开始,出生率也在下降,也就是说年轻女性更多地把政府宣传当耳边风,她们在志同道合的女性社群中体会到团结一致的氛围。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书中有很多关于LGBTQ+社群的内容,这些社群之间有很多交集。我采访了很多年轻的酷儿男女,了解这种鼓励婚育的政策和宣传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拒绝接纳这样的宣传,这非常好,让我感到充满希望。
但让人悬着心的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强,而且会越来越严峻。现在很多宣传的目标人群是老一代人,也就是父母那代人。推动一个女儿步入婚姻最有效的压力往往来自父母。我书里写的一些最让人难过的例子(都是父母的压力),比如有一位母亲威胁说,如果女儿不结婚,她就要跳楼,这个故事里的女儿甚至都没到30岁,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当然,男生也面临结婚生子的压力。但我在研究中发现,女生面临的压力要强得多,针对女生的宣传也要多得多。尤其是父母给的压力,作为女儿,这种压力是很难甩掉的;如果她深爱自己的父母,希望让他们骄傲,那么当父母说“你必须要结婚,免得我这么痛苦,我这么痛苦都是你造成的”时,这种压力是直接针对她个人的,带着非常强烈的情感色彩。年轻一代可以把政府的宣传当耳边风,但要他们完全不在意父母和家人的态度是非常难的。这种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强,情况会越来越严峻。
除了新实施的三孩政策外,政府还大大提高了进行输精管结扎术的门槛,并且多次微调有关终止妊娠的规定的措辞,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一点,那就是接下来会出台哪些关于堕胎的限制呢?我认为并不会在全中国范围内禁止堕胎,(如果有这样的政策)人们会有强烈的反弹,特别是年轻人。但女性面临的困境会十分严峻,特别是面临这种压力的20多岁、30岁出头的女性。我认为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干预,对于家庭和年轻人的私生活的干预将会变得越来越强。
CDT:可否请你谈谈在从一孩政策过渡到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优生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特别是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女性而言?
洪理达:这个问题是本书写作至今发生的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剩女时代》中我确实提到了优生学,在我研究“剩女”相关的所有宣传活动时,我发现这个词特别针对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汉族女性,她们属于主流民族,宣传活动特别针对的是20多岁、30岁出头受过教育的汉族女性,推动她们进入婚姻。从宣传中使用的语言和图像,都能明白无误地看出目标对象是谁。宣传中使用“高素质”一词,说高素质的女性应该结婚生子。通过采访和分析,我提出这个观点:这场宣传不仅仅是为了促进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进入婚姻,同时也是为了“提升人口素质”服务的。因为就在2007年那场关于“剩女”的宣传攻势之后不久,中国国务院就出台了一项决定,其中提到中国面临人口“素质低”的严峻问题,称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挑战,必须“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为了给未来培养高技术工人群体。
当时在新疆并没有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压迫和拘押,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新变化。2017年是一个转折点,新疆不仅出现针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押,还有特别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女性的强制绝育运动。当时政策允许这些女性生育三个孩子,而如果她们已经孕育了三个孩子,就会被强制植入宫内节育器。当时政策允许少数民族家庭比汉族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在新版书当中,我加入了一段文字探讨这个情况,我采访了一名从中国逃出来的维吾尔女性,她讲述了自己被强制绝育的恐怖经历,而且她在被强制绝育之前还遭遇了无理羁押。
中国在2017年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时,中央政府宣布所有的已婚夫妻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也就是说针对汉族夫妻的生育限制放宽了,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这反而是对生育权的严格限制,因为在2017年之前,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三个孩子。而且实际上,地方政府以往对许多超生的少数民族家庭并不追究。很明显,优生学是中国人口工程政策的一部分,这一点已经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了。政府以前确实更加明确地追求人口优化,但现在这种政策仍然是存在的。
通常,政府所担心的出生率下滑,指的是汉族人口的出生率。但如果我们看看新疆的出生率,从2017年开始,这种下降是更为显著的,相关研究已经很丰富了。这是强制干预的后果,包括使用强制堕胎和绝育手段。这正是优生主义人口计划的实际操作,因为这些女性被看作是潜在的麻烦,被认为是“低素质”的。中国的官方宣传称新疆的高出生率是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但与此同时,在谈到汉族的低出生率时,官方又说这同样是社会稳定的威胁。由于性别比例失调,有成百上千万的男性找不到妻子——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人,多出来的这些男子无法娶妻。所以说,对社会稳定的执着是一直存在的。这是过去十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
CDT:还有一个问题,你的书着眼于女性拥有房产的比例较低这一现象,以此体现她们面临的其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在新版《剩女时代》中,你提到过于十年女性拥有房产的比例所有提升,但也指出她们已经错过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增长期。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正面临危机,几个主要的开发商都在债务上出现违约,房地产泡沫在破裂。这场住房危机对中国女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洪理达:中国女性没有赶上房地产繁荣期间的巨大财富积累,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中原因有性别歧视、政府政策、家庭内部的歧视等等。在房地产市场不再繁荣的背景下,有调查显示现在有更多单身女性在以个人名义购房。虽然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支持,但我担心现在这些房地产开发商找不到人买房,而单身女性是有购房需求的,她们等待购房的机会已经等了十多年了,但以前房价太贵,令她们望而却步。所以如今我们确实看到更多单身女性以个人名义购买房屋,只要房地产市场不彻底崩盘,这对女性而言就是好事。我认为房地产市场是不会彻底崩盘的,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而是受到国家支持的。国家不会愿意房地产崩盘,尤其是居民住宅市场。
年轻女性在更多地思考如何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从人口学角度而言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她们想要更多的独立自主,不想结婚,也不像以前那样想要小孩。她们想要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显然看准了这个机会,在针对那些想要经济独立并拥有独立住房的单身女性进行营销,也就是说开发商将目标定位在这一人群上。但同时,消费者购房仍然面临种种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已婚人士购房通常仍然要容易得多,男性购房也比女性更容易。买房本身也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没有户口,想要买房仍然非常难。目前,在上海如果没有户口,作为单身女性是没有办法购房的。当然,这个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有更多单身女性购房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年轻女性确实在尽最大努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也是让我感受到鼓舞的事。
CDT:在书的前言中,你写道你最初的研究和相关文章曾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此外,你的第一版书的中文版也在中国发行了,虽然有所删节。在今天,很难想象这样的出版物能在中国流通。能否请你探讨过去十年更加严格的审查制度对你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外,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在过去十年里,审查制度如何影响中国女性表达自我、获取信息以及在线上空间里找到彼此?
洪理达:这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谈。首先,如果我想回到中国去再做一次这项研究,那绝对是做不到的。这个研究需要大量资源,规模很大,有成百上千受访对象,其中包括很多面对面的访谈。但我最初是依靠微博这个平台来招募受访对象的,大约有1000人给了我反馈,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不得不暂停接受新的受访者。接着我请这些人使用我创建的一个电子邮箱进行沟通。对于无法面对面采访的人,我通过网络进行了访谈。同时,我也通过微博私信进行了一些采访。而今天再看,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现在的监控实在是太严密了。作为学者,如果你人不在中国境内,那么你能获取的东西就非常有限;但如果你人在中国,那么你就会受到你所在的高校以及中共更为严密的监控。现在的监控比我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时要严格得多。如果我现在申请这个博士项目,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被录取,也无法想象自己的论文题目能在清华大学通过。这是一个方面。我也与人在海外的人进行了一些新的访谈,并且雇了几名研究助理帮我进行了一些采访。我不希望这些新的访谈影响到任何人的安全。但我之前做的那些采访确实都是站得住脚的。
说到中国网络审查,目前针对女权主义的大规模打击行动正在进行中。许多女权主义者的个人账户遭到删除,女权话语受到严密审查,比我2011年开始做研究时的情况严重得多。那时候微博才刚刚起步,是“微博的春天”;虽然当时也存在网络审查,但人们的表达是更自由的。在2011年、2012年甚至2013年,网络上仍然有很多活跃的表达。
到了今天,虽然政府在大力进行审查和监控,虽然有针对女权主义者的打击行动,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仍在网上找到了空间,亮明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继续进行对话,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非常吸引人的现象。这些女权主义者不那么公开强调女权主义这个标签,而是直接去参与到一些具体话题的讨论中,比如“我真的不想结婚”之类的话题。这样人们就更容易找到其他不想结婚的年轻女性的线上社群:如何应对父母催婚?回家过年的时候如何应对家庭的压力?各种亲戚不断追问你“为什么还没结婚”的时候怎么办?这类讨论仍然相当活跃。这表明公民社会并未完全消亡。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关于中国的女权主题讨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但像日本社会学家、女权主义者上野千鹤子的书籍却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十分畅销,这些书讨论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女权主义。她的书并没有明确谈到中国的女权问题,而是探讨日本的问题,以及抽象层面的的性别不平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尽管中国当局迫害个别女权活动人士、压制公开的女权话语,但女权主义在中国已变得更加普及。而在线下世界中,人们不能在街头进行活动人士所说的女权行为艺术,这也是我在初版当中就写到的内容。一些女权活动人士曾在街头进行行为艺术,吸引人们关注家庭暴力或性骚扰等问题。现在这样的街头行动已经不能做了。这些灰色地带让我在阴郁的政治大环境中仍然对中国年轻一代抱有希望。
CDT:你的回答已经基本上涵盖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否还有想要补充的呢?过去十年当中,有没有哪些改变表明中国女性在进步并让你感到充满希望?
洪理达: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2022年底发生的“白纸抗议”,那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虽然总体而言参与街头抗议的人群并不庞大,但中国多个城市都有人上街抗议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有那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其中有人呼吁习近平下台。这其中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也是很多报道都提到的,那就是许多年轻女性站在了抗议的最前线。这再次显示出中国年轻女性对性别歧视和不公的深深的不满。面对政治风险,女性挺身而出受到的损失比男人要小。在甘冒政治风险的年轻人里,女生越来越多。一方面,这让我感到充满希望、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当然,我也对当局接下来可能采取的措施感到担忧。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海外女权主义社群的迅速发展。这也是互联网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方式,社交媒体仍然是打破地理边界交流的工具。当许多中国的年轻人选择出国留学或移居海外时(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离开中国,这种现象被称为“润学”),就出现了其他国家为这些年轻人发放签证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和LGBTQ+群体愿意作为公众焦点,领导抗议活动,并建立了一个女权主义社群,不仅在海外活跃,还与中国国内积极互动,现在这个社群已经很庞大了。这让中国政府对把年轻女性和女权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去实施控制,因为现在和过去的情况不同了,过去通常是个别的、以男性为主的异见人士会获得人们的关注,然后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失去影响力,就像天安门一代那样。而新一代的女权活动人士认同许多女权主义的原则,相信平等权利和LGBTQ权利,同时也相信人权,这个群体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挑战。
这是另一件让我感到充满希望的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有时候极其残酷。他们可以通过再一次大规模抓捕年轻的女权活动人士来吓唬普通的青年女性,但我觉得这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争取20多岁到30出头的受过教育的汉族女性站到政府这边来,让她们结婚生子。怎么可能一边大规模抓捕女权主义者,一边又做到这一点呢?所以我认为未来确实会有真正的抵抗空间。由于新一代人更加明白要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要站出来发声,并且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没有人能预料下一个类似“白纸抗议”事件会在什么情况下被触发。这是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考虑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充满希望。再说回到维吾尔人的情况,不幸的是,维吾尔人处于明显的少数,而且目前大多数汉族人并不真正关心维吾尔人的境遇,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会因为侵犯维吾尔人的权利而受到惩罚。但我认为当局没有办法把这一套用在所有中国人身上,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