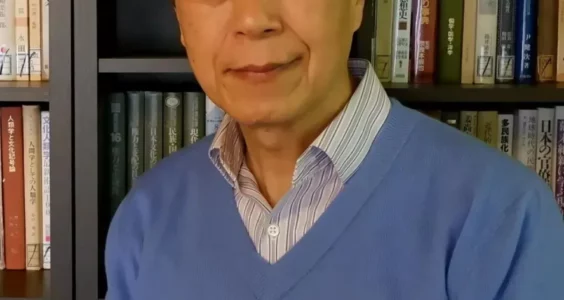编者按:目前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小粉红”言论甚嚣尘上。不少评论人士将这一情况和二战前的日本进行对比。近日,波士顿书评转发了一篇对旅日学者、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专访,解析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建构和歧路。以史为鉴,这篇专访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当下的中国。
短短几十年中,日本在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上迅速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发展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忠君思想,并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将世界和自身都卷入战争的泥潭,给人类文明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这其中,历史又能给我们以怎样的启发?2022年5月,记者对话王柯,交流有关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主义和近代日本政治等一系列话题。访谈首发南都观察,经作者和王柯教授授权,波士顿书评转发。
在访谈中,王柯指出,“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
1、自由民权运动阶段: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日本在19世纪开始引入“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等概念。此阶段民族主义的内涵偏重个人自由与平等,但这一阶段的民主化尝试因缺乏对西方思想的深入理解而受到限制。
2、国粹主义阶段:随着明治政府确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逐渐与文化共同体的概念相结合。德国式国家主义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天皇制国家的中央集权属性。
3、国体论阶段:日本民族主义最终以“天皇神圣性”与“血缘共同体”为核心,构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
王柯强调,现代意义上的“nation”原本是法国大革命中追求平等与自由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但在日本,它被改造为强调国家至上与忠君思想的“民族”观念。这种转变反映了日本政治精英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选择。
之后,王柯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如何从民族主义发展为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天皇为中心,强调国家至上的国体论是核心驱动力。王柯指出,明治维新后的底层武士群体借助民族主义完成了社会上升,而这些精英通过军队体制积累了特权,最终在20世纪推动了日本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道路。
国体论源自江户时期的古学学者本居宣长和贺茂真渊等人,国体论主张,日本在国家形式上是一个具有“皇运无穷、天皇神圣和忠孝一体”三点特征的“神国”。所以在江户幕府的体制之下,国体论是受到打击的,因为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的手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向中央集权体制,需要一个具体的国家统合象征,国体论中的“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等事项迎合了这种需求,而之后出笼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将国体论变成了日本的主流国家思想。
国体论将全体国民在生物学上说成是一个“血缘共同体”,但实际上从日本国家的规模来看,这本来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皇国论”、“神国论”,以及天皇血统的“万世一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虚构和宣传,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江户时代“人民只知有大名,而不知道天皇和中央政府”的意识,培养日本国民对日本国家的忠诚。
当历代天皇是你的祖先,而现在的天皇可以说是你的堂兄堂弟时,你怎么能不去保卫他呢?当把“日本民族”塑造成一个地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以后,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定型。
日本之所以会由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走向军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具有政治野心的日本军人、尤其是“青年将校”(青年军官)们,逐渐成为以“国体论”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载体。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来自于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底层武士。在地理上,这两个藩都属于边缘地带,而因为德川幕藩体制的崩溃,武士阶层的传统阶级上升途径消失。既处于地域边缘,又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武士都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捷径,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为维新政府的军人。近代日本军队的阶级制度和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制度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权力与权威的金字塔。尤其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直属于天皇而不是政府,这更使军人变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身于地方武士家庭的中下层军官发现,自己的家人并没有能够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而日本政府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也表现得软弱无能。这时他们发现,可以借以国体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口号,名正言顺地“清君侧”和“下克上”,甚至刺杀天皇身边的元老和重臣,提高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就这样,国体论为这些出身于边缘的军人群体,提供了一个干涉政治的合法手段,使日本逐渐由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军国主义的阶段。
此外,王教授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也是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的关键。哲学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的“物竞天择”思想被日本政治精英改造为“国家竞争”理论,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此外,统治者通过煽动危机感,迫使社会进入“无责任体制”,普通民众和政客放弃了自主判断,最终导致战争灾难。
这一变化的发生,还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传入日本有着直接的关系。1880-90年代中,日本翻译了许多斯宾塞的著作,甚至被称为“斯宾塞时代”。近代日本社会在接受斯宾塞进化论思想上,是各种思想流派各取所需。自由民权运动强调其自由主义的侧面,而明治政府和国家主义者们强调其保守主义的侧面。
在达尔文那里,进化论“物竞天择”的单位本来是个体,但到了斯宾塞,单位被换成了国家/社会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斯宾塞强调,国家间的关系就像自然界一样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正如列文森所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法则,使国家在生存竞争中成了最高的单位。”
社会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说,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理论根据。这种思想对加藤弘之、德富苏峰等自由主义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纷纷转向,抛弃社会契约论立场而转向社会进化论、转向国家主义。
但是究竟是以“主权在民”思想还是国家主义主导日本国家的未来?这一明治晚期就已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完全消失。到了大正时期,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只不过是一个行使统治权名义的机关,而实际的统治权则属于法人的国家。美浓部达吉的观点之后遭到了日本的右翼,甚至是海军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的猛烈攻击。
同样在大正时期,还有很多人对国体论也进行了隐晦的反思。思想家吉野作造提出的“民本主义”也是出自这一目的,它其实是日本特殊国情下民主主义的改良版本,但是为了避免与国体论者之间发生争议,吉野甚至避免使用“民主主义”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