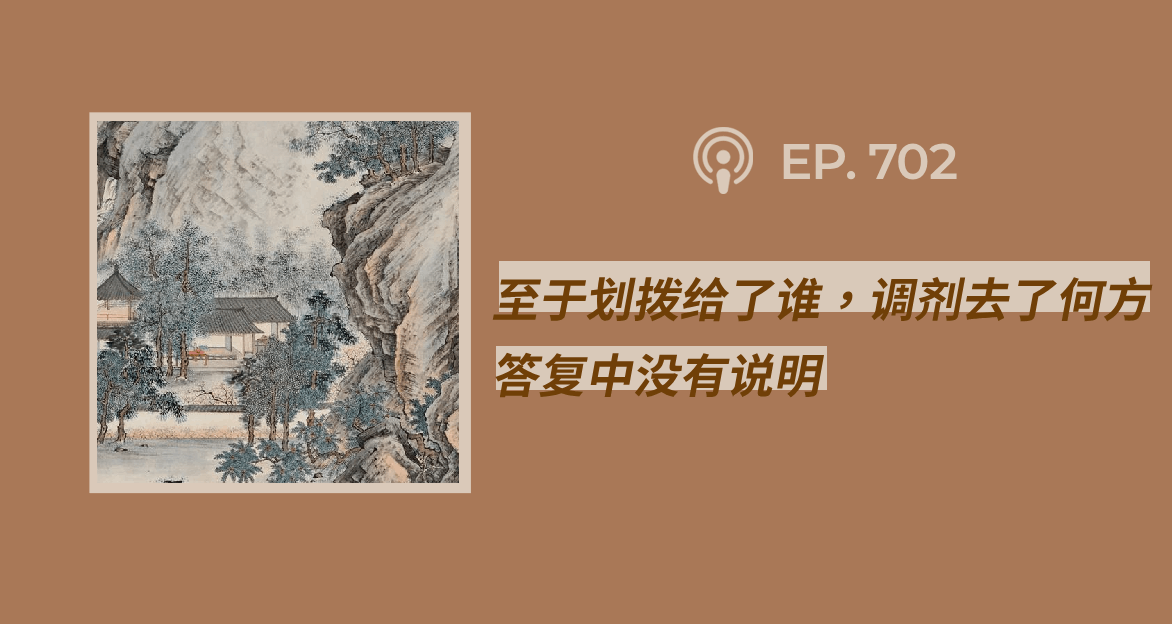刚才我看到乌鲁木齐文旅局的一个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中说,当事人郭珍明在湖南拍了一部名为《混乱与细雨》的纪录片,这部影片未获电影公映许可证,他曾携影片参加德国柏林电影节,随后,郭导演又跑到了新疆去旅行,并拍摄了一些当地的素材,存于硬盘内,尚未制作成电影。
新疆的相关部门认为,既然郭导演曾经把湖南拍的影片送往德国电影节,那么这次在新疆拍摄的硬盘素材,也有理由认定应为电影,于是:
没收摄影机和硬盘,罚款7.5万。
这是对电影的跨省追捕吗?
新疆的广电局直接认定,这些素材的电影属性无须成片,更不必公映,只要导演有前科、曾送过类似影片到海外展览,那这次的拍摄便可一律按电影算账。
处罚决定写得一本正经,认定理由赫然是:
“当事人拍摄的作品未成片,付费聘请演员,预计片长60-80分钟,成品画幅16:9,并计划公映或参加影展,符合电影的定义。此外,其曾将同类影片送至国外电影节,进一步印证了其拍摄行为的电影属性。因此,郭珍明拍摄的作品应认定为电影作品。”
你都知道他未成片,怎么就能认定是电影?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面的逻辑漏洞——郭导演在湖南拍的片子,居然成为了新疆判定违规的:
类推理由。
换句话说,只要导演曾在其他省份拍过片,新疆都可以合理怀疑、合理罚款。
按这个逻辑,中国的导演和摄影师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困境:只要曾经有过参展、参赛或境外展览的经历,不论你在哪里旅行、用什么设备拍摄,都可能自动转化成电影,随时面临处罚的风险:
难道摄影机在手,天下都是电影之敌么?
乌鲁木齐还十分严肃地开出了具体清单: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整,没收导演拍摄用的硬盘一个、摄像机两台、收音笔一支,以及两块滤镜和一台灯光设备。
这一纸罚单,字字掷地有声,透出一种决不姑息的架势,好像真的抓到了一个全国流窜的:
非法电影犯。
但细看处罚的法律依据,却只能用四个字形容:“似是而非”。毕竟,一个电影的认定需要作品的完成度,需要公映许可或至少是明确的放映意图。而现在,仅凭湖南的拍摄和德国的参展,就能跨越千里罚到新疆,监管尺度之宽松,让人瞠目:
他在湖南、德国哪怕做了再伤天害理、人神共愤的事情,跟你新疆有半毛钱关系吗?
再往深一步想,电影创作的边界究竟在哪?导演的相机究竟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如果仅仅因为“怀疑”导演会做电影,新疆便有理由作出处罚,那今天拍风景的摄影师,明天拍旅游短片的博主,后天记录家乡风俗的自媒体人,是不是都随时可能被纳入处罚名单?
事实上,这种看似严肃实则荒谬的执法逻辑背后,是一种对边界的刻意模糊化,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过度警惕,更是一种自我设定的无尽的:
行政扩权。
毕竟,权力的边界一旦变得模糊,权力本身的舒适区便会越来越大,而被执法的个人和创作者,则处于不断收缩的自由空间。
荒诞不经的处罚背后,是创作者日益缩减的自由。以“跨省怀疑”式的执法方式惩罚创作,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具体个体,更是对文化生态的一种损害。因为,当创作者的相机举起时,心里总是要忐忑一下:
这个动作,会不会在另一个省份引来罚单?
艺术创作本来需要自由的空气与宽容的环境。一旦权力的尺度变得随心所欲,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何谈优秀作品、何谈文化发展?更讽刺的是,在我们不断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却以如此方式阻碍艺术创作的生长空间,让人不得不感叹:新疆的这一纸罚单,不仅罚了导演,也罚了艺术创作本身。
湖南拍片,新疆罚款。听起来似乎滑稽荒诞,背后却隐藏着创作自由日益压缩的困局。这种荒诞如果继续下去,只怕下一个“被非法电影”的,会是你我身边拿着相机、手机的每一个人。
写于2025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