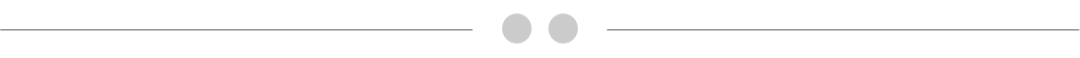伍尔夫曾经对她的传记作者奈杰尔(Nigel Nicolson)说: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没有什么算真正发生过,直到它被描述出来。)
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并不觉得多么犀利,直到最近,几件“这也能成为争议话题”的热门讨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譬如,一条女款裤装的口袋。多么小一件事情,和它的尺寸一样,装不下世界任何的关注,却像裤子上的虱子悄悄折磨着它的主人们,让她们手忙脚乱,捉襟见肘。长久以来,它就明晃晃地摆在每一间商铺和衣柜里,但直到最近被人摆在台面说出口,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因为女性都爱多带一个包。
又譬如,高铁售卖卫生巾的网络讨论。假如没有这场讨论,许多人根本不会想到,这居然是个需要争辩的问题;而另外的更多人不会意识到,许多人的生活中居然存在着这些问题。
一旦进入伍尔夫的视角,我们仿佛看见,女性好像生活在一个原始时代。在这里,大量重要的事情发生着,但用来描绘它的词语还没有被发明,人和人之间,尤其是不同性别之间,甚至无法交流一些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结果就是,女性成了“一个谜”,而不是一个人。
这一切并非偶然,“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
今天,从“卫生巾”等事件出发,借由一本口碑高分书籍《看不见的女性》,通过多个议题和数据分析的角度,我们试图探讨,在这个以语言为文明核心、精心打造的系统里,作为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是如何被无视、被消声。在当下的种种讨论之中,又存在着哪样语言与思维的陷阱。
01. 数据是这个时代的神学,女性在其中隐形了
在高铁售卖卫生巾的争论当中,“昆明高铁App上卫生巾累计销量超过12000包”的事实成为了关键论据。另一方面,许多反对售卖卫生巾的讨论,也似乎从理性和数据的角度出发,比如“不卖卫生巾就是因为利润率不高,自带卫生巾的女性也很多,如果市场有需求,那就自然可以卖”。
这个时代,“理性”是最被推崇的思维,数据则是巴别塔上最通用的语言,所以我们的描述就从数据开始。
四五年前,如果你想要找一本科普读物来系统了解女性月经的相关知识,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很难找到合适的选择。相比之下,在电线杆上和电梯屏幕里男性生殖广告之普遍和广泛,几乎让女性们都熟悉到能随口说出几个具体症状。
这个对比永远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认同。因为最大的不公不是由谎言造就的,而是由不存在本身。
上个月,有一本新书的中文版面世,名字叫《看不见的女性》,《金融时报》前主编的推荐语很有意思,他说,“卡罗琳·佩雷斯简直是掌握数据的西蒙娜·波伏瓦。”
豆瓣网友的评论更直接些,“堪称讨论女性权益问题时的论战数据库”。这本书从女人的身体、女性的无偿劳动和女性受到的暴力三个角度,梳理出许多重要数据、涵盖科学、经济、建筑等被认为是非常客观的领域,来体现世界一半人口被无视和消声的事实。
在《看不见的女性》里,展现大量数据和例证,比如:
-
自1990年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将Y染色体确定为决定性别的“唯一”区域以来,女性性别一直被视为默认的性别——这一点颇为讽刺。但在这种情况下,默认并不意味着我们关注女性。相反,研究把重点放在睾丸的发育上,认为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女性的性发育则被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直到2010年,我们终于开始研究卵巢发育的主动过程。
-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决不能有作曲的愿望——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又凭什么指望自己能这么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错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经做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纪最成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人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
数据被现代世界标榜为理性的典范,它允诺公平,客观。临床试验说明这个药物有效,统计报表证明你对经济贡献有限,你怎么能质疑数据的裁决呢?
数据也许是客观的,但选择怎样的数据,选择从哪个角度来统计数据,选择如何运用数据的,却从来都是人。
通过让人出现在某些表格里,不出现在另一些表格里,所谓“铁一般的事实”就可以马上成为另一种模样。高铁上的卫生巾销售量大可以归到“卫生用品”甚至“其他”里,轻轻松松消解掉我们唯一的数据论据。
但数据不是系统本身,只是系统的一层“皮肤”罢了。我们最该问的是,为什么往往是女性要用数据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以至于《看不见的女性》作者需要搜集如此多的论据,去证明女性遭受的明显不公,伸张类似于在药物试验中要包含女性样本和数据,这样显而易见、诉诸直觉和良心就该足够的权利。
况且,数据和理性,往往被认为是与女性无关的领域。但如果回看历史,所谓“女性不擅长数字”根本就是一种歧视和偏见。
历史上第一个程序员是女性——爱达·洛芙莱斯;而就在不久以前,当数字工作还被认为是枯燥,缺乏创意时,统计分析的差事也是交给女人去做的。更加不要提女人一直被认为“斤斤计较”,适合管理家庭内部的账本。
那怎么一旦数据变成时代信仰,女性就不擅长它了呢?世界无需解释。倒是想要反驳它,需要女性自己搜集证据。
在《男性统治》里,布尔迪厄为我们作了解释:“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男性不需要争取火车上出售他们更喜欢的物品,不需要要求车辆安全气囊应该以他们的标准身型做设计,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在叙述受尊敬的时代,是男人具备文采和浪漫,而数字大行其道后,人文学科就成了“不擅长数字和逻辑”的女性避难所。
根本的问题,并不出在数据身上,而在那些看到昆铁的销售量后仍然嗤之以鼻,认为这个话题不值一提的想法源头。
02. “常识”有害
许多热议言论认为关于卫生巾的讨论不值一提,因为“这是女人的事儿”,不该放到公共领域,太“占据公共资源”。
即使在这几年性别议题逐渐被人所接受,不管是媒体、知识分子或是普通言论中,“这是阶层问题不是性别议题”“为什么什么都要扯到性别”的言论从不少见。
翻看许多“重大事件”的讨论,地缘政治与经济制度,白宫和火星的最新动态都被认为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大事。为什么他们会觉得,30亿女性的身体健康和尊严福祉,算不上事关人类文明的重要命题呢?为什么在如何看待眼下的战争和去火星的未来这件事上,他们觉得不需要同等听听女性角度的意见呢?
书店里的陈列早就透露出答案:经济/政治/科技/…女性。女性和其他事情一样,是人们研究的其中一个“对象”而非研究“主体”。
翻译一下,如果人类文明是个游戏,男人和女人并不都是人,男人是默认主角,而女人像是同等数量的NPC,是主角会遇到的事情或完全忽略的神秘自然景观。
一旦接受了在文明中“女人是对象,不是人”的设定,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现实中总是会出现“有女人是女人的错,没女人是没女人的错”这样的逻辑谬误。毕竟主角的需求永远是对的,如果不对,那就发明一套新的理论。
《看不见的女性》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创业者珍妮卡·阿尔瓦雷斯为她的科技初创公司筹集资金。在一次会议上,投资者在谷歌上搜索相关产品,结果进了一个色情网站。他们便在页面上流连,开始讲起了笑话。
但当她推销自己的产品时,其他投资者都觉得“很恶心”,碰都不敢碰她的产品,或者“自称对产品一无所知”。那么,阿尔瓦雷斯推销了什么“下流、恶心、令人费解”的产品呢?一个吸奶器。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女装口袋、卫生巾议题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占用资源的讨论”,即便它的商业价值巨大,现有产品未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可依然没有投资者(主要是男性)愿意去投资。
某些女性需求是男人不会考虑去满足的,因为这涉及男性根本不会拥有的体验。如果一个人自身没有这种需求,那么要让他相信这种需求客观存在,就并非易事。
但其实,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月经被列为身体的重要信号之一。它的重要性跟我们的心率、呼吸、体温是一样的,是展现身体健康的有力迹象。
但这方面的研究不会被现有商业体系所考虑,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其中存在一种思维误区:
关于“人类未来”的科技和创业公司里,往往男性占主导地位,在针对女性的科技领域,数据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毕竟,如果女性没有很好的数据,而对方(男性)又没有亲身经历,就很难打开他们的思维,使其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问题。
但荒谬的是,在一个对女性身份(因此不能期望符合刻板的男性“模式”)特别不利的领域,数据对女性从业者和企业家来说尤其重要。然而,女性企业家又不太可能拥有它,因为她们更有可能尝试为女性生产产品。而我们恰恰又缺乏女性的数据。这是一个逻辑密闭的死循环。
在一个怎么说也有50%是女性的世界里,为什么男性默认思维如此普遍?
学者克罗克特对此有一个解释,因为“假设我们自己的经历与人类的总体经历一致”,是人类心理的一个特征”。
这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称为“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或“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本质上,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
而对白人男性来说,这种偏见肯定会被文化放大,因为文化会把他们的经验投射回去,使其看起来更加典型。只要你愿意,这种投射偏差还会被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进一步放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伪装成性别中立的男性偏见如此普遍。
如果大多数掌权的人都是男性——确实如此——那么大多数掌权的人只是没看到这一点。男性偏见在他们看来只是常识,这种常识坚固而且也无需撼动。
正如波伏瓦所说,“将世界呈现为世界,是男人的活动;他们以自己的观点描绘世界,把自己的观点和绝对真理混淆起来。”
03. 语言中看不见的女性
不售卖卫生巾,也用种种理由堵住讨论售卖卫生巾的讨论。这一套行为并不罕见,追根溯源,现代人面对的流传延续几千年的“文明”皆是如此:
把女性赶出公共领域,赶出公共记忆,再用语言来限制女性对自己的认知和想象,这是一套有意识的操作,不只是男性缺乏生命经验的缘故。
《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女人不算人”,是我们要描述的这个系统的核心。这听起来很离谱,实际过程倒不复杂:把所有“女人的事”,比如家务、育儿、女性的身体归为私人领域,再把公共领域当中的女性视角尽量删除。正如伍尔夫的观点,如果在文明当中,女人的存在从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那么女人在文明中就不存在。
虽然书号称“人类文明”的载体,但打开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名著,就像《看不见的女性》罗列的一样,书里到处都是空缺,纰漏,荒谬,可见“历史”的巨大虚伪,不仅遗漏了50%的真实,就连提到的部分,视角也全是男性的。
史书上写“刘备率军二十万攻打襄阳,十万百姓流离失所”,虚伪的不止女人几乎永远只在“十万百姓”里;而在于如果女性自己作史,对于这些反反复复的争夺杀戮、帝王将相的男性理想可能根本没多大兴趣,懒得写进书中。
那女人如何看待历史?读了那么多年传世名著,我们对女人的欲望,友谊,生育之痛,家务之繁等等生命体验,对女人如何影响进化,改变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仿佛女人对此毫无贡献。
教给我们的标准常识是,能学到的是毫无家庭牵绊的波德莱尔被认作现代人的模版,女性的性快感在弗洛伊德眼里是模仿男性的不成熟行为,斯宾塞找到了“证据”证明女性比男性更早经历个体进化是为了给繁殖存储力量。
不仅关于人的书不能看,连动物世界也一样。因为人们如此热衷于用动物生活彰显人类行为的正确性,于是我们看到的总是威武的雄性和温顺的雌性,是等级社会,竞争和杀戮。自然界那么多物种,真的都是这样的吗,完全相反的例子很少吗?很多,但它们也一样在叙述中被消失了。
在这样的教化下,人们只有唯一一套思维范式,这种范式根植于人们的常识态度中,其存在几乎是隐形的,影响着人们对现状的批评话语。也难怪满腹经纶的男性知识分子们不参与女性议题的讨论了,在这个领域,他们不仅同样缺乏积累,更可能因为“常识中毒”更深而少了一份直觉。
这样大面积的,成体系的消声女性历史人物和历史视角,反过来又成为了“女性够不上人”的证据。女性不够有谋略,所以没有几个女王;女性不够睿智,所以没有几个女哲学家;女性不够有才华,所以没有几个女文豪;女性不够勇敢,所以没有几个女战士。
每个时代,每个领域的女性都听到过属于自己版本的“女生不行”,又苦于缺乏史实而无法反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男的不行”激起如此大的反应:反驳终究还是回应别人的话语体系里,一个浑然天成,无须为自己辩解的主体,才会直接说出自己眼里的世界。
仅仅消声,还不足以让一代代的女性主动保持沉默,而是借由从语言、心理到文化等方方面面打造的“有效系统”,来直接消灭女性的叙述。
现在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个“他”的样子。绝大部分人想的这个他,应该是个男性,尽管“他”在日常使用中,是不分性别的泛指。“口头文字是心理经验的象征,书面文字是口头文字的象征”,语言是文明的核心,通过规范文字,实际上就在规范人们的心理经验和想象空间。
国王、哲学家、文豪、战士,这些词语都一样,当我们将大量名词默认为男性时,传递了什么信息?在前面加一个女字,是不是有些别扭?
比起有的语言会区分阴性和阳性名词,“他”似乎更包容,事实上无非是伪装的性别中立词罢了。有人厌恶他或她,she or he的表述,认为这破坏了语言的美感,但这语言本身就是暴力的,它是撕裂沟通,埋没女性的系统底层。
并不只是名词。《男性统治》里,布尔迪厄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如何运用象征的作用来让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种极端否定的印象。譬如,高/低,坚挺/柔弱,干/湿,将负面的形容词与女性身体深深绑定。最显眼的例子,大概就是阴气。而雄心壮志这样的好词语能对应的女性版词汇是什么?
通过如此这般的剪裁和限制语言,让女性仿佛永远操持着外语,从而更加难打破沉默。当她要开口时,发现公共领域里的词都是男性的,当她终于找到几个属于自己的词语时,却发现造出来的句子总是贬义的。
这个代价不仅是女性的。
在数据时代之前,语词是连接神的工具,修辞、辩论、逻辑,一点点铺设通往真理的路。直到20世纪的哲学革命,维特根斯坦宣布先贤们对形而上学孜孜不倦的错误追求是源于日常语言的误用,语词并不都是关于对象的真实表达,而是按照一定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
这一革命的重要性在此不表,只是一想到哲学界花了几千年才意识到,那个认为“女性本性低劣,而上帝是一个中年男子”的语言系统只是建构起来的一场游戏,就觉得好笑。但凡多问问女人的意见,也不至于花那么久。这是半吊子的“人类文明”为抑制女性而付出的代价。
在伍尔夫所有的叙述里,展露出最大抱负的,或许是她借小说人物说出来的这句:I want to write a novel about silence, the things people don’t say.
是时候把巨大的沉默说出来了,用我们自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