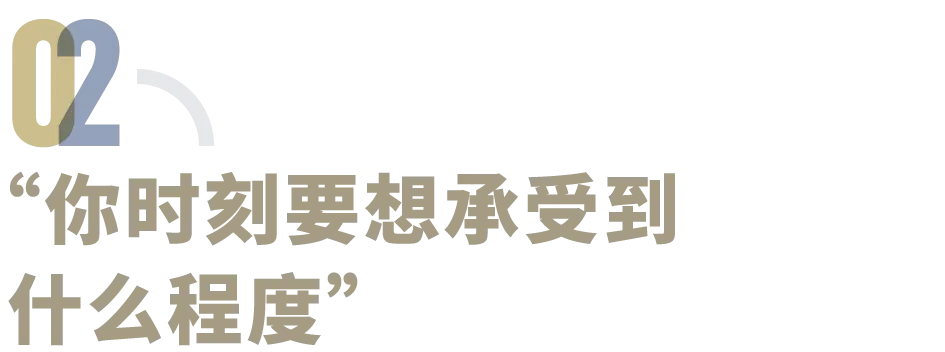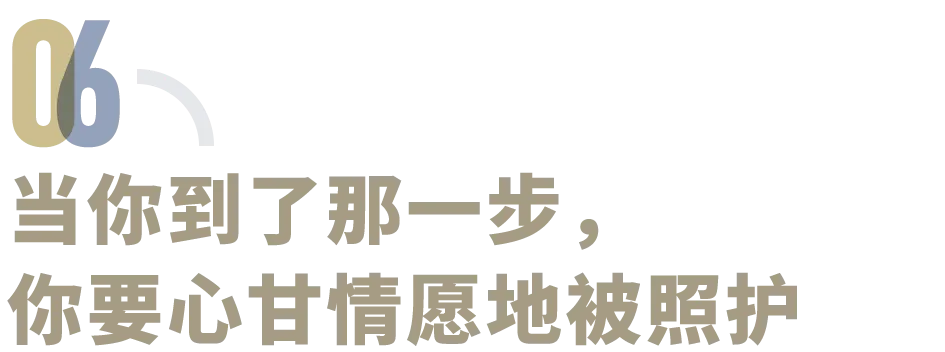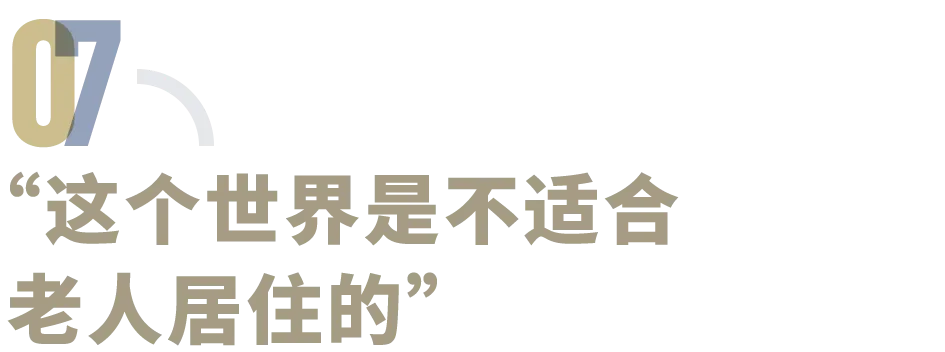当你身处人生盛年,拥有智慧、事业、家庭和现代生活方式,忽然间,你被每天强制劳动9小时,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将打翻物品归位;洗澡、擦拭、换尿布;换洗内外衣物;换洗床单被褥;陪玩陪聊;跑医院;喂药……
_你昼夜颠倒。你悬心吊胆。你面对意外,面对破坏,面对毫无理性的怒气和敌意。你每天的核心挑_战是抓住排泄时机(你观察食物摄入量、计算消化时间并神经质地反复追问: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行动必须精准,差之毫厘,意味着加倍的擦拭、清理、换洗,更不走运的日子里,你做这一切时,对方在玩屎。
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孩子——那毕竟意味着希望,而是地球上唯一曾为你做过这一切的人。他/她的生命如身体一样逐渐枯萎,直到困于一间屋子或一张床。你们的身份调转了。
“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胡泳说。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一个典型的“三明治一代”:父亲以96岁高龄过世未久,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孩子未成年,本人处于事业巅峰期。过去三年多,照护父母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活动范围随之缩小,现在他已经基本不出海淀区了。原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遭到切割、压缩,并轨到“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_你出于反哺之情接下这项工作时,未料到被改变的将是你的整个生命状况。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_,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你将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做这个,数年如一日地做这个。你将时时刻刻在生活、工作和照护之间寻求平衡,在做自己和做个孝子之间寻求平衡。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_你曾以为生活是持续的,甚至可以添砖加瓦,而照护一位老人,则是必然的失败。你无法奢望奇迹,必须接受_现实:你的付出在增加,却换来一个愈加衰老、离死亡更近的亲人。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你还敢不敢日复一日地踏进去?直到一切完成了,在失去之剧痛的同时,你成了堑壕里被推到第一排招架强敌的士兵,你成了只有四壁而难逃风雨倾泻的小屋——再没有什么可以隔开你和死亡了。
2023年十一假期,胡泳兄妹三人和父亲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遗嘱,写下这一生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父亲专门向母亲做了正式告别,抓着她的手,跟她叙说,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胡泳母亲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她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十月中旬,胡泳父亲去世。
一个晚上,看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胡泳泪流不止。他叫来两个孩子,让他们陪自己一起看。孩子看完说,能理解爸爸照顾阿尔茨海默老人有“多么难,多么难”。
“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他认为,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独生子女一代。
以下是胡泳对凤凰网的讲述:
我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症重度患者。她现在所有的行为方式跟三岁的儿童没有太大的差别。她需要人喂饭,你就做一些她能吃的东西,剁得碎碎的,给她戴上兜兜,一口口的,就像给小孩喂饭一样。
最难的是排便问题。她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大便或者小便了。甚至很多时候,她不知道,她会把各种东西弄脏。所以你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是,天天追问她,你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
你得计算,她可能三四个小时要尿,但是这又跟她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流质的食品有关系。严格地讲,这不会是科学的,相当于你每天都有可能遭遇到很狼狈的时刻,把所有的衣服、床单都洗了。
如果有一天,你看住了她整个的排便过程,她既没有尿湿裤子,也没有拉在被窝里,你觉得这一天好有成就感。但其实这是你每时每刻要做的事,天天如此。常有人问,为啥不给她用成人纸尿裤呢?我心疼她,因为会有其他负面后果,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用我的话来讲,人生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最后也归于屎尿屁。这是人生的基本常识,只不过我们用各种东西掩饰它。我们发明各种委婉语,巧妙地觉得它不存在。没有必要掩饰。这就是真相,人生的真相。我母亲现在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不是真的随处大小便,而是使用移动的坐便器,所以屋子内常年弥漫一股屎尿味。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
疫情时期,为了不让我父母(被)传染,我有段时间是纯物理隔离。我们也改成网课了,我完全在家,停止了一切交往,也辞了保姆。有那么几个月是我一个人管他们俩。我父亲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不需要我特别操心。母亲不能自由行动,她出门坐轮椅,在家推着一个小推车。我早上起来,先准备早饭,管理我母亲的大小便,我也得给他们俩洗澡。做完早饭是中饭,然后是晚饭,洗衣服,拖地,擦灰,刷碗,洁厕,白天做这些事。
我给我妈穿裤子,穿袜子,穿鞋,扶她站起来,晚上脱衣服,脱鞋,扶她上床,对我的腰真是个考验。收拾他俩掉在地上的饭粒和菜屑也是。
晚上很痛苦。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点是,黑白颠倒,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概念。她不知道是晚上,她不睡觉,经常折腾。一个方式是反复收拾东西,比如衣服,本来你给她叠得好好的,她把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摊得满床都是,全部弄乱,再一件一件叠。卫生间储物柜里头的洗衣液、洗发水、卫生纸,她半夜起来,全部翻出来,扔到地上,到处都是。你就很恐慌,你怕她拧开某一个什么液,给喝了。我瘦了很多,真的非常辛苦。
2022年12月31号晚上1点多钟,我在另一个屋子里睡觉,就听见扑通扑通地响。你知道照顾老人最怕屋里有响声,你怕她摔了。我的心揪到嗓子眼儿里,一阵恐慌,赶紧爬起来,发现我妈把东西扔在地板上,卫生纸撕得满地都是。
我火了,跟她大吵了一顿。我说:你知道我照顾你有多累吗?老妈:谁让你累了?谁让你照顾了?我: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老妈:我对不起你啊?——这句话一出,我就知道自己徒然枉费心力,也徒然生气。
这个架有什么意义呢?就好像孩子把父母气得不行了,你把他/她大骂一通,骂完了以后你特别地后悔,你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自己无能,无能到你为什么要发这个火。我就反省说,不能吵架,不能吵架。我就写了“控制情绪”四个字贴在电脑上。
人都是凡胎,很难遏制住情绪。但是如果你想得透彻,你就会减少冲突的次数。这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所以我说都是相通的,你能够通过照护了解关系的真谛,它就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上。
我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我的孩子未成年,我要养孩子,同时养老人,又处于事业上有很多要求的时期。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
非常挣扎,你怎么平衡?所以一开始,我动了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念头。
我也真的看了北京的养老院。我的核心诉求不在于郊区的风景有多么好,而在于跟老人的交往有多经常,养老院离医院有多近,所以我选的都是城里有地铁的地方。
我的确喜欢上一个可以搭乘地铁到达的养老院,环境也不错,就在二环边上。院长我也谈了,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养老机构,引进了一些做法。我带父母去看了,医生也聊了。回来以后开家庭会,结果是我父亲愿意去,但我妈不同意。她那个时候是轻度症状,她对很多事情还是明白的。
老人有老人的心理。如果有亲人环绕在身边,对他们来讲是更舒服的环境。养老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老人的需求来设定。它有一整套机构的规矩,不然没法运行。但是老人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养老院首先要评估老人的健康状态。生活能自理的,放在自理区;其次叫半自理区;不能自理了,由护工管着。你在这里头,很容易心情不好。这是人生的单行道,只会越走越荒凉。某一天,突然有一个人不见了,他挪到别的区了。最后的结果,每个人都知道会去哪儿。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在家养老肯定好于去养老院。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养老院?因为在家养老,有太多的负担是照护者承受不了的,照护者有自己的困难。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循老人的意见。我妈拒绝以后,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说,我们要做好很充分的在家照护的准备。你得认识到如此选择给你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它不是个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
很艰难,常常遇到决策的两难,不仅是身体的劳累,也有心理的,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无论你做多少准备,也是没有用的。实际情况永远比你的准备复杂得多,麻烦也要多得多。一边照顾着,一边对自己做各种建设,包括怎么保存体力,怎么形成一套照顾方法——老人的衣食起居,生病了怎么办,其他子女的安排,怎么安排你自己的生活。“三明治”的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在各种责任当中找平衡。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无私的?假定说正态分布,大部分人都是自私的,这就导致有一系列的损益比的计算,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在长寿时代下,照顾老人可能十几年。那损益比,你咋算,压根就没法算。
最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基本境况,所谓的human condition,生老病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经过这些状况,管理这些状况。你不需要说你是不是一个道德动物,什么自私与无私的比例。这就是你的责任。
有一度,天气不冷的时候,在太阳不那么热烈的下午,我会推着轮椅带我妈散步。我爸拄着拐杖跟着。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老人的聊天环境。因为在外头的主要两群人,一群是小孩,到处跑,另一群就是老人。以前我从来不会在这么一个时段干这么一个事儿,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忽然进入到一种生活状态。随着父母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例如吃饭、穿衣服和上厕所)都渐渐需要帮助,你会感觉自身被带到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世界中。你陷入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这几年,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我都不出海淀了,如果有人要找我,我把他约到海淀。我生活中的一大块都交给了这件事,社会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妈的作息时间是乱的,没有保姆时,我也做不到(按时休息)。
有一个统计数据说,照顾老人的平均时间为四年,但15%的照护者照顾年迈父母的时间超过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护理人员报告称,他们每天平均花费九个小时来履行护理职责。照顾久了,每天一睁眼就在干这个事,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非常容易焦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你永远在平衡,平衡工作和生活,平衡你和父母的关系,平衡你和配偶的关系,平衡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从根本上讲,照护一点也不浪漫,它很残酷——在我最累的时候,我会暗想,什么照护者?不过就是我父母的一个女佣罢了。很抱歉,我冒出的念头的确是“女佣”,可能因为女性总是更多地和照护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在朋友圈里写些“照护琐拾”,可是又常常觉得,照护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呢?能写出来的,都是包装过了的。残酷的东西不可言说。
很多时候,你会质疑,自己做这事的意义在哪里?你不能把它们浪漫化。一旦浪漫化,最后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你,因为浪漫化的泡沫会破灭。
看着最亲的人的生命在你面前一点点流失,而你对此无能为力,那种滋味,是一种刀割般的疼痛。
我看到他们老了,我就在想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也是这个样子,多么痛苦啊。
到后期的时候,家里不论来任何人,我父母一定要在窗户(前)瞅着这个人走。他们已经被限制了,窗户外面对他们来讲是一整个世界。人到最后就是囚徒了,这个世界对他/她来讲越来越难以进入了,他/她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成为婴儿。
家里的电话本来经常响。每年拜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后来拜年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同龄人都去世了。最后那个电话再也不响了,响的时候全是垃圾电话。
你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会想到一个人越来越废物,什么也干不了,**社会关系一点一点被斩断,就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
兔年大年初一的下午,老妈躺在床上对我说:没意思。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昨天本来挺好的,吃了饭,到了晚上,纸也没有了,裤子也没得穿。——别看她一生刚硬,其实最终对生活是那么无力。
在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悟到,老了,就是学会做一个无力量的人,习惯于羞耻。这是所有老去的人的归宿。男人更难一些,因为女人早已懂得什么是羞耻。
其实,有力量的人,也未必有自由。没有力量的人,可能扎下更古老的根。力量有大小,但别忘了,力量也有深浅。
去年十一假期时,有一个上午,我们子女三人跟我父亲围坐在桌旁,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父亲因为耳聋,他是笔谈)。我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的遗嘱。他写了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我们和他谈了什么是临终关怀,如果进医院,应该怎么办。
我父亲专门跟我母亲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跟她讲,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我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讲啥。我妈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
10月3号,我们给父亲穿上正式的衣服,我们三个陪着他,没下车,经过海淀区,走公主坟,到复兴门,然后横穿长安街,带他看了天安门。10月中旬,我父亲去世了。我很悲伤,但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宁静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
怎么跟老人讨论死亡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认真地说,哪怕你不好张口。因为很难,比如父母还健在,你跟他讨论说,爸,能不能留个遗嘱。你觉得能说得出来吗?我不觉得这适用于所有家庭。但是我会主张说,凡是有条件的,父母比较开明,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我非常建议这些重大的事情放在桌面上来谈。
在照护老人这种事情上,也需要开家庭会。怎么分工,去不去养老院,得病了怎么治疗。中国人有个特点,很多事儿不明说,说了好像伤和气。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
而且,这个最好在父母身体还好,还没有进入照护需求的时候,趁父母头脑还清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开这个家庭会。
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要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家族链条,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生生死死循环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要想着怎么把照护变成家庭范围内大家都去思考的事,让你的感受在家族链条之中能够分享。
我前阵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泪流不止。我叫来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跟爸爸一起看。电影里,阿尔茨海默老人搞不清楚整个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幻觉,就像一场梦,而常常是一场噩梦。孩子看了以后,觉得说,能够理解爸爸照顾奶奶有多么难,多么难(哽咽)。
虽然我前边也说过,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但我还是试图表达,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疾痛、衰老、死亡的书和电影,这是吸收的部分。你看别人是怎么老去,怎么经历死亡,我很大的解脱来自于此。
幸运的是,我是个大学老师,我的自由时间比别的工作多。我还有兄弟姐妹来分担。另外,我想礼赞所有的保姆,如果没有这些可敬的女性,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多照顾的事情?这些女性对于我们能够正常地过某种生活,是了不起的贡献。
这个世界有关养育和成长的东西很多。养育和成长代表着生命的曙光阶段,是向上的,美好的东西都在你的前方。大家乐此不疲地看这些东西。可是,有关照护的东西,大家关注得太少,被表达得也太少。而照护的时日,有时甚至长过养育和成长的时光。这是我愿意出来分享的原因。
我们看《返老还童》那个电影,把它看成是一种科幻。但是现实当中,人真的是可以逆行的,他/她会回到儿童时代。但是这个“儿童时代”没有任何的浪漫,是一种痛苦。他/她已经丧失了对很多东西的认知,自己没有那么痛苦,但是最亲的亲人都是很痛苦的。
我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才三年多。我发现她有症状,带她去医院做正式的诊断。医生说三个东西,比如苹果、算盘、杯子。五分钟后,突然问,刚才我说了三个东西,顺序是什么?
我妈答不上来,真答不上来。有很多方块,医生要她按规则摆来摆去,她就是不会摆。我在那间诊疗室里,当时就挺难过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类似于小孩的智力。
从此以后,如果听见有人说,你怎么智商那么低,跟个小孩似地,我就很敏感。对那些失智失能者,外人看起来觉得很讶异,但你无法了解的,你能吗?他们被关闭在每个正常人的经验之外,你对于这种体验又知道些什么呢?
当时我妈结果出来了,我们这些子女可能还有些幻想,她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我见过很多高龄的知识分子,有的人90多岁,头脑非常清楚。人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于公平感的质疑,很自然地就会想,这事不公平。为什么轮到了我?你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事情。
阿尔茨海默症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病。你不清楚发病机制是什么,至今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它。医生永远跟你说,只能延缓,不可能治愈。延缓的情况因人而异,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有断崖式的下跌。所以你对它是束手无策的。
更痛苦的是,你眼看着一个人的记忆走向衰亡。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跟记忆有关的?你记住的东西才是你生活里真正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母亲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胡泳,我最小的儿子,我很疼爱他,他管着我。慢慢地她开始糊涂,会把我叫成我哥的名字,然后直接喊我“老哥”。她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也不真的清楚老伴去哪了。现在她能沟通的已经很少了,她咕噜咕噜说她的,周围的人稀里糊涂地跟她讲。有时我下班回家,她在床上躺着,我站在床前,她攥着我的手,就那么咿咿呀呀地说下去。
所有的小孩会记得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所谓的“妈妈的味道”。今天把茄子、辣椒放在她面前,她不认识那些菜,她会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茄子,这是辣椒。过了没有几秒钟,她又问,这什么东西?她这么喜欢做菜的一个人,她根本不记得这些食材。
更难过的是,我孩子来了,她搞不清楚孩子和我之间是啥关系。小时候天天跟着她跑的人,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非常清楚,她认得我。保姆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不去,坐那不动。她根本不听保姆的。我就跟她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马上点头答应。咱们现在该坐在坐便器上小便了,保姆喊,她经常置之不理,但我一跟她说,她就很痛快。
我希望她一直认得我,就是这么低的要求。
她的脑子似乎有某种怪物,日复一日地蚕食她的记忆。与此同时,她的词汇量越来越少,由一个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表达的人。我女儿形容说,奶奶的大脑就像被虫子吃了一样。你看着这个过程一点一点走,心里是非常痛的。
哲学家帕菲特说人之所以成为我,是心理经验的连续性。这在哲学上叫作自我的同一性。但是我用阿尔茨海默症来想这个,我就想不通。因为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能说我妈的心理经验是一致的,但我能说她不是我妈吗?
所以你就需要另外一种解释,它可能跟头脑没有关系,是身体或者气味。在任何场合下,我都认识我母亲的那双手,那是一双劳作的手。现在是瘦的,青筋暴露的,只有皮和骨头的。我回到家,她会拉我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在家里她的手很热乎,她会说,我给你暖暖手。从小就是这双手领着我,带着我干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不是精神的本质性,而是身体的本质性,这双手的本质性。这迫使我去想,到底什么是我,什么是妈妈。
我妈喜欢家里来人。她会问你爸你妈怎么样,你那口子怎么样,你的小宝宝呢?所有人来了,她都这么问,你怎么回答也没关系。她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但她明显地喜欢家里有人。来人了她就高兴,人走了她就很难过。
这也是我不想把她送到养老院的原因。现在她已经没有意志了,我可以轻松地把她送走,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记忆丧失到这种程度,对周围的世界已经没有反应,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里会怎么样。有一个常年在养老院里工作的看护说,那些病人不仅仅在等待死亡,并且每天都在受折磨,自身病痛和外界的折磨,特别是老年痴呆患者。所以我愿意看着她,哪怕苦或者累。过去我觉得送养老院是对的,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我没有动摇过。
《相约星期二》写的社学会教授莫里·施瓦茨,是真事。他上了很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你最难受的是什么?他说,过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你想这个人天天需要别人给他擦屁股,对他的自尊有多大的影响。
被照护者的心理负担很大的。我妈算是好的,为什么,她丧失了这种意识。她的确需要有人擦屁股,甚至像小孩一样,她抓屎,玩痰,这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得洗很多东西。但是她没有尊严感的丧失。像我父亲,最后插尿管,有个尿袋挂着,他都觉得没有尊严。
我在跟我父母生活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说,你们最好是心甘情愿地被我照护,这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挺好的。那会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只会让我更累。因为你想自己干,好,你摔了,麻烦大了。
老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他/她欣赏你为这些事情做出的努力,承认你的努力,不需要对你感恩戴德,但是可以为你感到骄傲。
老人真的夸你两句,你说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你该干的事情一件少不了。但是心理上是个很大的安慰。我父亲去世之前,就会写,胡泳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我很感谢,父亲看到了。
你就在想说,以后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能不能处理得更好。我老了,当我的孩子要来照顾我,我能不能放心大胆地把我交给他们照顾,而不去说你不要照顾我。或者当孩子没有力量照顾,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能控制的养老院,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晚年生活,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的抢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进不进ICU……
这个事情需要想得特别透彻。用佛教的话讲,叫作“桶底脱落”,你想得桶底直接掉了。归根结底,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没什么尴尬的。因为你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在照护之中,要么照护别人,要么将被别人照护。
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所有趋势性变化中,有一个变化最致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
但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我们的世界主要是为青年人设计的。
我对北京的盲道深恶痛绝,走走就断了,就被占了。北京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台阶,没有缓坡,甚至有的地方本来是通的,却要人为地立个栏杆。我们一家到外面聚餐时,我总要先打电话问餐馆,轮椅是不是畅通无阻,就发现很多餐馆不符合这个要求。还有,你极其难以忽视的是什么?厕所——有台阶,是蹲坑,我妈这种腰腿不便的,要去上厕所,这就费了劲了。
你说我可以不外出吃饭,就在家里吃。问题是有个地方你不得不去,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大量的地方不是无障碍通行,或者它真的没电梯。我和我哥两个人把我妈的轮椅抬上二楼做检查。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到处活动的正常人,你觉得哪里都挺好的。可是你年龄大了,有残疾,处处都是障碍。你会发现周围是一个充满了老年人的世界,而老年人寸步难行。
对老人真正的关爱,是让他/她觉得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是虚拟空间里的。我是互联网学者,研究数字化的适老问题。我曾经严厉抨击过现在的智能电视,连我自己都搞不定,界面无比复杂,让以电视为生的老年人怎么办?
现实当中空间的适老化,我觉得挺难的。凡是改造就很难,最好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适老化)设计进去。
比方说,家庭的改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必须把床扔掉,想办法弄一个能升降的床。老人如果卧床的话,需要翻身、下床,或者需要吃药,医院那种床你能升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吃药。
社区范围内能做的事情,比如社区里有没有很近的医院或者卫生中心?尤其是,社区里能不能建食堂?空巢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你让老人天天做饭,第一个他们累,第二个有危险,可能真的会忘记关火。
还有一类叫养老院的养老。首先考虑(机构)数量是不是够多,第二是质量问题,怎么保证一个稳定的、有爱心的护工队伍?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医院。除了老年的常见病门诊,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医院有临终关怀病区。凡是那些选择临终关怀的人,能够很容易地在附近医院找到这种病区,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走过生命最后的一段旅程。
开学聚会的时候,我给我的学生讲“胡门第一课”。每年征集题目,都是年轻人的苦恼,怎么化解焦虑,怎么找工作,等等。去年第一次忽然有学生提出来,老师,你能不能讲讲照护。我真的很高兴,我觉得我走过了这些路,我有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可能对学生有用。
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这些孩子当中很多是独生子女,焦虑说我将来怎么办?照护与被照护,这两个身份你永远逃不掉。所以你越早思考这个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事,对你来讲更有益。
独生子女一代的照护问题,是一个社会现象。独生子女会很累,一个人对付两个人,真的很惨,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很多的牺牲。好的地方在于,你可以自由地决定。我们这代人见过太多由于子女众多,从而产生关于照护的矛盾。长期的家庭照顾需要体力和情感的储备,更不用说沉重的经济负担。要未雨绸缪,做好心理、金钱、生活方式上的准备,在各方各面有一个规划。
自从我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以来,《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一书曾长期是我的案头书。这本书开头有一段献词,我第一次读到就潸然泪下:
献给所有经受过、忍耐过,但终究没有挺过
苦难与失能的人们——你们教会了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教会了我们生(与死)的问题缘何重要。
同样,献给所有的照护者们——为了让生命延续,让希望长存,
为了让大家都能有善终,你们付出了所有,
做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
我们用再多的时间去赞颂它,
都是不够的,
即便有的时候这是你们不得不去做的。
我们已经身处老龄化社会。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品质,很大程度将取决于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老年人被照顾的程度有多好(或者有多差);取决于照护者是被支持还是独自苦苦挣扎;取决于它是否能维持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以符合人性的方式衰老和死亡——始终得到照顾直到最后,永远不被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