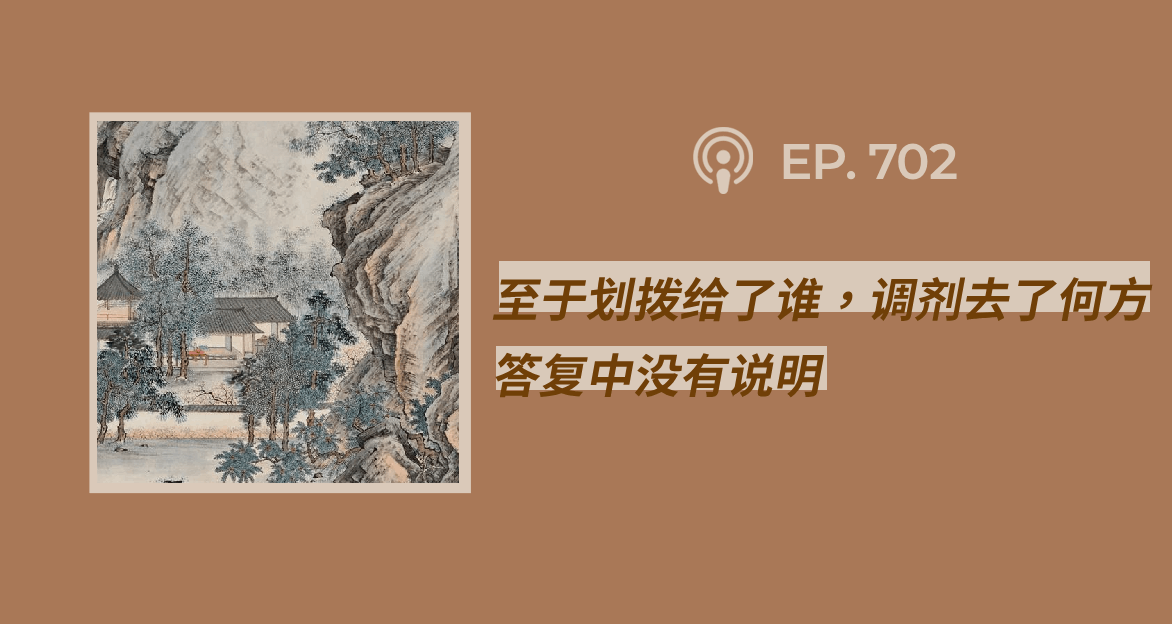學人Scholar | 蔡定剑逝世十周年:接过先生手中的启蒙火炬
蔡定剑认为,如果依然坚持“特色论”和“国情论”,那么丛生的社会矛盾将难以解决,这将难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改革的成果,则有可能化为乌有。吊诡的现实,使得不少人心存疑惑:既然体制内改革的自动力已经殆尽,改革的后备动力在哪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曾经的体制内官员,对于中国的改革,具有理性的乐观。根据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深入和丰富的社会调查,蔡定剑得出一个判断: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已经从民间产生。
蔡定剑认为,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多元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