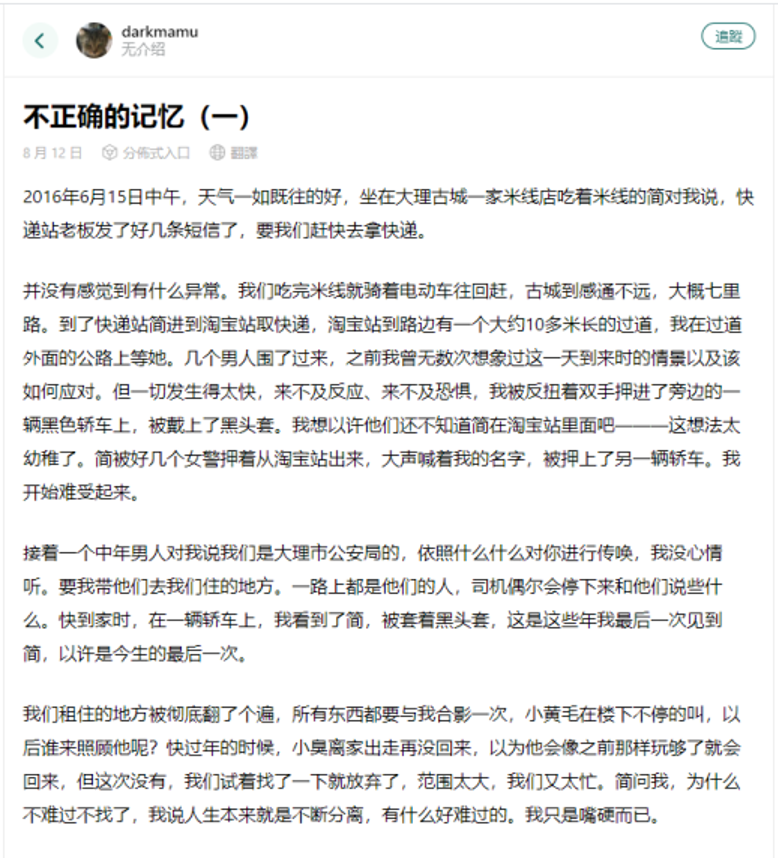1 被 捕
大理古城是一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中国西南小城。对于从内地来的游客,最亮眼的可能是云南高原的宝石蓝天空和青瓦白墙、雕梁画栋的房子。因为四季如春街边、店门外种满了花草,墙上爬满藤萝,站在街上可以看到云雾环绕的绿山。不管从地理上还是美感上,大理像一个世外桃源。的确,上世纪九十年代和这个世纪的最初十年,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来到这里落脚,还有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希望远离喧嚣和骚扰的人。
2016年6月15日中午,卢昱宇和李婷玉在一家店里吃米线。卢昱宇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长方形的瓦盆,准备种猫薄荷,给家里的猫吃,也吸引别的猫到家里来玩。吃饭的时候,淘宝站老板给李婷玉发来了好几条短信(他们在网上购物不留自己的地址),催她去取货。催叫频繁有点异常,但是他们没有多想。
“我们吃完米线就骑着电动车往回赶,古城到感通不远,大概七里路。到了快递站简进到淘宝站取快递,淘宝站到路边有一个大约10多米长的过道,我在过道外面的公路上等她。几个男人围了过来,之前我曾无数次想象过这一天到来时的情景以及该如何应对。但一切发生得太快,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恐惧,我被反扭着双手押进了旁边的一辆黑色轿车上,被戴上了黑头套。我想以许他们还不知道简在淘宝站里面吧—这想法太幼稚了。简被好几个女警押着从淘宝站出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被押上了另一辆轿车。我开始难受起来。”(卢昱宇《不正确的回忆》)
他们是一对情人。他们办的“非新闻”博客在2012年到2016年之间专门记录中国群体抗议事件。
警察命卢昱宇带路去他们住的地方。他心里抗拒,但知道没有用。何况猫还在家里。到了他们的住处,大概一公里的路程,门口已经有很多便衣在等着。他下车的时候看到押着李婷玉的车已经停下,她在车里,头上套着黑头套。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
2 在‘非新闻’之前
卢昱宇1977年出生在贵州遵义城外的乡村。他的父亲是名解放军退役军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遵义经营一家种苗场,母亲则做个体户。父母是那个年代的先行者,城中最先富裕起来、最先拥有电视机的家庭。父亲曾当选全国100个先进个体户,母亲则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
也许是因为忙碌,父母把三个孩子都送在外面上学,最小的卢昱宇从九岁开始,就借住在亲戚家、老师家上学,周末才回家一次。他换了很多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受了很多欺负,上中学的时候到了县城的重点中学。少年时期,他喜欢听摇滚乐,喜欢吉它。在贵州的小县城,这是个少有人分享的爱好。还加入了男孩子们的帮会,经常打架。每次见到父亲,后者会教训他“好好学习”,不允许他有别的爱好。他很厌烦。
1989年,参加过六四的表哥跟他描述过当年的学生抗议和静坐。他也目睹了当地的一个中医学校的学生堵路抗议。那时候他开始用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中文节目。
1995年,卢昱宇考入了贵州财经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他一点也不喜欢。他想和朋友组一个乐队,还准备转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但是大学第二年,他和几个朋友介入了一场群架,把人打伤了。他因此被判刑,从96年到02年,在遵义服了六年刑。
六年是很长的时间。但是他说那时的监狱管理和现在不一样,加上家人的说情,他可以看书,也可以弹吉他,还可以看电视看球赛。但是这期间,他的家庭发生了变故。2000年,他的母亲去世了。母亲是他最亲的人,父亲没有通知他,直到丧事处理完后几天才到监狱通知了他。
出狱后,他从家里搬出来,在一个小广告店里打工,给客户做标牌、标语。那正是互联网在中国兴起的年代,如同很多生活在偏僻和狭小生活空间中的年轻人,他在网络上找到了自由。在网上的头几年,他主要是找音乐、听音乐。开始听的比较主流,从中国的张楚、窦唯、何勇,到国外的Guns N’ Roses, Kurt Cobain。后来他的口味后来转向哥特(Goths) 和黑浪潮(Darkwave)。
“那个时候我很迷这个,”他说。他一边打工,一边开设了个博客,收集自己喜欢的音乐和乐队,出入网上音乐论坛。那时候,中国的网络还没有什么禁忌(或者说中共还没有发展出严格的审查系统),谷歌还在中国运营。
卢昱宇不想呆在遵义。他感到和环境格格不入,和小时候的朋友想法也不一样。他感觉如果他不离开的话,就会“烂在这里”。他开始出去打工,在云南,在浙江;在工地,在工厂,在网吧。后来他应 “中国地下音乐网”经营者的邀请去了银川,做网站总版主,负责介绍乐队、上传音乐资料、管理论坛等。但是这个网站在还未开始盈利的时候,就倒闭了。
他说,虽然他没感觉生活有什么异常,但一直有种压抑的感觉。“我不知道它具体来自于什么东西。”
2010年,他又回到了遵义。他和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做着结婚、安顿下来的打算。农村人受户籍隔离制度的限制,能进入体制正常上班的机会很少。在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人乡村人口,只有打点零工,或者做点摆地摊的小生意,甚至混黑社会。后来这对情侣分手了。
3 2000**年代到2013年期间的维权画面**
中国的维权运动发韧于2000年代初,标志性的事件有孙志刚收容遣送案(2003年),《南方都市报》因为曝光萨斯被调查和处分(2004年),蔡卓华印刷圣经被判刑(2004年),高智晟律师曝光和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05年),独立候选人参选基层人大代表(2003-2006年),太石村民罢免村官(2005年),民间学者和律师对宪政的讨论(2003-2008),陈光诚计生案(2005-2006),四川汶川地震引发的公民社会参与(2008年),北京律师倡导律协直选(2008),以及零八宪章(2008)等。
但是这些主要是由学者、意见领袖、博客主人、和律师带领的事件,借助当时空间还比较大的市场媒体而发力。
2007年5月,中国第一家类似推特的社交网站“饭否”出现,吸引了大量用户。到 2009年上半年,饭否用户数已突破百万,其中包括大量进入2000年代以后关心社会事件、政治转型的普通人。2009年“六四”十周年,饭否上出现大量1989年民主运动的照片;在2009年7月发生的乌鲁木齐骚乱中,饭否成为信息量最快、最大的传播工具。8月份,中国当局关闭了饭否。
2009年8月,新浪微博诞生,在大约一年内,还出现了网易微博、腾讯微博等多个社交媒体。到2011年4月,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突破了1亿大关。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不管是饭否还是新浪,微博的出现是一场热烈的言论革命,也是一场无声的社会革命。普通人不管在哪里,通过网络可以从四面八方获得信息,可以和任何人在网络上“相遇”,志趣相投的人可以在网络上汇聚、沟通、组织、交友。之前在某个山村或小城发生的事情,无人知道,但是通过网络,它们可以迅速成为全国性公共事件,如2009年5月发生在湖北巴东一个小镇一个名叫邓玉娇的年轻女子刺杀企图强奸她的当地官员的事件;比如2010年12月浙江乐清一个名叫钱云会的村长,在多年带领村民反抗征地后被一辆工程车轧死的事件。
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将维权活动(activism)的公众参与推向更大范围的,有两个标志性人物。一是北京艺术家艾未未,一是山东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
仅仅举几个例子。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艾未未动员了几十名志愿者在四川调查并统计豆腐渣工程校舍导致的学生死亡人数,和当地官员与警察发生了频繁冲突,他本人不止一次被便衣警察殴打。这些事件,以及他所拍摄的记录片《老妈蹄花》在微博上引起成千上万人关注。2010年5月12日,艾未未在网络上发布大型声音作品《念》,由数千名网友念5,196名遇难学生名字的音频剪辑而成。几年前,我走进华盛顿 Hirshhorn Museum 观看艾未未展时,听到的就是《念》。
2010年11月艾未未在上海的工作室接到拆除通知后,他在工作室举办“河蟹宴”,近千名来自中国各地的网民前往参加。
2011年4月艾未未被失踪,81天后获得释放。11月1日中国当局对艾未未工作室课以RMB15,220,910(约$2.34百万美元)“逃税”罚款。艾未未将此变成了一场更大型的网络活动,发起向网民借款活动,并设计了精美的借据。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有将近三万网民“借款”给艾未未。有人甚至将人民币叠成飞机,投到北京草场地艾未未工作室的院子里。环球时报的社论嘲笑说, “艾未未‘借钱还税’搞得太戏剧性”。它的确很戏剧性,同时也是最有创意的社会动员。可以说,许许多多中国过去十年的民间权利活动者都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010年9月9日,陈光诚因为带领村民反对暴力计划生育被判刑四年出狱后,他和妻子立刻被几十名当地政府雇佣的人员24/7软禁在家,禁止外出。他家门口和外面的道路上被安装了监控摄影机、手机屏蔽器;强光灯晚上照射着他的院子和周围。全国各地网友开始自发到山东东师古村看望陈光诚,在当地遭到拦截、殴打、凌辱、抢劫或强制遣返。网友将这些经历发布到社交媒体,引发更多网友前往东师古。探望陈光诚活动成为社交媒体历时一年半、声势热烈的活动,直到陈光诚2012年成功出逃。我记得2011年秋天我第一次登记微博账户的时候,微博上几乎很多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网友都使用带着墨镜的头像。没有微博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权利意识与社会运动是不可能这么快出现并建立起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2012年至2013年间,中共宣传官员和党媒不断发出紧急信号,表示社交媒体是一个失守的战场,共产党必须收复,尽管当时审查已日趋严格,而且微博在2011年已经开始实行实名制。
4 开 始
卢昱宇是那一亿多新浪微博用户之一。他2011年开始用微博,被围绕艾未未和陈光诚一浪又一浪的热情所吸引。不过他既没有借钱给艾未未,也没有想过去东师古。看到那么多人去东师古被打,他发了一条微博说,你们不要去临沂找打了,不如去北京。
就这样一句话,遵义的警察找到了他。在派出所的问话中,警察问他为什么叫大家去北京。他如实说,我觉得如果想把陈光诚救出来,去东师古可能不是个好办法,去北京施加压力可能更有效。
警察做了一个笔录,把他放了。那是警察第一次找他。
那之后卢昱宇很快去了上海。他的姐姐在上海开一间小服装店,他在一个工地上找到一个安装管道的工作。他开始在微博上接触到更多东西,跟各地维权活跃者(他们当中很多都是东师古“毕业生”)线上聊天。2012年3月,广州十几位维权活跃者在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举牌,要求胡锦涛带头公开财产,要求自由选举权,当下被警察抓捕。网上很多人拍照声援他们。卢昱宇也想试一下。虽然他已经是个35岁的男子,但是话少、性格内向,对在大庭广众之下举牌的恐惧,比被抓进监狱的恐惧还要深。他想找个伙伴一起去,没找到。他在上海市政府门前犹豫了很久,最后在繁忙的南京路,他下了很大决心举牌,拍了个照就匆匆离开了。他把照片发到网上,表达对广州朋友的声援。
他的标牌上写着:官员公开财产。把选票还给我们。
两天后,警察在工地找到了他。他在干活,全身都是灰。他们把他带到派出所审问了一天后把他放了。警察禁止他再呆在上海。然后他去海南三亚呆了一段时间,呆不住,又回到上海。刚回上海第一天他就被警察找到。他被拘留了10天。警察还去骚扰他姐姐。没办法,卢昱宇只好再次离开上海。
这是2012年10月。在那些年多次公共事件中出名、并广受活动者尊重的吴淦(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屠夫)叫卢昱宇去福建。在那里,吴淦的朋友给他在一间塑料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福州,他不使用自己的身份证,生活相对安定下来。白天工作,晚上和周末自由的时间,他开始做一件事。他开始搜索那时候在各个微博上经常出现的群体抗议事件,然后他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这些信息。他是个有经验的搜索者。
他说,微博当时对维权群体事件删得还不是很厉害。他只有一个手机,刚开始的时候搜到的比较少。“最开始我记得每天能搜到八、九起,一两个星期后就开始慢慢多起来,每天有20多起。次年,他买了一个iPad,工作更顺利些。他会把搜到的信息拷贝下来,图片也保存下来,然后发到微博,再把来源账户附上,有时一个,有时几个。几个月后,越搜越多,每天搜出很多,他开始感到应接不暇,身心疲劳。他想找个人一起做,没能找到。他的账号 @darkmamu存活几天、或者一个月就会被删掉,有时候则存活的时间稍微长些。删掉了他就重新注册账户,叫做“转世”。他的粉丝最多的时候大约有一万人。
到2013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感到无法再一边打工一边做下去。生存的压力是真实的,是每天必须面对的。他打算放弃。他感到如果不能全时做的话,就没有多大意义。当他在微博表达了这个意愿时,没有想到关注他账户的人很多。微博上很多网友,包括几个非常活跃的抗争圈意见领袖,如晏今峰、莫之许、以及观察和研究社会运动清华大学教授吴强,都纷纷表示要帮助他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大家开始为他众筹,第一次获得了两万多人民币捐款。
5 李婷玉和‘非新闻’博客
李婷玉那时是在微博上关注卢昱宇的众多年轻人之一。她是广东人,1991年出生,当时是珠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的三年级学生,也是那几年涌现的众多关心社会公义、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之一。2013年初,她曾到广州现场参加对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审查和修改的抗议。因为这次经历,她成为政治警察注意的目标。国保审问过她,学校的政工教师也经常对她提出警告。
她和卢昱宇在微博上通过私信聊天,进入 2013年他们聊得多了起来。春天的时候,她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并且成为情侣。他负责搜索,并把搜到的信息发布在微博;她负责存档收藏。
但是她不仅仅负责存档收藏。她将卢昱宇的工作进行了升级。
首先她开设了一个博客,并取名为“非新闻”(news worth knowing),将每天搜索到的信息和图片上传博客。2013年6月,她开设了“非新闻”推特账户(@wickedonnaa),将每天搜集到的信息发到推特。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正规和专业。
2013年8月,卢昱宇从福州搬到了珠海,他们租房住在一起。卢昱宇每天搜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李婷玉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13年年底到14年的时候,腾讯微博、QQ空间还可以搜索,”卢昱宇说。“她天天做,做不完,会积压大概五、六天。太多了,特别是到春节前的一个月,农民工讨薪很多。每天随便一搜,有可能有几十起,数百张图片。遇到一起比较大的事件,可能会有上千张图片。她做不完。我记得当时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人来帮着做,但那个人做一个礼拜之后,国保就找上门,把他的电脑也搜走了。”
国保当然也找到了他们。“我要是违反了你们的法律,”他告诉警察,“你们可以把我抓起来。”警察没有把他们抓起来,但是骚扰接踵而至。房东受到压力,叫他们搬走;有人从窗口向他们恐吓;有人切断了他们的水管。
2014年春节过后不久,他们俩离开珠海,搬到了大理。李婷玉没有办理退学手续,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自动弃学,跟着卢昱宇离开了。
到大理之后,他们开始了一种隔绝的生活,把和外界的联系降到了最少。大理是一个旅游城市,外地人很多,物价便宜。他们在客栈居住,大约一千元一个月(约160美元),可以经常更换住地。卢昱宇不仅不用手机,而且不用自己的身份证。李婷玉用一张电话卡。他们使用VPN上网和发布信息。
他们每天工作至少八小时以上,如果不跟上, 工作就会堆积起来。周末或者长假日,内容比较少,他们会骑自行车出去玩,去洱海,去喜洲;有时候去古城逛街,听乐队,或者在小酒吧坐一下。
有时候会有外国记者就某一事件在网上联系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卢昱宇求证信息真实性的专业意识。“首先是通过多条信息源来求证: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信息源可以互证,再加上图片、视频、地理信息,就可以确认了。有些事件发生在偏僻的地方,信息源少,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信息源。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图片和视频判断,再与发信息的人联系,进行确认。至于更详细的信息,如事件起因、示威人数,我们通常也会联系当事人。像被抓捕人数这样的信息,信息源在微博上可能不会说。”好在那些把原始信息发到微博的人,都希望将信息传播出去。当卢昱宇找他们求证的时候,他们都很愿意讲。
他们被捕前最后一个帖子是2016年6月13日,记录了94起事件,类型包括工人抗议欠薪、农民抗议环境污染和强征土地、拆迁户抗议政府和开发商违约失信、业主就产权或管理服务进行维权、投资人抗议融资诈骗、退伍军人抗议待遇不公等。其中泛亚投资人集结北京国家信访局追讨投资款, 有上万人参加;复员军人到中央军委信访局集会,要求落实职级待遇、确认干部身份,有2100人参加。
在6月的13天里,他们一共记录了840起抗议事件,从每天34起到每天110起不等。这些记录,包括照片和视频,每天发布在推特。
活跃的推特用户大概都有这种感觉:看到这种定时定点只发内容、从不参与聊天、也从不发任何生活信息的账户,总不免对背后是谁、动机如何生出几分疑惑和不信任。我们难以想象 @wickedonnaa 背后是这样一个名叫李婷玉的千禧年一代,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子。她卢昱宇在做一项艰辛的工作。他们只有17K followers, 转推也不多,一般在几推到十几推之间。但这些似乎并不影响他们日复一日地坚持这项工作。几年下来,他们记录了7万多起群体抗议事件。
他们对这项工作充满了兴趣。“每天工作完都有成就感,”卢昱宇说。“因为这些东西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只有我们在做。”
他们搜集了那几年发生的重大抗议事件。2014年3月茂名一万多市民游行,抗议政府建设PX(芳烃)项目。2014年4月,广东省东莞裕元鞋业十多个工厂、近十万工人罢工,抗议公司在购买社保金上欺骗员工,导致工人退休后只能领到很少的养老金。同样是2014年4月,在浙江苍南县一个小镇,城管与摊贩发生冲突,一名中年男子因为在旁边拍照而被五名城管用榔头围殴至吐血,最终生死不明。愤怒的人群开始围殴这五名城管,接着几千抗议者将警车、救护车、城管执法车等砸毁掀翻。
卢昱宇注意到,“像城管打人这样的抗议,2013年的时候,平均每星期肯定会有一起规模比较大,上万人的。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从苍南城管打人那起事件后,类似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就明显很少了。我猜想政府针对此类事件有了一种专门的预警机制。如果街上有人聚集,他们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把它处理掉,就不会像之前那样有一个时间差来发酵。不是说现在城管不打人了,而是现在没有在民众中发酵的时间和空间了。”
他说,“环保方面的示威也是从14年以后就大规模下降了,不像2012年、2013年那样,有很多。2014年以后,政府应该是特别针对这种情况做了处理。”
卢昱宇和李婷玉在大理生活的两年多比较宁静,美好。卢昱宇说。“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工作。我话比较少,她会问我小时候的事情,有时候她也会讲一些她的事情,比如上高中的时候在学校广播站播音。更多的时候是她做她的,我做我的。”
他每天负责买菜、做饭。她不挑拣,什么都吃。他们养了一只猫,叫小臭。卢昱宇有一把吉他,有空的时候就弹一下。有时候,李婷玉很渴望社交生活,但是这样的愿望必须放弃,因为他们需要隐藏。那两年多,除见了一两次朋友外,他们摈弃了任何交往,即使从网络上知道有朋友来大理了,他们也不联系。有时候李婷玉会买一些小东西,买多了,又责怪卢昱宇不约束她一下。“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很苦了,就这么一点点奢侈,”他告诉她说。他们几乎没有吵过架。
6 危险临近
对终将来临的危险,卢昱宇有预感。
在2014年以及之前,他的新浪微博帖子转发量都比较高,有些可以转到上万,最少也是上百;转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帖子会被删掉。但是进入2015年开始,他的帖子网友经常无法转发了。他的 @darkmamu 账户的转世变种,一经发现就会被删掉。有人会在微博上私信他问一些奇怪的话,比如出钱删某条信息之类的。
有一次他收到了的Gmail邮箱两步认证的通知,他知道有人试图在异地登录他的电邮。
有一天他们骑电动车在古城的时候,路旁突然冲出一个人,卢昱宇慌忙躲避,他和李婷玉双双摔倒在地。那个人没有帮忙,也没有道歉,旁边一个女的三个男的,和那个人一伙的,站在路上旁观。“他们看着不像游客,穿着也不像游客。我感觉很不对。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发火,李婷玉还说了他们几句。就是这样一些迹象,也有可能是正常,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都是说不清楚的东西。”
他委托朋友对非新闻网站做了存档。
他从来没有和李婷玉讨论过被抓的可能性。但是,“她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做下去,肯定会被关进去。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记者曾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一直做到被抓去不能做的时候。”
“我记得我被抓进去之后,看到卷宗上写的是‘1517寻衅滋事案’。这可能就是当局成立专案组的日期。这个时间和我感觉到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很吻合。我能感觉到这不是大理当地的案子,后面也证实了,这是公安部的一个专案。他们在还没找到我们在哪里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找到我们之后,就委托给大理的警察和国保办理。他们提审我的时候,手上总是拿着一个单子。还有他们手上办案的那些资料,不是一个市公安局可以取得的,因为在新浪微博,那些资料是被删掉的,有些已经被删掉了好多年了,但他们都有。”
7 获 释
2016年11月7日,卢昱宇和李婷玉获得201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颁发“新闻自由奖”。 同年获奖的还有叙利亚记者Hadi Abdullah**、中国六四天网**。
在狱中,卢昱宇坚持不认罪。他不久前告诉德国之声, “有一次他们把我的案件升级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会被判7年以上的刑期,但我还是没有认罪。后来他们又发回检察院,改为‘寻衅滋事’,判入狱四年。检察官每半个月就会来找我一次,就会问我已经给我机会,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又说如果我不认罪就会判我很重。”
在监狱里,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无法得到治疗。
2020年6月15日,卢昱宇43岁生日后的第一天获得释放,旋即被警察直接送回贵州遵义。他在狱中时从检察院人员那里得知,李婷玉被判刑2年、缓刑3年。
卢昱宇出狱后第一件事,是寻找简— 李婷玉。他问了李婷玉的律师和其他朋友,竟然没有人有任何关于李婷玉的音讯。他发了一条推特,“Jane, 看到消息请联系我”。也许她会看推特。
最后他在微信上找到李婷玉的母亲。她告诉他,李婷玉结婚了,让他不要再找她。他不信。
后来他们通了一次话。她说她有了新生活,但是“她一直在哭,”。她说她出来的这三年多过得很苦。她还说,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三年就是和卢昱宇在一起的那三年。那一次电话后,他们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那天我从电话里听出来,她是相当恐惧的,” 卢昱宇说。“她都没有用自己的电话打,而是拿别人的电话打。”他决心不再去打扰她,希望她获得安宁。
卢昱宇出狱后,发现当下的政治环境比四年前更加恶劣了。“中国的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不会让你有任何空间,”他说。“在虚拟空间,它不会让你发声;在现实空间,它让你没有立锥之地,让你低头,甚至有些人会被威胁做线人。”的确,维权运动历经近十年一波又一波灭绝式的打压,似乎已经分崩离析,更加碎片化;任意羁押更加任意,长期羁押不判或者秘密审判正在成为常态。
令卢昱宇意外的是,往日的网友没有忘记他。他出狱后的两个月,收到了来自署名和匿名网友75封信。他在推特上开始了一个 #晒太阳 标签,把这些信贴出来。在监狱的四年中,他只收到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信来自当时也住在大理的维权活动者王荔蕻大姐,明信片来自一个匿名者,上面只写了四个字: “多晒太阳”。
“互联网有记忆,我们都有。你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还有许多人在挂念你,感谢你。”
“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你的,不如说是写给我的痛苦和良心……我没有勇气和力量做你们做过的事,也没有逃离开来的资本和胆色,只能想想你们,继续懦弱地活着。”
前几天,一个网友和他分享了坐飞机飞在高空时无端生出的快乐和自由感。
但是在老家,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没有朋友,没有人理解他。他的共产党员父亲叮嘱说:“不要去做什么坏事啊。”亲戚们敦促他“做点正经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总之所有人都认为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最关照他的当然是警察。出狱后,当局要求他到派出所综治办报到,办好电话卡之后要通知他们,他们要监控手机。平时有一个片警专门负责他,随时要知道他的消息。他被警告不许回大理,不许去北京、上海、新疆;去外地要跟他们汇报。秋天他出外一个月,到四川、福建、广东游览、见朋友。在广州,他被警察驱逐回来。最近警察在向房东施压,试图逼他搬走。
他还会继续“非新闻”或类似的工作吗?我们想知道,监控他的警察更想知道。不可能了,他说,我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一个月就会再进监狱。
夏天的时候,他开始写四年牢狱的生活,题目是《不正确的记忆》。他已经写完了看守所部分。接下来写监狱部分。他在推特分享了一部分。出人意外地,他是个非常好的作者。他的文字,如同他的性格一样,非常tart,但很精确。监狱的残暴,即使在纸上,也足以让人flinch. 我希望能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这个题目。
“我不是英雄,”他说。“我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中国】,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