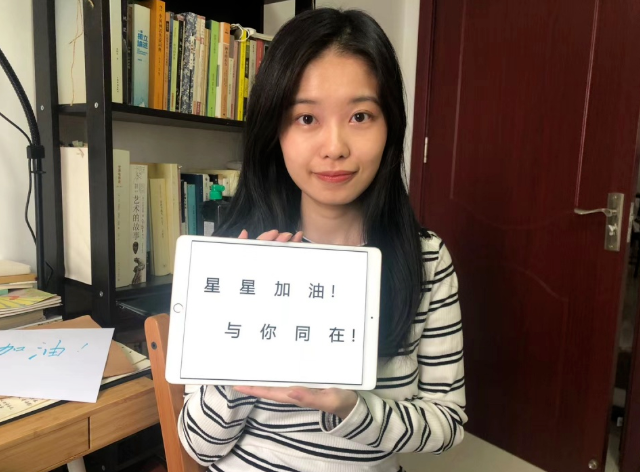牵动人心的“弦子诉朱军”案,日前已宣判,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弦子败诉。
两天来,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评论,都在指责她撒谎,诬陷了好人。我一个女性朋友看到后,跟我说:“朱军胜诉了。又一个玷污女权的案例。”我说:“但我觉得他还是失败了。”
让我意外的是,她说:“是的。晚节不保。这个弦子我到现在为止都搞不懂她的动机。怎么可以平白无故的编出这么大的谎言?这跟霍尊的前女友一个路子的,或者说后者跟前者一个路子的。她们是怎么可以做到昧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是很多人都很容易误解的关键点:弦子败诉,并不能证明她撒谎。从法律上说,“驳回诉讼请求”只是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证实她所提出的控诉。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人们普遍相信他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但证据不能充分支持、样本还遭到了污染,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只能将他无罪释放。
即便我们明明记得有一件事,但如何证明它发生过,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历史学家葛剑雄曾举过一个例子:某地某年冬天曾下了一场大雪,但如果没有历史记载、事后记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后人几乎就没有办法证明曾经有过这么一场大雪。
刘强东一案,电梯里的监控场景
像性骚扰这样的案子,由于其本身的界定就模糊暧昧,又常常发生在非公开场合,举证更为困难:有时是缺乏证据,又或有了证据也各有解读(例如刘强东案,女方在电梯里挽着他手臂,究竟是暧昧自愿还是出于礼貌?),更棘手的是,难以证明双方究竟是你情我愿,还是不情不愿。
近年日本的一起著名性侵案中,受害者伊藤诗织最终虽然获胜,但她在庭审中也被要求再三详细加以证明,自己在失去意志、被拖进酒店遭性侵之际,并未表示“情愿”。因为检察官将这种发生在私密空间里、没有第三方知情的情况称作“黑箱”。
在那样的紧张、慌乱中,当事人的记忆往往是“情感记忆”而非“事实记忆”。沟口雄三曾讲过一个故事:两国发生战争,B国的一位少女控诉自己遭A国一名身高2米的士兵强暴,但A国的法院予以驳回,理由是本国军队中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身高2米的。这位少女被强暴其实是事实,但她遭受创伤、恐惧之余,将加害者夸大为巨人,这是她的“情感记忆”,但法院却认定这不符合事实,忽视了她的感受。实际上,这正是日本右翼最钟爱的手法之一。
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当事人内心不可见的意愿,但不可避免地,这在实践中往往就意味着对弱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明清时代,由于国家对妇女贞节的标准越来越严苛,加上取证困难,女性在非法性行为中的表现,从主动参与到因恐惧而默许、忍受,都一概被视为“和奸”,只有非常激烈地反抗侵犯者,才能被认可为是遭到了强奸。
问题是:现代司法判决必须依赖有效的证据链,这样,调查取证的过程就成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在本案中,弦子一方在败诉后说,他们曾多次要求调取当时的走廊监控录像、化妆室内两人的合影等证据,但都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与性骚扰核心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不予调取”。
换言之,这个案子给所有潜在的受害者敲响了警钟:如果要提出诉讼,那就必须事先留意掌握对方不可抵赖的核心证据,否则不论事实如何,控诉将在法律上难以成立,最终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遭驳回。
弦子(左)与朱军(右)
尽管弦子败诉,但如果她在意的并不只是个人的荣辱胜败,而是推动国内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性骚扰案的程序正义,那么在这一点她并没有输,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获胜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她争取的是性别平等的权利,那在另一方那里,这个案件的意义却迥然不同——那事关“名誉”。这一点,在去年冬第一次开庭时朱军的声明中明白可见:
这两年多我承受了巨大耻辱,一直未发声,因我坚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我负责任的对所有观众说,我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我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到我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
在此,他以道德人品起誓自己的清白,并将之视为一场名誉之战。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出一辙:这类案子在帝制时代之所以要被法律追究,“不是因为当事者的人身权利遭到了侵犯,而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污染’(pollution)观念有关——它玷污了家族血缘、阶层差异以及女性的贞洁”(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只不过,如今是翻转了过来:那个以受害人身份出现的女性不顾自己可能遭受的人格形象玷污,而男性倒处于为自己的“清白”防守的位置。但如果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更应该坚持程序正义,在此基础上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一切都讲证据,那在水落石出之前,按说他也不应被打入冷宫,这难道不也侵犯了他的权利吗?
这也是中国社会需要上的一课。本案刚爆出时,赵忠祥曾表态支持朱军,理由是不该这样毁了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人”。这其中隐含的意味是,如果是一个好不容易功成名就的人物,就不该去毁了他,他应该受到特殊保护,跟普通人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那美国人当初因为莱文斯基事件,把总统弄得灰头土脸,岂不更是“民族的闹剧”了。事实上,莱文斯基一案在1998年爆出时,我周围很多人的反应都是:问题不在于克林顿有没有做,而是就算他真的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这样“小题大做”——用现在的话说,占用司法资源。
这也是在国内语境下性骚扰案的困难之处。因为这类案子中的双方往往在权力地位上不平等乃至悬殊。此前还有人推断朱军在公共场所猥亵不合理,然而,很多猥亵就是发生在人员混杂的公共场所,诸如地铁、公交上。所以,不要以为公共场合他们就不敢,制约他们的并不是他人的眼光,而是对方的反抗能力。
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不论这一案子的结果如何,这注定将成为一个里程碑。在第一次开庭时就有很多庭外的年轻人一声声高呼“向历史要答案”,确实,这样的进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样,一个新的篇章毕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