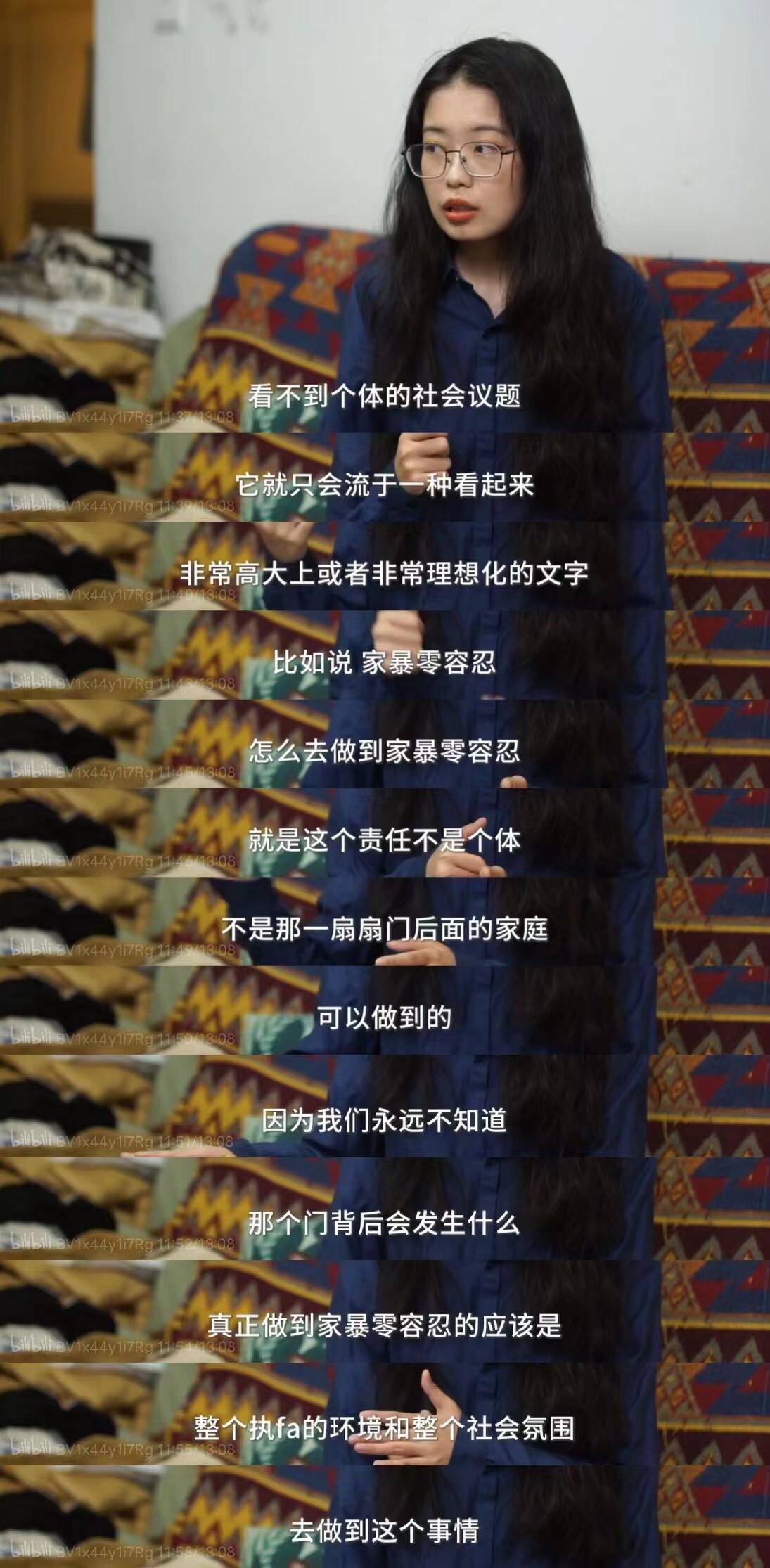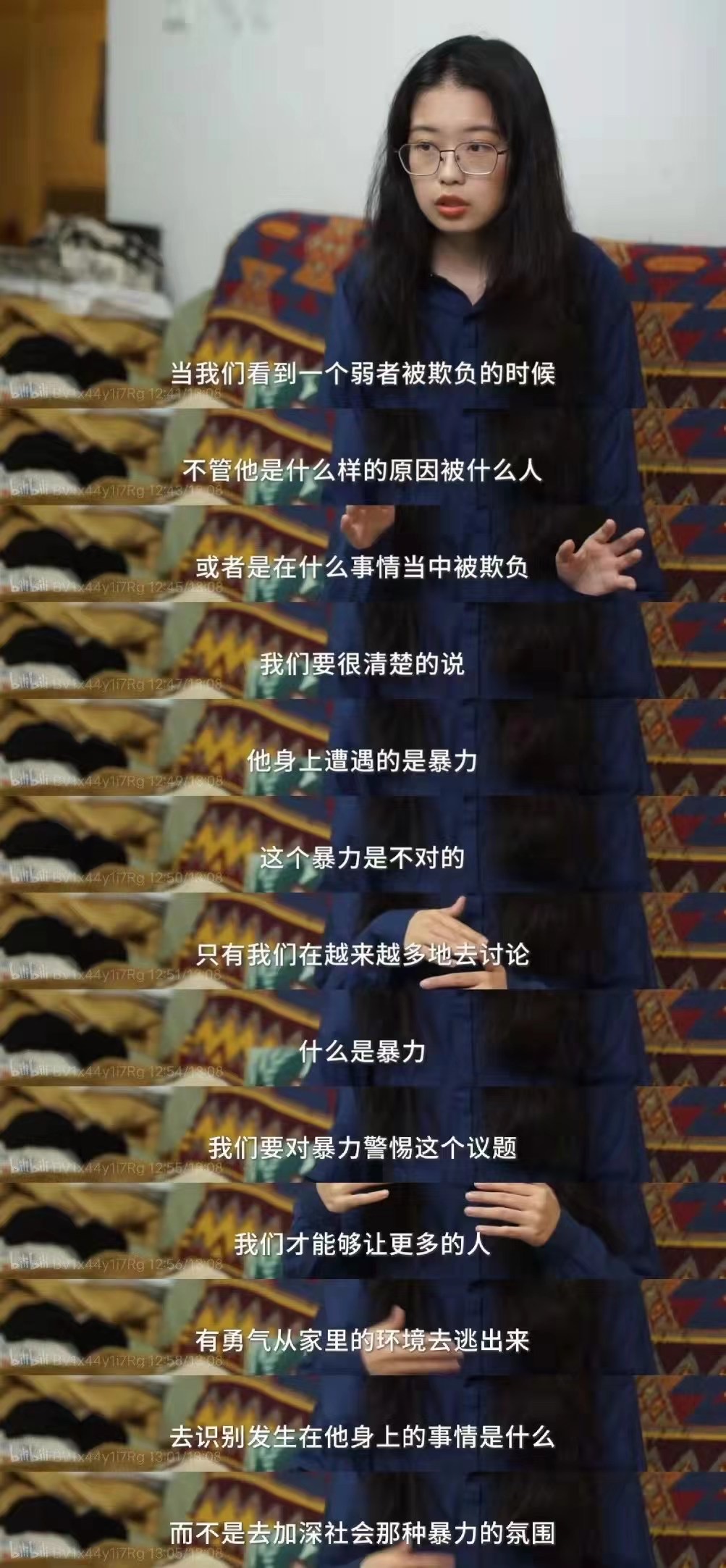拍摄时间:2021年春天
拍摄地点:弦子的家
此时距离弦子选择公开发声已经过去了三年。
弦子:
你之前上网的时候会很害怕被攻击,或者是你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或是不说什么。但是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不管你说什么,都会有一部分人在攻击你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表达出去。应该焦虑的是你有没有勇气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而不是你把这些话说出去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为了后者去紧张或是犹豫是意义不大的。
很多人觉得女性在被强暴的时候会拼命地去反抗,我那时候其实很震惊,我才知道大家其实不了解女性在被性侵的时候是会愣在那个地方的。你不敢去反抗,没有办法去反抗然后跑掉。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就是我必须得去做一个回忆,我得很完整地去把那个化妆室发生的事情讲一遍。这就意味着你要把你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你的创伤去暴露出来。
我开完庭结束后的那个星期,我要去写那篇文章,我觉得那就是我最痛苦最痛苦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在家里哭,从来没有写东西写得那么难受过。因为我还是会觉得在那个化妆室里的我的形象是一个很软弱、很失败的形象。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用受害者这个词,不管是我还是邓飞案的何谦,还是雷闯案的花花,在很多场合说自己的时候,都会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但是当你自己都不愿意承认你是一个性侵受害者的时候,那你怎么能说你是在很真诚地去讨论这个议题呢?我觉得你还是得去正视你的痛苦,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战胜它的。
Q:为什么要跟他磕到底?
弦:我当时其实从化妆室出来以后,就在给我的家人打电话,给我的大姑还有我的大学同学说这个事情。他们会跟我说,这个事情会影响你的工作,会影响你之后在北京的工作,因为我之后还是会在影视行业工作嘛。然后还说他的势力很大、很危险,大家都不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一直到我跟我的大学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在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很明确地表示她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体上而感到很难受。她听到我这个电话以后她就哭了,因为她能够想象我当时很痛苦,她在感受我的感受。她说我觉得你要去报警,主要是你去报了警后,起码之后他对其他实习生可能会收敛,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实习生去那里。
在那个化妆室里的一些肢体触碰本身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那么的痛苦,但是其实在这之后,比如说包括你在去维权、打官司的时候,大家因为各种牵强的理由,不允许你说出去、让你去放弃。包括在你站出来之后,也有很多人他会完全地否定你的经历,说你这个经历是假的,说你站出来的目的不纯。相对于身体上的伤害,这是一种对你整个人的否定。当你言说、阐述自己的记忆、阐述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事情时,你的这个权利被否定了,其实就是对你个体存在的一个否定。
14年的时候我去报警,其实除了我老师跟我说的话之外,还是因为我很天真地相信,他伤害了我,我就应该得到一个道歉。但是当你进入到这个系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不是的。其实他就是比你更有价值、比你更重要。你就是要为此去牺牲你自己的个人感受。在某个评价体系里面,其实你的感受跟你自己本人都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非常容易被抹去的一个存在。这个感受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是更让我觉得受到伤害的。
Q:公开此事过去三年,令你难受的是?
弦:我最近老觉得我要开庭,有的时候睡醒了之后我也会想:如果我不用操心这个事情就好了。我最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看法院有没有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开庭。我觉得这个状态很不好,人真的会变老的。你心里有一个很沉重的事情要记挂。
我跟我男朋友在疫情前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去日本玩,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朱军在湖北卫视复出,在主持春晚。然后我那段时间在日本玩,就没有办法玩,我每天都特别难过,因为那是我家乡的电视台,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就每天都在哭,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所有行程,其实都是他安排的,他都安排好了,我都没有管这个事情。然后他其实就是想带我出去散散心,但是你没有办法散心,你就发现你每天走在路上都在哭。在地铁里面都在哭。回到宾馆之后我男朋友也哭了,他受不了了,当时情绪已经崩溃了。因为我们在日本一共待了10天,但前四五天都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没有办法玩。你就是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事情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它在折磨你身边的人。
我之前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折磨我父母是因为我父母觉得,从中国家庭的常规来看,这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事情。因为我爸妈的同事其实很多都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痛苦,后来我妈那天哭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妈妈的痛苦是她很自责,她自责她当时在我报警的时候没有给我更多的支持。但是这个其实就会让你自己觉得更愧疚,这些情感都不是我爸妈应该去面对的。
Q: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两性教育有问题吗?
弦:性骚扰发生之后我都觉得很奇怪,就是真的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可能父母会比较有意识地去保护我。大家跟你说的性侵都是发生在比如说你走夜路的时候,坐公交车时,或者是你打了一个黑车,这就是我童年意识当中全部的、爸妈警告我不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跟你说,性骚扰更容易发生在权力关系这个结构之下,以及原来校园性侵这么常见。
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她们单位有一个习惯,在每年年会的时候,都会有人让年轻漂亮的女生去跟那些领导坐,每一桌都会坐几个很年轻漂亮的女生,然后会在结束之后让她们去跟领导一起去唱歌。其实这就是一种在权力结构下将女性视为性资源的一种方式。它最后又会变成一个女性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看待一个陌生人,你要把陌生人想象成一个好人还是想象成一个坏人。属于我们的安全空间已经很少了,但是女性难道还要为了保护自己退出更多的公共空间吗?你已经不走夜路了,难道你就不去当学生,难道你就不去实习了吗?
我们能够做到的还是通过法律,跟所有议题不断被充分地被讨论,跟在司法程序上的推动,让更多在权力上位的人意识到,你做这个事情是会付出代价的。你伤害别人,将别人视为性资源,是会付出代价的,你要去少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女性每天都在思考:我要如何去看待一个陌生人。
Q:为什么还积极帮助其他人?
弦:因为我自己的身份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所以我其实很容易被其他跟性侵有关的受害者相信。当我们建立了联系之后,我们可以很快就获得彼此的信任。然后我可以去介入到个案,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之前会一直觉得,很多性骚扰的受害者站出来做的表述不完美。大家会觉得这个受害者在撒谎,或者这个受害者有很多描述其实不准确的。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标准很高,受害者其实就是普通人,可能是大学生,可能都没有接触过很好的教育,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她想要维权的瞬间,就可以习得跟媒体沟通的技巧。他们会非常害怕在面对公众的时候,会遭遇比如说荡妇羞辱或者是境外势力的指责。
大家会觉得诚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涉及到暴露一个跟性有关的伤害,包括对公众暴露发生在你身上的让你感到最痛苦的经历的时候,我相信很少有人是可以天然地做到完全诚实的。之所以在Metoo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受害者的表现、跟媒体的沟通比较顺利,往往也是因为在她们站出来的时候,她们身边就已经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女权主义者或是社工、律师在旁边介入去帮助。但是这个对于很多我们接触的个案的女当事人来说,是很难的。因为她们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应激的、非常孤单的、非常看不到希望的一个状态。她们其实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才站出来决定去向公众求助。
获取一段真实的经历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当你站在这个人面前说我要帮助你的时候,她就有义务把自己所有真实的事情说出来。尤其是当那些真实的细节会给她带来伤害的时候,她是完全有权利选择不说或者是选择隐瞒的。但你要取得她的信任,其实意味着你自己作为助人者,你要付出更多。你需要不断地去告诉她,我可以理解你,我可以保护你。我不会在任何事情上面指责你,不管你是想要放弃,不管你当时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不会因为一些事情去指责她,你不会因为一些事情去要求她做她不想做的事情。就只有在你自己作为助人者表现得足够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获得一个真正的故事,你才有可能获得对方的信任,让对方把所有经历跟你去讲。因为其实没有人有义务把最真实的事情透露出来。尤其是当这个经历会对她自己构成伤害的时候。
我觉得换位思考的能力其实从来不是人天生就有的。在参与到所有的你关注的社会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就是你去考虑这个受害者当时的处境是什么,然后去站在她的处境去思考。我们接触到的可以去处理的个案不单只有性侵这个议题。包括跟家暴受害者之类的,你也可以跟她们去建立一种彼此信任的一种情感联系。
Q:如何看待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里的暴力?
弦: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地你会很适应暴力的。很多人会说女生不适合理科,这个你也不可以做,那个你也不可以做,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对于女性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接受这些。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不管是就业歧视还是高考的歧视,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女性,她没有办法去识别暴力。当暴力被常态化的时候,你就是非常难从暴力的控制当中逃脱出来。
拉姆案当时刚爆发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给他生两个小孩?如果在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他就打你了,你还要生第二个小孩,这就是对小孩的不负责任。很多人会指责拉姆,哪怕拉姆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去问这个男性,你为什么要去打女性?为什么不能够去问警察,去问执法人员,你为什么不在接到报警的时候马上立案去处理?你去问法院,你为什么不开人身安全保护令,你得去问他们,而不是去要求那些个体、那些受害者。中国之所以反家暴法、性骚扰还是家暴等等议题可以得到全社会那么多的关注,就是因为那些受害者站出来了。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她们的经历,大家才意识到她们身上受到的伤害有多么的惨痛。
看不到个体的社会议题,它就只会流于一种看起来非常高大上或者非常理想化的文字,比如说:家暴零容忍。怎么去做到家暴零容忍?这不是个体、不是那一扇扇门背后的家庭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门背后会发生什么。真正做到家暴零容忍的应该是整个执法的环境和整个社会氛围。当我们用非常暴力的语言去指责那些受害者、指责那些女性、指责弱者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难意识到,其实你也是在使用暴力去做事。而当暴力越来越常态化,充斥在整个社会,人们就会越来越难以去识别暴力、难以鼓起勇气去逃离暴力。尤其是当她觉得外部也很暴力的时候,人是很难从家庭内部去逃离出去的。这方方面面其实都是一种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种非常暴力的语气跟大家说:当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真空,生活在一个露天环境里面就可以去逃离暴力。我们只能够尽量地让大家对暴力产生警惕,当我们看到一个弱者被欺负的时候,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被什么人,或者是在什么事情当中被欺负,我们要很清楚地说,她身上遭遇的是暴力,这个暴力是不对的,只有我们在越来越多地讨论什么是暴力,我们要对暴力警惕这个议题,我们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有勇气从家里的环境去逃出来,去识别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去加深社会那种暴力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