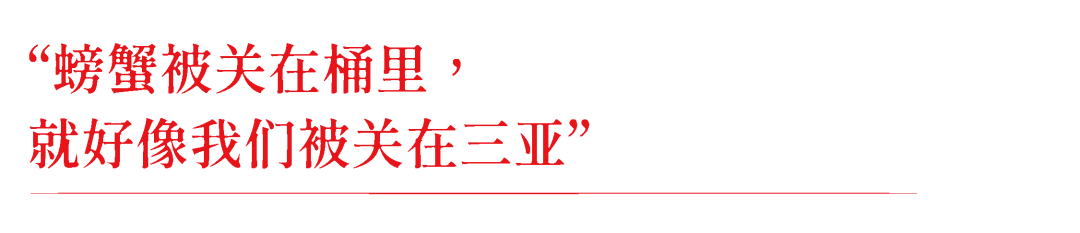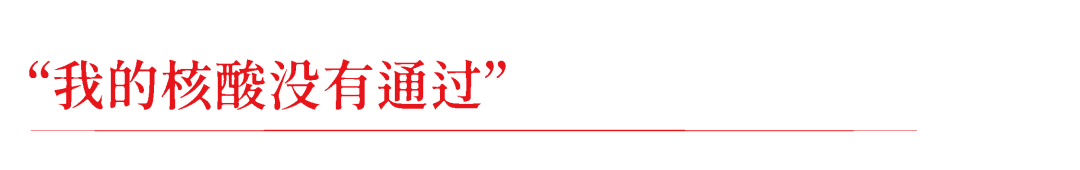前文(点击可阅读)提到,我和朋友两家人于8月初到三亚旅游。8月6日三亚封城,我们逃跑失败,带着孩子们与八万游客一同滞留三亚。
在三亚滞留的几天,我仿佛走在一条布满迷雾、不可回头的路上,这条路有若干分岔,每个分岔又有新的分岔。没有人知道每条小路的尽头是什么。我只能凭手头有限的信息分析、判断和决策,然后带着孩子们往前走。
每天我都在问自己,今天我所做的决定正确吗?
8月7日,我们得知我们所在的Y酒店即将被转为隔离酒店,我们决定立刻转去另一家酒店。我联系了曾住过的X酒店,对方表示还可以接受新客人,但交通需要自己解决。
此时交通已被严格管制。没有滴滴,没有出租车,没有巴士,黑车不接单,Y酒店表示无车可派。朋友辗转联络到一位住在其它酒店的朋友。他租了车,可以载我们去。
X酒店前台等待办理入住的客人比我上次来时少了许多,但空气里依旧漂浮着柔和的音乐和宜人的香氛。工作人员依旧奉上欢迎饮料,又递给小朋友们人手一只彩色气球。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我们不禁觉得:来对了。
封城后的最初两天,游客们关注的焦点围绕着食宿费用。
虽然政府给予了房费5折的建议,但是,在X酒店,我们一行6人分住三个房间,每天的房费折后仍需三千多元。最关键的是,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够离开,每天三千多的房费需要付多久。
X酒店虽然仍开放堂食,但午晚餐人均消费一两百元。如果全部都在酒店吃,每天6个人需额外花销上千元,这也是个不小的负担。
此时海棠湾的餐馆几乎已全部关闭,几家仍能送外卖的店家生意火爆。朋友下午3点订的外卖,晚上9点才送到。孩子们都饿得眼睛发绿。
我们于是常常用泡面解决正餐。存货很快告急。但外卖平台上的超市也已全部停止营业。有一天,我发现某个小超市可以下预订单,我赶紧下单,然后打电话过去确认。店主在电话那头慢吞吞地说,“我们都是半夜送的,你安心睡,不用等骑手电话。” 在睡梦中,我预订的半箱泡面被放到了酒店大堂门外,第二天店主还来电确认是否收到。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本地人的务实和友善。
孩子们依旧每日在海滩挖螃蟹,在泳池游泳,嘻嘻哈哈,看起来对大人们的忧心忡忡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在电梯里,8岁的大女儿突然说:“早餐要多吃点,吃饱点,因为早餐是免费的,这样午餐可以不吃或者少吃。”大家都笑了。
8月8日,一些酒店的旅客收到政府的慰问物资,包括泡面、面包、酸奶、火腿肠等。同日,X酒店的堂食菜单被砍掉了2/3,因为装载食材的车辆无法进入海棠湾;酒店员工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库存的食材还能撑多久。
继续待下去,会有一天没饭吃吗?
8月9日,送我们来X酒店的朋友告诉我们,他所在的酒店在核酸检测中发现混管阳性,所有客人被关在自己房间里复查核酸。同日,另一家老牌五星级酒店曝出阳性确诊,全店客人就地隔离7天。
我们有点慌了,可怎么才能离开呢?
8月9日晚上9点,上海政府宣布,从海南低风险地区回来的人员需要实行三天集中隔离加四天居家隔离。在此之前,同样的人群只需实行三天两检。
我的心沉了下去。在经历上海的两个月封控之后,再多丧失一天人身自由都让我难以忍受,何况这次还要集中隔离,和孩子们一起。
航班仍未恢复。我为一家4口买了连续5天5个航班,一共20张票,然后一天天地看着它们依次被取消。
这一天,孩子们终于在海滩挖到了螃蟹。那只蟹拼命地想从桶里爬出来,但桶壁太光滑了,每次爬到一半都掉了下去。蟹腿在桶壁上不停地划拉着,呲啦,呲啦。大女儿看着那只蟹,突然说:“螃蟹被关在桶里,就好像我们被关在三亚。”
8月10日早上6点,海南政府开放网上离琼申请。同日,酒店发来一张“致滞留三亚旅客的一封信”,落款是三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部”)。信尾有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即可填写返程申请表。信上写道:将按照返程目的地旅客人数进行排序,依次安排航班转运。
这封信拉开了政府包机转运滞留旅客的序幕;而这张申请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酒店将根据申请表里填写的信息整理客人名单,并上交给指挥部以供挑选。
并不是所有滞留旅客都有机会填写这张申请表。
某航空APP上显示,包机的每日客运量仅占之前商业航班客运量的2%。这是人为造成的资源极度紧缺。而这极度紧缺的资源如何分配,取决于指挥部。谁先走谁后走,没有公之于众的规则。
后来再回头看,在酒店客人和散客之间,指挥部选择了让相对好管理的酒店客人先走;在无数家酒店之中,指挥部选择了酒店相对集中、疫情相对轻微的海棠湾先走。
我们就在海棠湾。海棠湾有上万游客,而每天能走的不到千人。
游客们迅速建起了微信群。人们在电梯里,在餐厅里,在排队做核酸时,彼此询问:“加群了吗?”我加入了三亚逃难群、返沪群、回家群、X酒店滞留群,等等。
各种小道消息在各种群里流传:今天某家酒店走了多少人?明天可能有去哪个城市的航班?隔离酒店不肯搬走的游客是不是被优先安排离开了?为什么有些酒店排在前面?怎样才能进入指挥部的回家名单?
有人说自己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用来打电话,给酒店,给文旅局,给12345;有人说自己起了满嘴的燎泡;有人说自己让小孩穿着外出的衣服睡觉,因为担心半夜突然得到通知要走。
大人们每天在希望中醒来,在焦虑中煎熬,在失望中入睡。而孩子们兀自玩耍。我和朋友的两个大孩子挖螃蟹的技术日益精进,有一天竟然一气挖了5只,最大的有手掌大小。5只螃蟹都想从桶里逃出来,呲啦呲啦呲啦,很吵。我把小桶放进柜子,关上了柜门。
8月11日上午9点,有消息说X酒店当天有人上了返沪名单,只要有连续三天的阴性核酸记录就可以走。然而此时,我发现两岁的妹妹缺了第1天的核酸记录。
8月初我们来三亚时,机场采样人员说三岁以下不用做核酸;也许因为此地的医护人员还不熟练,自从有一天被捅得干呕之后,每次捅喉咙之前妹妹都要大哭一场,躺在地上一边蹬腿一边哭叫:“三岁以下!三岁以下!” 所以有两天,我心一软,没有强迫她做。
我来到大堂,看到前台经理被询问返沪名单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我觑着空子将她拉到一边,小声哀求她派车送我和妹妹去301医院补做核酸。医院采样,出结果比酒店采样快得多。如果妹妹的核酸结果下午两三点出来,也许我们还能赶上当天回家。
在去医院的车上,妹妹奶声奶气地说:“我的核酸没有通过。”司机听了哈哈大笑。
一切都很顺利,妹妹的核酸结果很快出来了。我们收拾好行李,在房间里等待。但是,当天X酒店无人接到返沪通知。
8月11日下午,有传闻说,上海多日无阳性新增纪录被三亚回去的游客打破了,上海即将禁止三亚游客返沪。
这条传闻当天傍晚就被证伪了。但在当时,它正好契合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上海游客内心最大的恐惧,所以我们立刻就信了。朋友和我快速商量了几分钟,当即决定更改目的地。她和孩子投奔A市的孩子外婆,我带着我的孩子们去位于B市的奶奶家。酒店在电话里再三问我们:“您确定要更改吗?”“是的,确定。”我们回答。
几小时后,8月12日凌晨2:30,大量上海客人接到X酒店的电话通知,准备好当天早上返沪。我们没有接到。朋友半夜3点下楼,恳求将我们加回当天的返沪名单,但前台经理说更新后的名单已上报指挥部,无法更改。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只是托辞,但当时我们慌乱得犹如没脚蟹,竟没听出破绽。我们又询问前往A市和B市的新名单何时上报给指挥部,这次前台经理回答要等到早上9点“志愿者”上班后。
指挥部向每个海棠湾的酒店派出了至少一名志愿者。驻扎X酒店的这一位,高大胖壮,戴小蓝帽,穿印着“海南志愿”的蓝马甲。当游客问他到底什么人可以上回家名单的时候,他说“由我们根据大数据综合判断”;当游客要求安排回家航班时,他说“我只是个志愿者,没有这个权力”。有消息说这些志愿者来自三亚文旅局或文旅集团,但这未经证实。无论如何,在戴上蓝帽子,穿上蓝马甲之后,他具备了可官方可民间的双重身份。X酒店的游客们都叫他“蓝帽子”。
8月12日上午,X酒店发来消息说,由于修改目的地的人太多,指挥部即日起不再接受新的修改申请。这意味着,如果我和孩子们没能被选入前往B市的名单,我们很可能也无法改回上海了。
同日,前往B市的包机再次被取消。坊间传闻,B市严控从海南回去的包机数量,平均两三天才允许一架航班降落。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此时酒店已关闭堂食,改为提供盒饭。我的盒饭正好到了,里面有几块排骨和鸡翅,一些龙角豆和一格米饭,一共要88元。盒饭没有附送筷子。我本可以打电话请酒店送筷子来,但发现自己竟没有力气拿起听筒。我浏览着关于B市的消息,慢慢地用手抓着把饭吃完了。
吃完饭我又一次来到前台,询问新名单提交了没有,询问何时可以走。前台小哥答应帮忙叫前台经理出来,但随即又说经理不在。他看着我的表情,小心地说,“我们也希望你们快点回家。今天是我在这家酒店的最后一天,我也不想干了。我老家在江苏,我也想回家。”
我内心烦乱,下楼乱走。楼下大堂人声鼎沸,人们成群地向前台后方的办公室走去,志愿者和前台经理们都在那里。办公室门紧锁着。有人开始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越来越大。终于窜出来一个人,是金头发的外国人,X酒店的总经理。他一边说“外面,外面”,一边往外走,人群跟着他回到大堂。
谈话很快变为争吵,争吵声越来越大,随即人们开始一起喊:“要回家!要回家!要回家!”总经理扭头就走,但被团团围住。他推开一位女士,女士倒在了地上。人们立刻喊:“老外打人啦!老外打人啦!”他跑向办公室,又被拦住,随即倒地,人们又喊:“老外假摔!老外假摔!”总经理窜回办公室。民警很快又来了,这是这两天的第四次。有人说,“来得正好,请民警同志为我们做主!”又有人说,“他们么,没用的,他们又不管回家的事的咯。”
酒店是否尽了最大努力为住店客人争取?酒店是否消极应对,以便强留客人赚取房费?酒店是否存在高价宰客行为?这些都不重要了。五星级酒店用金钱打造的柔软、宜人和舒适荡然无存,商业文明温情脉脉的轻纱被撕得粉碎。焦虑和愤怒已席卷人群,每个人都已沦为斗兽场里的兽,使出浑身解数,只为一个目的——回家。
8月13日,我突然接到酒店电话,说我们在这一批的返沪名单上,当晚可能可以离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离开了。
我们收拾好行李,终于想起柜子里的小桶还装着5只螃蟹,于是走到海滩上放生。这一天风平浪静、晚霞满天,姐妹俩放倒小桶,一只大螃蟹蹭地一下子爬出来,吓了我们一跳。但是,除了最大的这只,没有更多的螃蟹爬出来。姐姐小心翼翼地翻动桶里的沙子,只找到一条蟹腿、两只蟹钳。那4只小螃蟹应该都被吃掉了。我们悚然一惊,目送那只大螃蟹消失在波涛里。
13日夜里,我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把铃声调到最大,等待随时可能响起的电话。
14日凌晨3点,我接到航司电话,点击链接购买了机票。
14日早上7:30,我接到三亚市政府办的电话,说早上8点左右会有巴士来接我们。
我们拖着行李箱在大堂里汗流浃背地等了一个多小时,但仍然无车来接。我去找“蓝帽子”。
“蓝帽子”说,“我正在跟机场确认航班何时起飞。因为怕你们到太早,在机场里等,白白增加风险。你愿意在机场里等,还是在这里等?”
几分钟后,我见他在角落里打电话。转头他又把前台经理拉到一边,说:“现在有另外几个客人也想坐今天的这个航班,我们正在协调,你先安排客人回房间等候。”
我知道无法可想,只能回房等待。又过了一小时,已经到了航班原定的起飞时间。我突然接到航司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大声说:“你们怎么还没到机场?!其他人都到了,我们马上起飞了!”
我飞奔下楼,冲进办公室,向蓝帽子争取立刻开车。一番吵闹之后,巴士终于开动了,绕路Z酒店接了一个男人、一个妇人和一个小孩。
航班太少了。但是,只要返回家乡的游客还需要集中或居家隔离,需要当地政府调配资源管控,航班就不可能大幅增多。
8月14日,就在我们返沪的当天下午,在前往集中隔离点的大巴上,我看到上海发布宣布:次日起自海南返沪的游客无需集中隔离,落地检验核酸后居家隔离。
同日,三亚宣布次日起停止政府包机转运,有序恢复商业航班。
踏上返程的游客开始增多。截止到8月17日早上6点,海南已有累计7万多名滞留旅客乘机离岛。
据官方统计,因疫情滞留海南的游客大约有15万。我有好几个朋友现在仍在三亚、博鳌,或者海口。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家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作者目前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
这篇文章是坐在厕所里这个盆上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