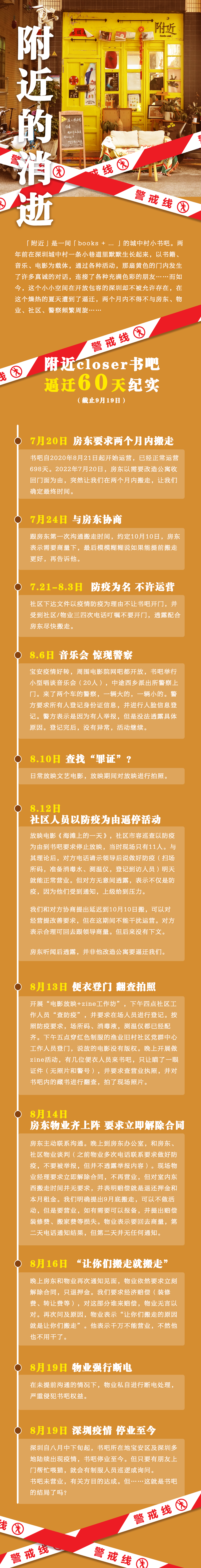01.
我从未想过这是书吧的最后一天
深圳八月初的傍晚一如既往的燥热,蝉鸣如昼。书吧老板反复和社区确认,早早准备好场所码、测温枪、酒精、登记表、口罩——只要做好疫情防控,就可以继续开门。
大家放下心来,准备放映的影片排到了九月,各种活动也安排在了不同的周末,朋友们热切地盼望着周末的到来,喝酒,聊天,发呆,一起做些活动,一扫工作的疲倦。
平静的时光被突如其来的闯入打断。先是拿着“特制场所码”的社区工作人员出现在门口,盯梢一般,要求大家扫码,并且对朋友们进行拍照。
二十分钟后,两位穿着红色马甲制服的中年男子与两位便衣的男子闯了进来,自称来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抓着参与活动的朋友一顿盘问:“你们不能聚集!”、“你们都扫码登记了吗?”、“你们看的东西有版权吗?”。最后似乎没有发现可以指责之处,便悻悻离去,走之前建议我们放些“正能量影片”。
大家好不容易从混乱中缓过来,村里的小朋友也加入我们开始一起快乐地做拼贴画 ,又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了进来,带头的是两位穿着蓝色衬衫的人,看起来大腹便便的,态度非常强硬,“把营业执照拿出来查!叫你们把营业执照拿出来,干什么啰啰嗦嗦”。
后面跟着四五个年轻些的男子,举着手机拍摄当晚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在门外还有几位男子没有进来,只是偷偷摸摸的观望着。
在我们质问他们有什么资格闯入的时候,他们一直不肯表明身份。并且挤开做拼贴的朋友们,把书吧的书籍和版画翻了个遍。仿佛抄家一般,对每一本书、每一张画都仔细的翻看,不知是在查找什么。
在并没有什么“收获”之后,他们背着手离开了书吧,却还在默默讨论:“不是说他们在看电影吗?怎么是在画画……”。
附近最后一场活动 截止至8月14日,附近一共举办了248.5场活动
这不禁让我一阵头晕目眩:他们凭什么可以擅闯私人空间?
然而这并不是附近第一次遭遇盘查。此前,就有不少“社区人员”反反复复以“疫情防控”为由,打断书吧的活动,他们肆无忌惮地打断观影,随意翻查书吧里的书籍和陈设,对不明所以的朋友进行审问。
一起做手工的朋友们被突如其来的氛围吓住了,小心翼翼地要对方说明身份,却被厉声威胁“态度好一点”。
这个平时温暖和谐的小房间里,氛围降到了冰点。经历了这场“大检查”,朋友们有些不知所措。几位朋友慌张地收起了架子上许多带“女”字的书,我们已经不明白何处是“边界”。
惊恐的朋友们一个个离开,带着对彼此的珍重、对书吧的担忧,互相拍拍肩。不知这一天究竟会给这间将冷漠城市中残存爱意之人链接起来的书吧带来什么,不知我们何时才能再聚。
02.
让你们搬走的原因就是让你们搬走
8月中旬,房东和物业开始向书吧施压,要求立刻解除合同,让书吧搬走。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理由,只丢下一句:“让你们搬走的原因就是让你们搬走。”
书吧(以合约并未到期为名)要求经济赔偿、要求时间缓冲做好收尾工作、要求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在我们与房东争辩的时候,几位穿着制服的警察从门口向里张望着。
一个月前,房东还曾经以“房子要改造成公寓”的名义,希望书吧尽快搬走。虽然合同约定的房租期限还有半年,但书吧理解并接受,只是想在最后一两个月里,留出一些时间让书吧的朋友们再聚一聚。直到后来才从社区干事说漏的口中得知, “房子要改造成公寓”这个理由居然是编造的。
8月19日,书吧被强制断电了。此后这里开始被漫长的寂静和黑暗笼罩。我们并不知道物业单位有什么依据对一个正常营业中的场所进行断电,但书吧从营业的第一天起,从没断缴过电费。
一幢黄色房子,一张橙色沙发,一只叫马小软的猫,书架上满满都是书吧和书吧的朋友们收藏捐赠的书籍,只借不卖。有酒有咖啡,有一群有趣的人儿,做着自由的事。门口的衣架上还晒着书,对联是两年前的除夕挂上的那副:心中唯存歌和友,门内只富书与酒。
“持此山上心,待君忘情友”
这是相聚的初心——在流动性最强的深圳搭建一个“附近”,让表面的、浅尝辄止的、非功能主义的相遇有一个温暖的落脚点,让冷漠的货币媒介被隔在屋外,让久违的共情、关切、团结而多元的共同体生活重现人间。
曾几何时,这里有观影会,有音乐会,有读诗会,有换书会,有聊天茶话会,有手工工作坊,有真人图书馆,有爬山,有飞盘,有朋友们举办的跳蚤市场和个人展——但这一次,只剩下了告别。
附近其实并不近,大家常常玩笑“转个湾到”,实际上从深圳中心区到宝安这个城中村的小角落,地铁整整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常常无分工作日与否地赶来,挤在这个小小的精神角落,一起看“义务放映员”为大家放映的片子,围坐一圈,观看自己,了解他人,通过分享和讨论触碰彼此,打开对世界的认知。
人人都是书吧的主人,书吧也并不谋求盈利——能保本就谢天谢地了。
来到附近的人是小小的偶然,许多“边缘人”在此相识,有了共鸣,有了故事,有了联结和慰藉,成为朋友,遇到知己,终于与“深圳”这片广阔而悬浮的大地,有了精神上的连系。
03.
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从没想过宣扬“开放包容”的深圳,容不下一个温暖的“附近”——附近或许是这个冰冷沙漠城市里,无数打工机器人的充电站:在这里,没有阶级尊卑,没有职级薪水,没有商业利益,只有思想的碰撞、会心的笑声、同伴的关怀。这样一个去商业化的角落并没有死于商业竞逐、资本挤压,可它到底死于什么?我至今都没有答案。
宾至如归——附近的德国朋友在社交网络上写道,“从今往后,深圳再无可以回去的家了”。他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生活在深圳的人,对于深圳的自豪和信任,也如山崩不可挽回。
作为一个不愿隐忍沉默的市民,我心中有无数疑问:
是深圳人配不上“附近”,还是“附近”配不上深圳人?
为什么连聊天和手工活动都要遭受监视和骚扰?为什么连“出示证件”的要求都不能被表达?
为什么连一个理由都不给,就对“附近”下了搬迁通牒?
或许一切迟早都要结束,但在告别之前,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附录:附近的消逝
希望朋友们给予附近精神支持,欢迎大家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