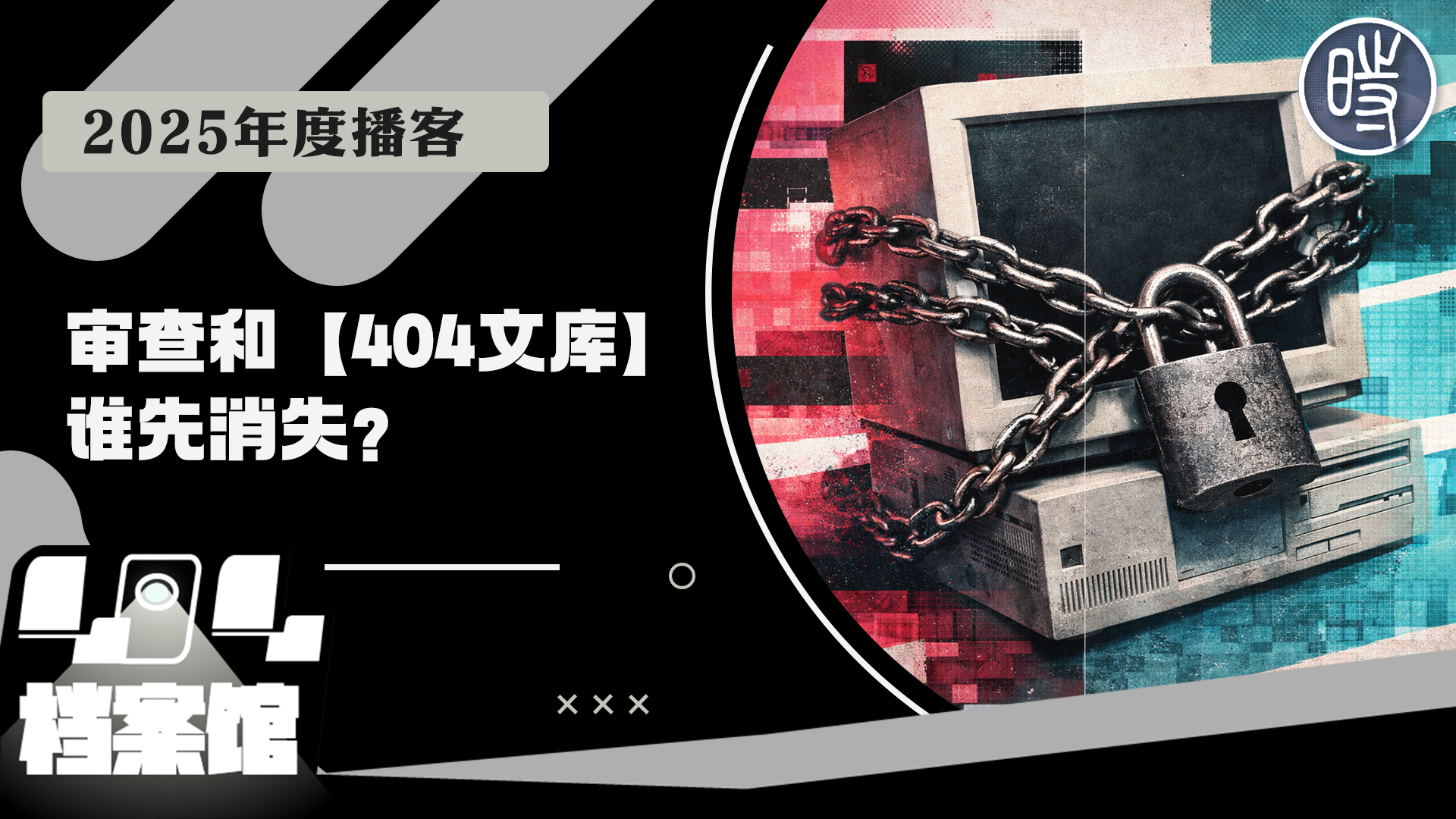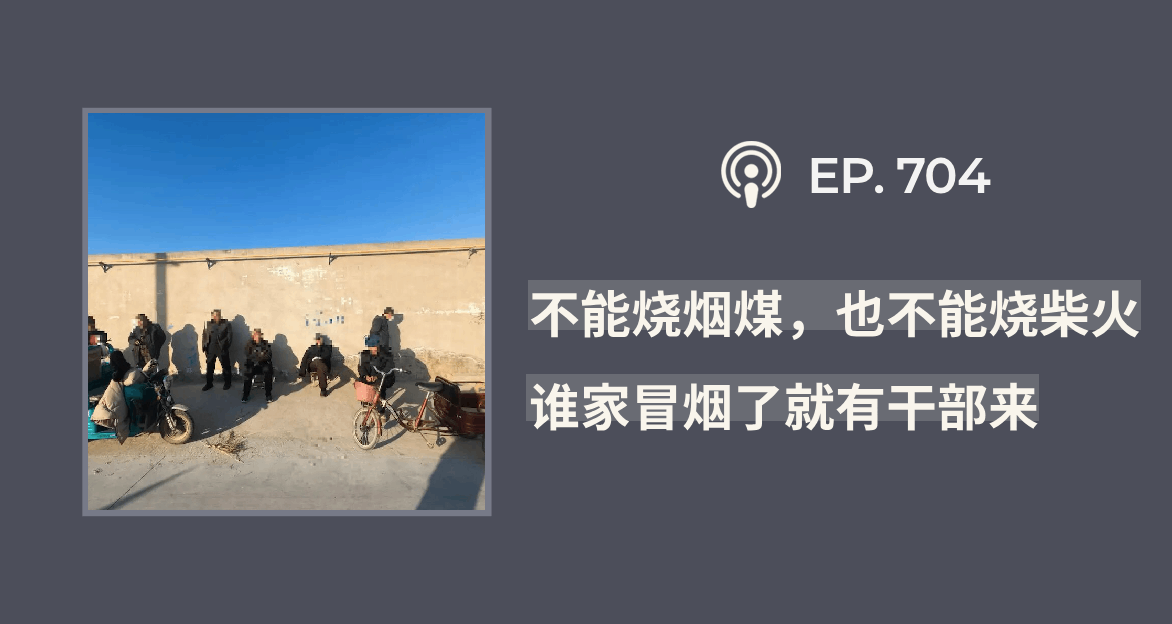知名辩手席瑞在评论唐山打人事件时,层层分析其背后的动因,着重聚焦于一点:男性对女性的危害性,永远不该是男性气质的呈现。不仅如此,他指明了这种有毒的男性气质之所以盛行的文化心理机制——不仅是打人者,还有那些袖手旁观的男性,无法体察到女性的处境。
评论区里有人惊叹:“这是我第一次听懂和认真听清男性为什么在女性有危险的时候,对她所处的环境和对这个女性有鄙视甚至于旁观的原因。我一直以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为女性有时候也有这种想法。现在我才明白男性为什么,因为没有同等的感受,他甚至可能觉得女性是因为本身种种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女性本身就是一个弱者,经常会受到这种危险的困扰。”
另一位将之概括为一句话:“就像席瑞说的,男性永远没办法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
但是等等,请注意:席瑞本人就是个男性啊!毫无疑问,他本人的清晰论述就在证否这个判断,至少他(甚至比一些女性更好地)做到了“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事实上,这样绝对化的论述,也不可能出自席瑞这样的知名辩手之口,因为那太容易遭到反驳了。
当然,你也可以争辩说,这并不矛盾:“男性”是一个全称,说“男性不能理解女性”,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男性都不能理解女性”——在哲学上,这就是all(所有,全部)和everyone(所有,每一个)的区别。所以第三帝国时期常有这样的说辞:“犹太人都是魔鬼,但我认识的那个犹太人真的是好人。”
也就是说,就算有一些例外,但人们仍然可以坚持认为那个全称判断是成立的,毕竟信念很难被经验事实所动摇——何况,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一点也确实是成立的。
赫尔曼·黑塞曾感叹过:“一个人若要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大概必须有过类似的处境,受过类似的痛苦,或者有过类似的觉醒体验,而这却是非常罕见的。”
完全的同情理解,即便一家人之间也很难做到;甚至就算是在女性内部,不同处境和体验也会阻碍共情。《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中指出,美国反堕胎的激进分子多是操持家务的妇女,占了63%,而选择权利激进分子的女性,则94%有工作。
更有甚者,同一个人都可能因经历差异而转变立场。1973年历史性的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女主角诺玛·麦科维,在赢得诉讼多年后,宣布放弃拥护堕胎合法化,转为支持生育的积极分子。保守主义者艾伦·卡尔森曾讽刺:“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有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
照此说来,男性要理解女性可想有多难了,毕竟他缺乏相应的体验,有些人干脆认定那是不可能的——对中国男性中就更不可能了。
类似的说法,我听过无数回。我自认在男性中算是支持女权的了,可是每次讨论性别议题,有什么和女性稍有不一致的,就经常听到对方甩过来一句话:“维舟毕竟是个男的。”
我当然是男的,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也没有任何不满,只不过话说到这份上,就讨论不下去了。很多的讨论,到最后就是下个判断,然后结束对话:暴露出本质特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行,到底还是个男人/上海人/理客中,不跟你说了。
这种泛性别思维,原本其实是男性用得更多,他们常常嗤之以鼻地表示“女人毕竟是女人”。其关键之处,是无法个别地看待人,我的其它特性,都被认为不如男性重要,因为男性才是我的本质属性。这样,本质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就像血统,天生就有,无法改变,也是一种特权。
这样的本质主义论调,意味着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人不可能采取和自己身份不一致的立场。照这逻辑,那就不存在慈善这回事了:做慈善的那些富人,怎么可能真正理解、同情穷人的处境?事实上,很多人对“白左”的反感正是基于此:那些人高高在上、惺惺作态,与其说是真正理解同情,不如说只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优越感和姿态,由此自我陶醉而已。
在性别政治中,也一直有人相信,那些“男性女权主义者”是不可信的,往好里说也是缺乏道德真诚、动机可疑的。有位朋友(他本人也是男性)挖苦:“一个男的,非要完全设身处地站在女性角度考虑,不吓人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对太能‘共情’你的人,还是留个心眼……”
我能理解这种警觉(对弱者而言,这总比轻信要好),但从群体政治的视角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性权利》一书着重强调,“性是一件冒充天然的文化造物”,它看似天生决定着我们的身份角色和感受(谁给予,谁索要,谁要求,谁服务,谁渴望,谁被渴望,谁获益,谁受损),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既非不可改变,更非无法超越。
女性其实也深知这一点,尤其是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往往一方面断言男性不可能“真正理解”女性,另一面又痛恨某些女性认同男权文化。当你相信只存在性别划分的两大对立阵营,对方阵营不可能转化,而己方阵营则总有人倒戈,那就很陷入一种自我孤立、自我强化,进而不断自我净化的境地。
在社会实践中,争取权利的博弈几乎总是在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域中展开的,没有那么非黑即白。现代社会默认社会成员由善意的陌生人组成,其顺利运作也未必需要“真正理解”——要指望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但哪怕是做到一部分,也是好的,关键是争取一切可能的支持。
我当然理解,“男性永远没办法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这样的话,与其说是一种斗争策略,不如说是表达一种失望、一种控诉;然而,这不应该是一个让自我陷入无力、无助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这是当下的现实,那正需要我们去做点什么,改变这一现实——比如,那些生了男孩的妈妈,就不能“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新的一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