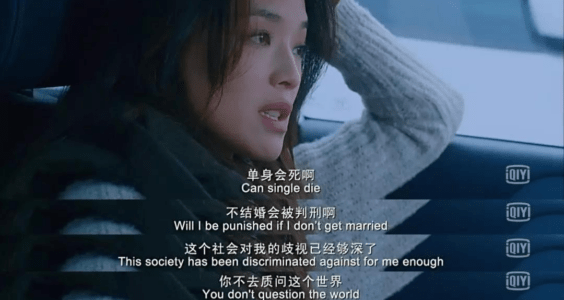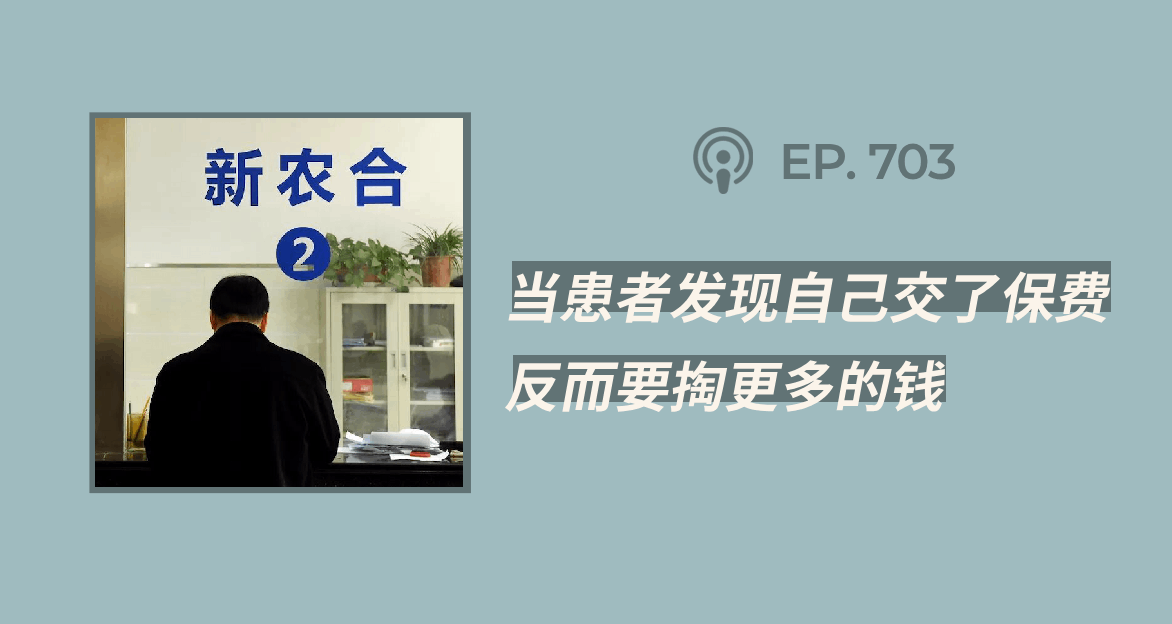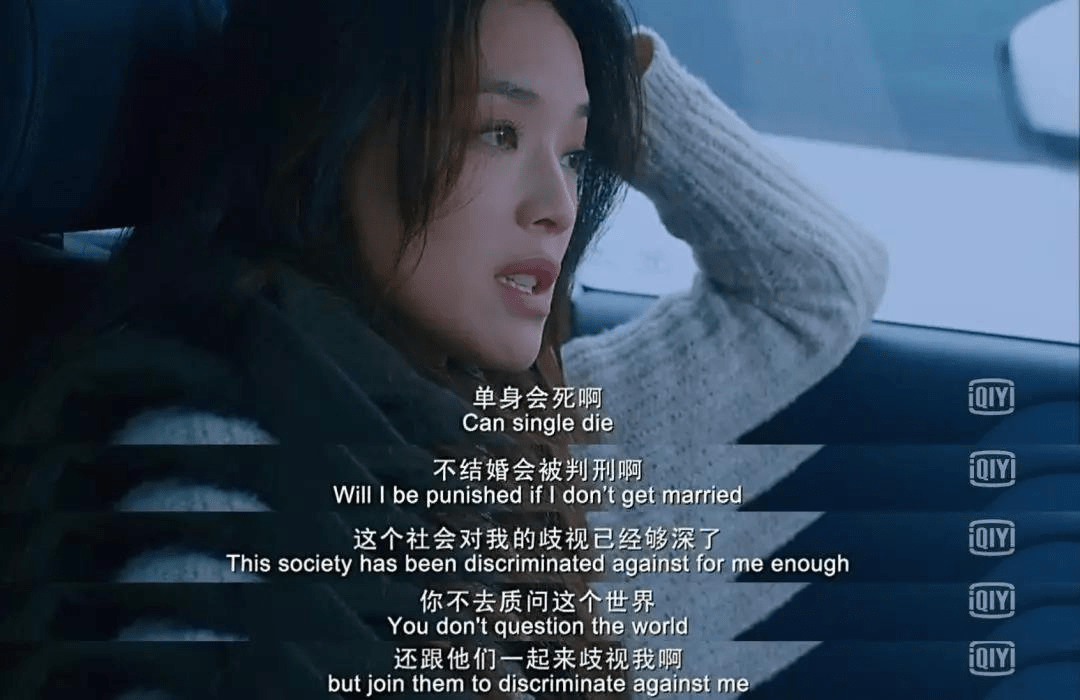
明眼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已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就没那么容易搞清楚了。
当然,你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点:人少了,无论是劳动力还是消费者都随之变少,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城市还可以吸纳新的劳动力,但大量村庄将逐步衰败乃至消失;少子化还会导致抚养比失衡,年轻一代需要供养大量老人;与此同时,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偏高,也会使整个社会丧失活力,偏向保守化……
但这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
确实,低生育率危机有点像气候变化:虽然它最终会影响到每个人,但其后果是温水煮青蛙式逐步显现的,责任也极为分散,以至于很少人会有什么紧迫感去做点什么。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那些宏大的变动更是遥远,毕竟单单是自己活好就已经够累的了。如果你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生活好歹简单多了,怎么都行,“不婚不育”至少会让减轻你不少负担——如果你是女性,那就更是了。
上一代人不论如何独立、叛逆,默认的还是“婚总是要结的,结了婚,孩子总是要生的”,然而现在,一旦你下定决心不婚不育(这也是年轻人为数不多能自主决定的事),实际上谁都拿你没办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社会应对这一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问题”的话)的主要方式,一是惩罚,二是恐吓。
人口学家们试图解决低生育率的建议(征收单身税等等),多是前者;而家长则多采用后者,渲染孤独老死的可怕——然而,就算是那样,对一些人来说,那也不如草率结合带来的痛苦婚姻、婚后带娃的劳苦来得迫在眉睫,甚至也不见得更苦。
家长原先的说教失效,这远不是“年轻人没有责任心、不能吃苦”这么简单,而是时代精神变迁的征兆,是一种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决裂。
因为儒家社会的生殖崇拜,从根本上说其实根植于永生的渴望——谁都会死,但只要血脉延续下去,自己的一部分就仍然在后代身上活着,本人也在祭祀中一直活在后人的记忆中。
中国文化之所以那么强调孝道,原因也在这里:“孝”即“肖”,意味着每一代人最好精确地复刻父辈的所思所想、行为举止,也就是说,中国人理解的“永生”与其说着重个体的“不死”,不如说是强调生生不息的“延续”,真正实现永生的其实是宗族。
正如历史学家岸本美绪所言,根据这种信念,“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旨在“冲决罗网”,将个体从家族网络中解救出来,然而那不论如何,毕竟是着眼于瓦解那种束缚个人行动自由的小共同体,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外部制约力量,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那种“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信念,最终只不过是把“大家族”变成了更为原子化的“小家庭”,最终还让脱嵌出来的个体重新“再嵌入”组织化的单位制度中。
然而,如今“最后一代”的宣言则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意味着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一种呼声,抛下了永生渴望,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将血脉的延续视为个体活着的最重要使命了,相反,他们将精力聚焦于个人在短短一生中的生活质量。
这种社会心态的变动,最鲜明地体现在这么一点上:95后对生死看得十分淡漠,乃至根本不关心自己死后骨灰被如何处置,拿这随意开玩笑——当然,你可以说那仅仅是玩笑,但这玩笑竟然得到那么多人赞成,这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吗?
老想着去纠正年轻人的“错误观念”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从新的价值观来看,那恰恰没有错——社会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型”,要再回到老路上去,按旧模式引领人们的行为是不可能了。
前些年,历史学者葛剑雄也曾不止一次谈到少子化的问题,他考察古今中外,结论是唯有重新提倡“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被人嗤笑是开倒车的复古想法,但我想他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建议,是因为实在没什么现成的出路:对那些不想生的人,各国都束手无策,而乐于多生养的,确实常是出于强烈的文化信念(例如犹太教的正统派)。
对现代人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已经不是种群的生物繁衍这种低等的本能欲望,而是“自我实现”,那是他们在放弃了“永生”的愿望之后,在现世的终极追求,一种更高级的自我繁殖欲望。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就是这一意义上对创造的超越。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极好地道出了这种内在超越:
荷马笔下的英雄认为他们的目标不是不朽的生命,而是创造一个关于卓越、英勇事迹或者作品的不朽记录。荷马笔下英雄想象的合理目标并不是永生的生命,而是对永久流传的卓越事迹、作品的创造。通过这些,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变成了以后的样子。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指出,这种类型的超越是“有生命者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特征,一切生物有了它才有了生命”。
也就是说,在这种信念下,人类寻求生存下去的冲动,是“在世界上留下他们自己的某些表达,他们特性的某种延续”,那恰是在他们意识到自己不会永生之后,放弃了对外在超越的渴望之后,才会追求这种内在的超越。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下的低生育率既是危机,也是社会转型的契机,恰恰表明越来越多人已经想清楚,放弃了血脉延续意义上的永生,转而追求在人生中尽可能活出自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一个良好的社会,理应当助力人们去实现这种现世的良好生活,让人们活得有意义。
不论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给新一代(尤其女性)赋权,切实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让养育孩子不再成为一件个体(往往是一个家庭里的最弱势者)无偿承受的苦差事,而享受真正的快乐。不仅如此,还应真正尊重每个个体,去除那些压抑个体潜力发挥的不合理障碍。这并不仅仅是“多生孩子”的简单任务,而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天真的理想,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