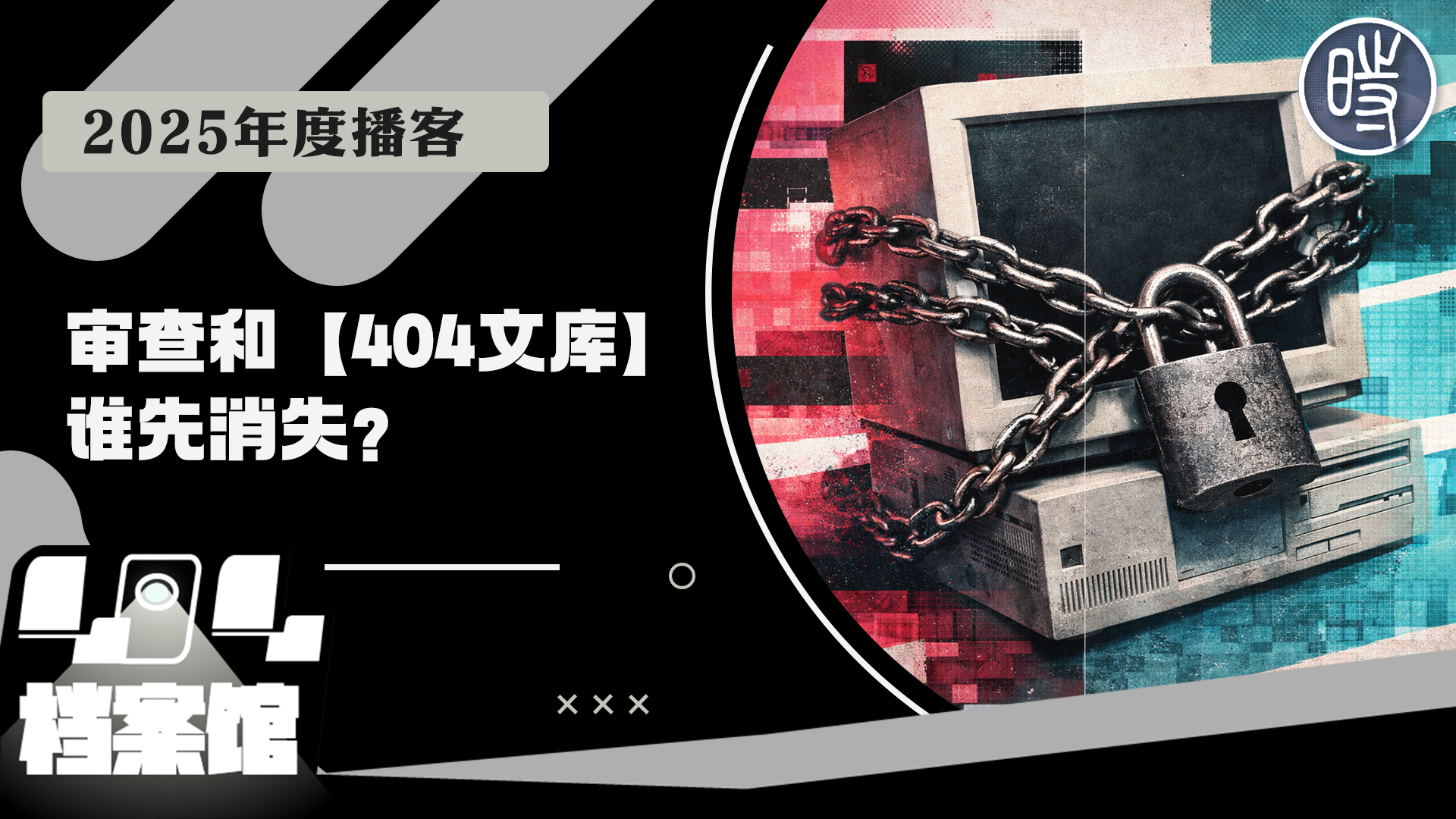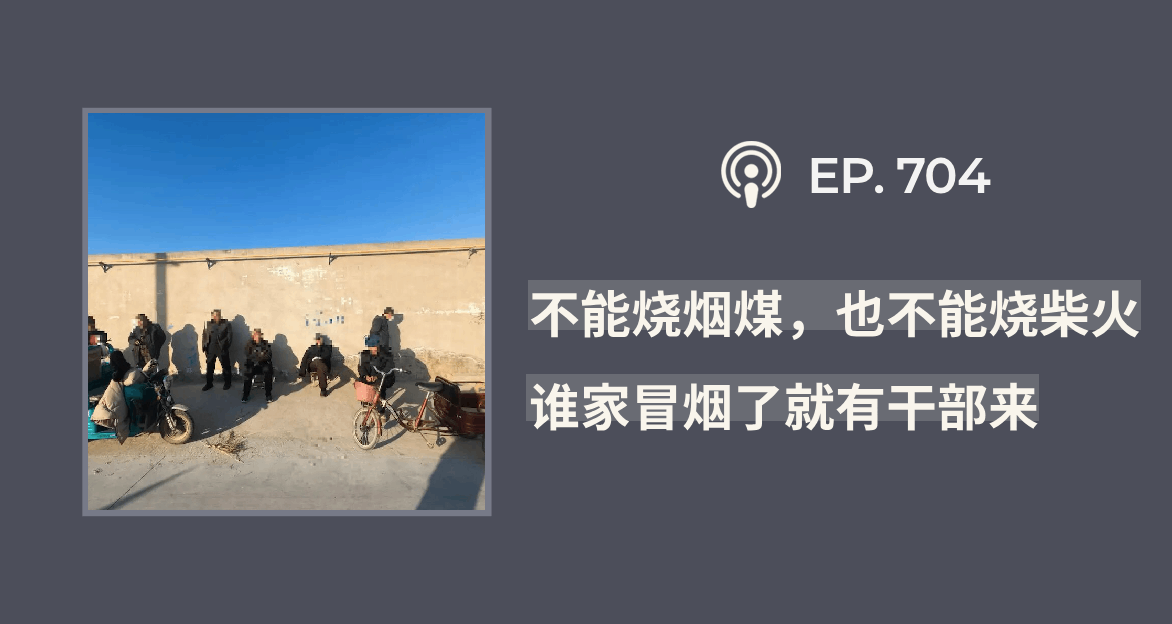在河北省三河市,领导觉得大街小巷的商户招牌,红、蓝、黑三色太难看,遂发出一个非正式命令,勒令所有店铺门匾都改色,全都换成绿的。
连医院的红十字标识,也被刷成绿色。于是三河市区整体变得绿油油的。
这几天忙于琐务,对这事没来得及评说几句。本以为这波舆情,也就热闹个一两天,不料事件持续发酵。
三河招牌“绿灾”,在舆论场上招致普遍的不满和批评。
权力任性,形式主义,治理异化,劳民伤财,胡乱折腾,这些指向都没错,批评得都很有道理。
但上述性质的其他一些公共事件,若论伤害烈度、关联程度,都比三河招牌“绿灾”要高,现有的批评话语叙事,似乎尚不足于解释公众对此事的负向反应情绪。
或者说,就三河招牌“绿灾”事件,已有的舆论批判和公共讨论,尚未触及公众深层化、弥散性的某种隐忧,达至更为深切的认知共情。
那么,就很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对于三河招牌“绿灾”,公众在意的到底是什么?
之所以称三河招牌颜色之变为“绿灾”,是因为城市沦为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权力美学恣意泛滥的实验场。
历史上没有什么美学趣味,比权力美学更崇尚整齐划一。
在一个官本位传统深厚的特定场域中,权力美学总是要运用无所不能的权力,将自己的意志和旨趣任意挥洒于每一个角落。
三河市街面成为一片“绿海”,使得个体的特征湮没于整齐的色调中。这种千篇一律的整齐而宏大的美,抽空了人文和个性,放逐了权利和法治,让人觉得丑而不是美。
毕竟从自然性(生物性)根基来看,大量研究表明各种动物——从鸟类到陆上爬行动物到深海鱼类,都有某些审美化趋向——况乎人哉。
正如启蒙学者假设的人有天生的自由权利,我们也可以假设人都有审美的需求和权利。
三河无所不在的“人工绿”,作为一种低劣的审美趣味,堂而皇之、理不直而气却壮地在城市空间亮相。
作为一种具有侵犯性的元素,“人造绿”是一种包围着三河市区民众的“环境”。它几乎无处不在,所有人避无可避,退无可退,逃无可逃,形成一种审美暴力、审美侵害。
这种由权力亲自导演的视觉盛宴和宏大景观,其负面的审美对人的伤害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真实、深切和长久的。
从短时间看,剥夺人的审美需求,不如剥夺粮食和饮水那么致命。但从人身心的健全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这种深层次需求来看,这种审美剥夺的后果同样是严重的。
被剥夺了审美机会和审美权利的人群,某些境界他们永远无法达到,失去了进入某些高层次生命境界的权利。
三河招牌“绿灾”,戕害审美感官,凌辱审美知觉,降低审美趣味,不是把人往席勒所言的朝上拉升,而是向下拽扯。
然而,这种由统一色调所构建的宏大绿色场景,体现着权力意志的视觉规训;权力美学隐含的政治叙事,汹涌占据着当地民众的视野,这无疑能极大地满足权力所需要的秩序和虚荣。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个人空间越来越被公共空间整齐划一的话语体系、环境体系所填满、侵占,个体日益成为被权力拆解的零件和碎片。
过去,一场政治运动就可以把百姓的审美需求剥夺殆尽,乃至于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等等具体琐碎的生活细节,都有明确的规定。
对于那些穿件花衣服、烫个头发什么的,便可以冠以“生活作风问题”的罪名,轻则进“学习班” ,重则游斗、收监。
如今,这种荒诞的政治性审美剥夺已不存在,但某些实际的审美剥夺仍然在发生,比如三河“绿灾”。
公众对三河“绿灾”的不满和批评,实质是对权力美学肆意泛滥的警惕和拒斥。
(题图来源于网络,由人工生成,并非实景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