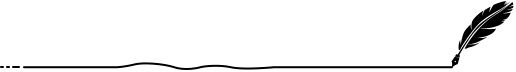一个关于“创伤性怠惰”的故事
1912年3月5日,辛亥革命的硝烟刚刚散去,清帝刚刚下了退位诏书。孙中山先生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著名的《剪辫令》。这纸命令里直言:“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
简单的说,就是留辫子本来就是清廷强加给百姓的规矩,现在清帝都退位了,国家也要走向文明开化了,留一条既丑陋又不方便打理还不与世界接轨的辫子有何用呢?大家赶紧剪了吧!
按理说,这纸命令无论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非常正当的,孙中山先生可能也认为此令一下,不等他的“临时大总统”任期结束,全国百姓都会立刻积极响应,剪辫之潮席卷全国。
所以政府的用词也特别乐观——“允宜”,不是强制的,而是允许并鼓励大家,把辫子剪了,能不蓄辫尽量不蓄辫。
可是孙中山想错了,从法令颁布的1912年开始,直到1914年一战都快爆发了,中国很多地方的百姓对剪辫子都持观望的态度,以至于一战中赴法劳动的华工群体中,仍有大批人没有剪除辫子,闹得民国政府为了“国际观瞻”起见,不得不在华工上船之前在码头现设一案,给未剪辫子者挨个剪辫子,才让他们远渡重洋。
乐观、温和的“允宜”,终于还是变成了“必须”。
其实,你去观察民初留下来的很多剪辫子照片,也会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很多被剪辫子者,似乎都不那么乐意,甚至需要被强按着才能剪。
像这位,一只手被制住,辫子都剪了,还想抓住不放呢……
也就是说,一度,留辫子是民众自发的,而剪辫子反而成了官方强制的。
甚至民间为了防止官府给他们强行剪辫子,也发明了一些“防剪小窍门”——一些人为了避免被剪掉辫子,坚持让妻子出门买东西、办事;还有一些人干脆把辫子盘在头顶,然后戴一顶帽子遮住,导致民初很多制帽场生意都特别好,专门产那种内部容量特别大的帽子。
而如果你看过鲁迅的《阿Q正传》,你会对未庄里的人为了保他们的辫子而不敢去县城办事情景印象深刻。
但鲁迅先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风气比较开化的江南,对当时中国民间自发的抗剪辫风潮的烈度还是描述不足。
当时在北方一些地区,比如山东,民国政府派出的“义务剪辫队”在深入乡里后甚至会遭到乡民的围堵,甚至一度闹出过激动的乡民为保辫子打死城里派来的工作人员的事情。
这就奇怪了,明明辫子是当年清廷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强行让汉地百姓给蓄上的,怎么如今大清都亡了,政府要求大家剪辫子,反而汉地民间有这么多百姓自发的死活不剪呢?
过去的很多论者,会将这种自发蓄辫的行为解释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认为当时的人们觉得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代表了某种文化,所以剪不得。
这种解释其实似是而非,因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先有文化,像王国维那样饱读一辈子诗书而自居“大清移民”,亦或者像辜鸿铭那样,洋墨水喝多了,产生排异反应,反过头来梗着脖子硬说中国人蓄辫、缠足、纳妾都大大的好……
说实话,与同时代真正的国学大家相比,半路出家的辜鸿铭虽然留着辫子,但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其实相当之粗疏。
他们这些人坚持蓄辫子,确实是“文化保守主义”,是文化多的有点糊涂了才干的事儿。
但清末民初坚持蓄辫的主力军,其实不是这些人,像为防剪辫子不敢进县城的阿Q,以及“义务剪辫队”下乡来宁可把人打死也要保自己辫子的愚昧乡民……
这帮底层百姓,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他们对辫子的“文化认同”就算存在,究竟能有多少呢?
所以,民初中国社会底层普遍存在的那股“抗剪辫”风潮,其实来自于另外一种动机——那是一种小民在底层社会倾轧中不得不养成的“精致”与无奈。以及一个民族在被过度驯服后养成“创伤性怠惰”。
有一个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冷知识——近代中国最早的剪辫风潮,其实不是孙中山或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后才开始的,而是晚清政府自己力倡的。只不过清政府没有“违拗”的过“保辫”的民意而已。
庚子国变之后,清朝开始正经编练新式陆军,当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西式军装头戴大盖帽、身穿制式军服、身后还要背一个硕大的行军囊,让士兵留条辫子,真的是放在哪里都不舒服、不合适,更不方便打理。于是一些满人勋贵就开始零星上书建言,要求在新军中剪辫子。
比如1904年起,以旗军改制而来、以满人为绝对主力的禁卫军,就开始尝试剪辫子,到了1910年时,已经成为了中国第一支“无辫军”。
到了1905年,清廷为了“预备立宪”,五大臣分赴欧美日本等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宪政考察的咋样另说,但载泽、端方等满人亲贵此行受到的最大触动就是“要剪辫子”。
在一帮衣着现代的西洋人里面,自己留着条大辫子行走其中,时刻感觉到后面有人掩面而笑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所以五大臣留洋团队走到一半,四十余名随员中就“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这些擅自剪辫者,还是回国后向慈禧老佛爷力陈蓄辫之害的人,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旗人(包括满军旗、蒙军旗和汉军旗)。
也就是说他们是清廷统治集团的自家人。而汉人大臣,像戴鸿慈、徐世昌这帮人人,要么不说话,要么还要在载泽、端方等人高喊剪辫子的时候泼泼冷水。
其实徐世昌等汉臣们的持这种态度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毕竟是的“外人”,旗人提剪辫子口号,那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汉臣如果也跟着喊,立刻就成了立场问题、忠心问题。所以在慈禧太后没有亮明对此问题的态度前,他们根本不敢参与这个话题的探讨,甚至必须成为“保辫派”。
而慈禧太后作为深谙统御之道的权术老手,就是不亮这个态度,每有所奏,“皇太后但笑而不言”。
于是剪辫子这个话题,就在这种其实没有多少真正反对者的情况下,愣是拖了下来。
1908年,慈禧和光绪都驾崩了,摄政王载沣重用满族亲贵,搞了一个“皇族内阁”上台,虽然被世人所诟病。但有一件事情随着汉人大臣的退场却出人意料的达成了一致——剪辫子!
在朝廷“上意已明”的情况下,各省咨议局相继达成共识,纷纷上书情愿、要求全国尽快剪辫子。
于是1910年,大清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时,就通过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与《剪除辫发改良礼服》两个议案。明确要求大清臣民剪除辫子。
议案一下,很多留过洋的年轻满族亲贵,立刻忙不迭的就把辫子给剪了。
但那个之后困扰民国政府问题,此时就出现了——大多数人,嘴上答应着,但就是不动手。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人们搞不清楚这个命令到底是要动真格的呢?还仅仅是一次“欲擒故纵”的忠诚度测试。对于小民来讲,万一你听了这个命令,动手把辫子剪了,明天朝廷再下个什么什么令,说“跟你客气一下你居然还真剪啊?都抓起来!”那怎么办呢?
所以非常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议案下发到地方,居然还出现一些人上书,指天画地的保证自己忠于大清,辫子绝对不会剪的奇景。
转过年来,1911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第二年清帝都退位了,这个忠诚度测试的问题看似解决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再次下令剪辫子也是这个意思——清朝都没了,你们还留辫子给谁看?赶紧剪了吧!
可是孙中山先生没有站在很多地方的升斗小民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清政府虽然没了,但一些坚持按着之前老规矩来的地方势力还在。比如当时的山东地区,“保辫运动”之所以闹得最凶,真不是当地民众保守,而是当地人知道一个事实——北洋军的“辫帅”张勋所部,当时就驻扎在兖州。
张勋这个人,说来也很有意思。
清廷当年尝试部分放开,允许军队剪辫子的时候,他就公然“抗旨”,表示自己的部队永远不会剪辫子:行军打仗留辫子不方便?不方便我们可以克服、忍耐么。反正辫子是一定不会剪的!这是我对朝廷、对大帅的一片忠心!
颇为微妙的是,对于张勋这个“抗旨不尊”的态度,无论朝廷还是其顶头上司袁世凯,虽然面上不置可否,但心里其实鼓励的——因为剪辫子这主张毕竟最早是革命党提的,即便是后来朝廷允许了,总还是怀疑响应过于积极的人是不是有里通革命党的嫌疑。现在有张勋这么一个人,愿意自己为自己的辫子负责,那当然其上司们都安心……甚至开心。
于是张勋的“辫子军”就这么从清末保留了下来,又留到了民初。在其势力范围下的老百姓那当然是不敢乱剪辫子的,因为那年头正好是兵荒马乱的时节,北洋军官兵常有找茬欺压驻地乡里的事情。万一你把辫子剪了,那么那些辫子军的军爷一定会借此拿上了搪——你怎么把辫子剪了呢?罚你款!抄你家!
你说,碰上这种人,堂堂民国参议院都没辙,你个平民百姓能到哪儿能说理去?
而非常黑色幽默的是,张勋这支辫子军后来还真就“搞了个大新闻”。
1917年,利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争权矛盾,辫军张大帅来了个“一鞭直渡清河洛”——亲率五千辫子兵北上京师,重立废帝溥仪登基坐殿,复辟了“我大清”。
而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这场闹剧虽然只持续了11天。但京城还真的里突然冒出来很多留长辫子的人,溥仪自己都嘲笑说:“一个个像从棺材里蹦出来似的”。
而等到张勋复辟一倒台,京城满大街又到处都是散落的假辫子。
可以想见,至少在这十一天里,那些坚持把辫子留下来的人,会有一种阿Q版的精神胜利感:怎么样,幸亏我把辫子留下来了吧,这又用得着了!
是的,这就是人心,是长期被“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威权所恫吓、所驯服、所吓破了胆的人,在看不清未来的乱局中,所必然作出的胆怯选择。
你说它是可悲的奴性也好、是无奈的精明也罢,但这里面,真的没有半分“文化保守主义”的大义在其中。
这是一种“创伤性怠惰”,“祖宗”通过辫子给这些人留下来的,其实只有胆怯而已。
剪辫子之争的最终解决,说颇有戏剧性,且非常简单。
自1913年以后,认识到剪辫在民间推广困难性的民国政府,就一直尝试给溥仪去函,劝说这位逊位的皇帝自己把辫子剪了。
但可能是因为溥仪当时还小,自己没有判断力,这些信都被近臣内侍拦下来,泥牛入海了无音讯了。非但如此,被汉人太监把持的清廷内务府,为表对大清的耿耿忠心,还搞了一个“准入制度”,任何人想进紫禁城见皇上,都必须检查有无辫子,无辫子者不让进。
可是随着溥仪的长大,他终于看到了这些信件。溥仪就问了他最喜欢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一个载泽当年访问美国时曾经问过的问题:“你们到底怎么看我们留辫子?”
庄士敦略做思考后,给了一个和当年老罗斯福总统回答载泽时几乎如出一辙的答案:“你们的发辫在我们看来是落后的象征,西方人一直嘲笑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您最好将它剪掉。”
溥仪听到这话之后,立刻就吩咐拿来剪刀,让太监把自己的辫子剪了。
孰料,那位亲信太监听到皇上这么吩咐立马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口称“万死”“不敢”。
这其实也是自然的,即便是亲信太监与皇上之间的,也存在一个无法破除的“猜疑链”,太监怎么会知道皇上这个命令是不是在考验他对自己的忠心呢?
于是溥仪只能叹了一口气,把辫子绕到身前,自己拿起剪子咔嚓一刀把辫子剪了。
翌日,上海《申报》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简单六个字:“溥仪昨剃辫子!”
然后,全国一片嘁哩喀嚓、那最后一批留辫子的人,终于都把辫子给剪了。
理由也无他,只是因为附加在这个劳什子上最后的那一丝“忠诚宣誓”意味,终于也消失了。
只是,这一年已经是1922年了,距今刚好一百年整。
离清政府默许新军、警察剪辫子,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离民国政府下令“限期剪除辫子”也居然过去了10年。
无论当年的倡议者,还是反对者,可能都不会想到,这看似最最简单的咔嚓一刀,居然在争论平息、政府命令的情况下,还需要延续这么久,花这么多的强制力,才能最终剪下去。
这,就是剪辫子的故事,
一个创伤性怠惰的故事,
一个族群被过度驯服后,重启革新之难、革新之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