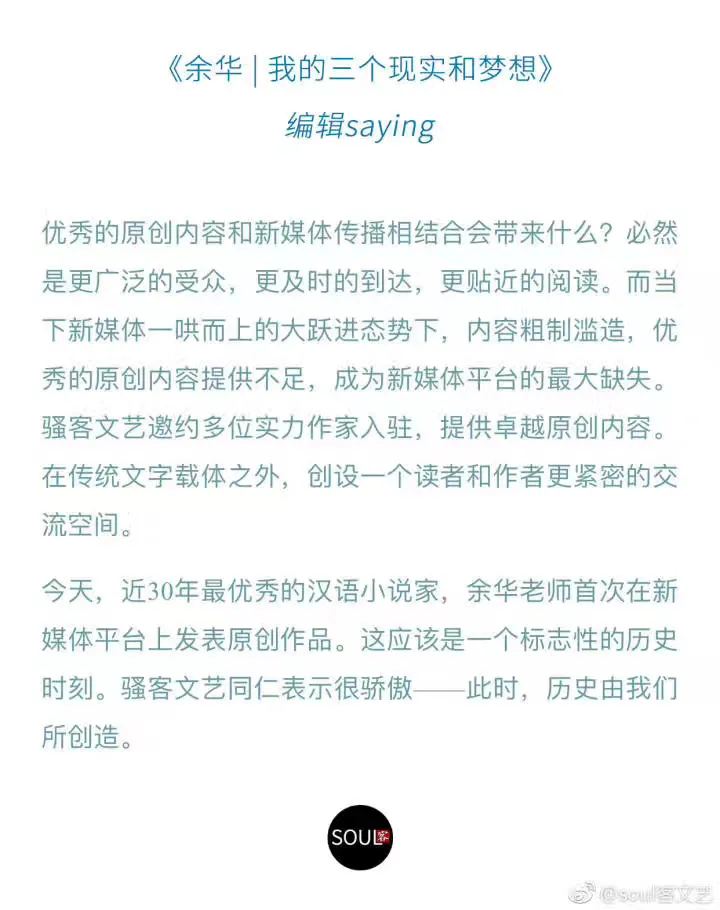01
父亲最近给我留言:“要静心耐心等待,老妈血压正常,我上次输液,居然治好了脚上的皮肤和趾丫的溃烂。这叫做意外的收获。另外,我松动的牙自动脱落了,没去麻药,更没流血。老爸想你,也担心你。”
最近一次见他,是今年四月份在成都,我们一起过了一个迟到的2020年春节。两年不见,父亲还是红光满面,但每次下楼梯,母亲都要紧紧搀扶着他,生怕他脆弱的膝盖承受不了。而且,一说话我才发现,他下面那排牙齿都掉了,仿佛半边黑洞,看得我心里一阵颤悠。
最近,时不时的,有心的读者就会在后台问一声:“为什么现在更新得这么少了?”
想了想,这两件看似不相关的事,得用一篇文章来回答一下,也当是个提前的告别吧。
到今年的6月8日,骚客文艺成立已四周年。胡兰成当初写《民国女子》,说张爱玲让他有“看见自己尸身的惊”。这四年,那么多的作者,那么多的文字,虽不是字字珠玑,亦曾让我有过“头盖骨被轰开”重新见识世界的惊。
昨天,我还在朋友圈说:“士大夫之所以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总还是要承担一些‘引领’大众的责任,如果连起码的自省都没有,也不能对文字有多于大众的敬畏,那就会让不知道哪里来的魑魅魍魉毁掉美好的文字世界。”
去年下半年,我把骚客文艺的简介修改成了“精英引领的阅读”。
四年多以来,我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尽量推送了一些与读者互相尊重、沟通,启蒙多于讨好、启发多于煽动的文章。
但是,从世俗意义上来说,我无疑是失败的。我们的所谓A+轮的投资人还有很小一部分的钱没有进来,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账上余额所剩无几,囊中羞涩,人也就难免更羞涩起来。
大厦将倾,落下来的不是灰,而是巨石砸在身上,区别只在早晚。
凑巧的是我背部筋膜炎又犯了,手也因为烫伤而感染,各种不适迭加,身心俱疲,感觉自己一下成为了一个手不能提、口无法开的“废人”。
我想,这一切也许都在暗示我,是时候告别了,是时候告别我不擅长的事情,也是时候回家去陪伴一下父母了。
02
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关于自媒体的所有经营方式,收入最高的那些,还是靠广告,至于其他方式,我也都试过了,连文化基金支持,我们也鼓起勇气申请过了。
大概做生意这种事,必然需要一点“时运”的:每当我竭尽全力,把骚客文艺做到影响力增大,广告商纷至沓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莫名其妙又触及到了那根看不见的红线……
当然还是忍不住感慨一句,想当年和@七个作家 同时出道,且同时做到同等程度的公号,现在活着的,都变成了大号。
除此之外,赚钱也确实需要某些天赋,比如,把自己彻底放低,但骚客文艺从来没有接过类似p2p、医美、中医药、面膜等广告,因为不懂,怕出卖了读者的信任。
不合时宜的,还有我内心深处那点可怕得很的“清高”。某次,有人让我帮忙找位知名作家策划一个活动,大概我和那位长者八字不合,接触了几次他都各种拒绝推脱。如果为了采访,我可以赔上耐心,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很容易就觉得,去你的吧,我也不欠你的,老子不伺候。
所以,说来说去,都是我这个CEO的问题,需要检讨的地方太多,在商业这条路上,宛若白痴。
总有人问,你们怎么不多接点广告?我认识一个也是从媒体出来的创业者,他的项目虽然动静不大,但他早年采访过的几位商业大佬一直在无条件支持他;还有另外一位做销售的前同事,虽然对内容完全不懂,却凭借早年积攒下来客户,东墙赚了补西墙……
这些都是我的弱项。
早在2019年,我们的天使投资就花光了,一个伟大的朋友如英雄般出现,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即使他现在还有很小一部分资金没有到位,他也已经是骚客文艺的天使了。
但我们既然没有那种世俗的造血功能,再多的天使,也徒唤奈何。
其实不管是之前给王五四写的那篇人物,还是《商人野哥》的推广,效果都还挺不错的。但我们也并不是那种篇篇10万加,很会鸡汤很会营造情绪的公号。
说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几乎每一次开选题会,或者编辑稿件,都在尽力避免煽动、煽情,都希望把自己放在一个和读者平视的位置,互相尊重,但事实上,有那么一部分流量号,很容易接到广告的公号,恰恰是不用判断合不合适、怎么煽情怎么来那种。
我不行,DNA决定,就算做一个鸟人,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03
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在那样的末世,并没有哀怨,而是置一壶热酒膝前,火热的温度也就从天地之间蹿上心头,万物从未如此清楚地呈现在你的心里。
四年来,我作为一个创业者,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是李华吊古战场的那种“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的肃杀。
当一个人孤独到极致的时候,能看到的却不是这样的澄澈,而是万物的幻灭。当然张岱并不是彻底的隐者,一个真正的好时代,应该让一个“士”既能保持出世的孤独,也能偶尔享受鲜衣怒马、烈火烹油的生活。
最近和连清川老师聊天,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得出一句颇为唏嘘的结论:我们只想过上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而已。
前两天,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对上海夫妻算了算一家五口在上海每月的花费,大概需要五万左右才能维持小康……如果再苦苦维持骚客文艺,我原本平凡的生活,只能变得越来越不体面。
04
最后,必须感谢无数的作家朋友,为骚客文艺提供了上千篇好文章;必须感谢曾经担任过骚客文艺主编的董啸,兼职主编的余少镭、张丰、身中一刀、燕之敖,担任过搜历史主编的曲飞(编辑大梁如姬),尤其要感谢从@七个作家 开始就陪伴我至今的编辑小窗。
今天早上突然惊醒,犹豫着是不是还需要再跟跟最近大热的那些社会话题,但说实话,心里已经有说不出来的厌倦感。
骚客文艺的老读者都会发现我们风格的转换,从早期的纯文学,到后期的社会热点。因为每一个人都夸赞着文字的美好,却在美丽的标题面前犹豫着要不要点开。
可以这么说,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自媒体,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流量裹挟。
而我受够了做一个雪村老师所说的“吃蜻蜓的人”(明明知道食物没有营养还要勉强咽下去),我只能说我也曾尽全力,在流量的泥沙中稍微保持一点独立的姿态。
前几个月,天使投资人之一来到我们的办公室,说到最糟糕时候他也得上天台,我们不禁黯然。
我不知道该回他什么,因为他说:“发现所有投给你们这些文人的项目,都没有一个成功的。”
他大概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投资人应该说的狠话,一直以来,他们真的足够宽容了,再次叩谢各位投资人。
说话间,他撞倒了书架上的一本书,书一跃而下,又砸倒了一盒不知谁放在那里的、更加无辜的藿香正气液,玉碎瓦不全,药液洒到哪哪都是。
那不是想你的夜,而是现实面前头破血流的日日夜夜。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所有的“正气”,最后都会液化,不成流量,便被蒸发。
多年以后,我大概会写上这么一句:“失败是有味道的,那是藿香正气液的味道。”
绍圣四年,被贬到惠州的苏东坡已经失去了王夫人和心爱的小妾朝云,他把自己投入到俗世生活之中,种地、酿酒,和陶诗,并花尽积蓄在惠州筑屋,打算终老于此。然而,他很快就又收到了追贬至琼州的诏令……由惠州而雷州而儋州的苏东坡已经62岁了,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天涯海角,远无更远了。
人生如果一直穷困潦倒,或者静静无为模式,反而容易安然度过,而像苏东坡这般,年仅22岁就名满天下,在异常艰难的制科考试中名列三等(宋朝开国以来“制举”对策考试的最高名次)的成绩,那个时候他的面前是一条由鲜花和艳羡铺就的康庄大道,丞相的位置仿佛只有一步之遥。
人生的高光时刻之后,却是天才和勤奋、努力与付出都不能主宰的诡异命运,颠沛流离、穷途徘徊,萧索、孤独、惆怅与叹息,这些晦暗的词语很快充斥着他的一生。
一身是病,形单影只,又是在一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天涯海角,恐怕他自己也觉得路已经走到头了。但他的诗词文章却依旧豁达,竹杖芒鞋,任凭一蓑烟雨。
最近这几个月,一直都在探索苏东坡的内心世界,有时候在黑夜里,我试图设身处地,进入那个纷乱复杂的年代,不知不觉,模模糊糊,就会出现一个场景,那是《后赤壁赋》里面描绘过的陡峭的江岸,江水在脚下呜咽,岩石松动,天地之深,却无一人唱和。
我当然无法代入苏东坡,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进入到另一个人的孤独和痛苦,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即使是很少的程度,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句多么真切的表达。
05
父亲节的时候,我曾经写过父亲,“不争不抢,不随波逐流,永远有种少年人才有的天真的趣致,他学识丰富,待人赤诚,对生活永远充满热爱,而且从不人云亦云,独立思考,不迂腐地抱着单一价值观,在这世上是我心目中知识分子的标杆”。
大概只有从这意义上来说,我并非是失败的吧。
最近这一周,托受伤的福,有时候能享受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想想自己的前半生。以前时有抱怨,觉得和同龄人相比,我是一个常常被遗忘在命运洼地的人:从小就被老师欺负被同学霸凌,在北京做过低端人口,失过无数次业,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找到一生值得托付的职业,却成了覆巢之下一颗支离破碎的蛋……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都那么喜欢创业吗?我们大概也只是求得一簞食一瓢饮之后,有张安静的书桌就足够了。
深夜两点的北京,那种“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的场景;凌晨两点的休斯敦,“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的空寂;还有上海的凌晨两点,一个人凝视着黑沉沉的深渊,紧紧抓住内心的峭壁,以免掉下去的那种黯然……我已体味太多。
是我还不够努力吗?这一年来,我也各种考虑把自己作为产品推到市场,想把之前在乐视的《荷体育》再接着做下去,想去承接一些我比较擅长的市场公关项目。甚至我也想过,把别人欠我的钱红着脸要回来,或是把我唯一的房子卖了……
但也许这是某种安排也不可知,就好像冥冥之中总有些什么东西要重重地压在我肩上,让我微小的生命不那么轻薄,不那么“起舞弄清影”,也就可以踏踏实实地住在人间烟火里了。
有人说,这种失败大概是“因清醒而被主流抛弃,在困顿中显示尊严”,我并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清高,只是在悬崖边上站久了,有点累,想按下暂停键,容我歇息一段时间,先暂时回家去种红薯去了。
再见了,泥沙俱下的舆论场;再见了我的读者,虽然四年以来的骚客文艺已经成为我的血和肉;再见了我的朋友们,我说的是再见而不是拜拜,只要文字不消失,我们总能在生命的某一段重逢。
(这不是最后一篇文章的分界线)
还是想说一句,这并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谢谢所有关注过我们、喜欢过我们的朋友,我也能记得每一声问候、喜爱,和转发。接下来还会发一些答应过朋友们的推广,才会慢慢离开。也许偶尔也还会在@荷谈阅色 信手写几笔,那也许会是一个更加任性的易小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