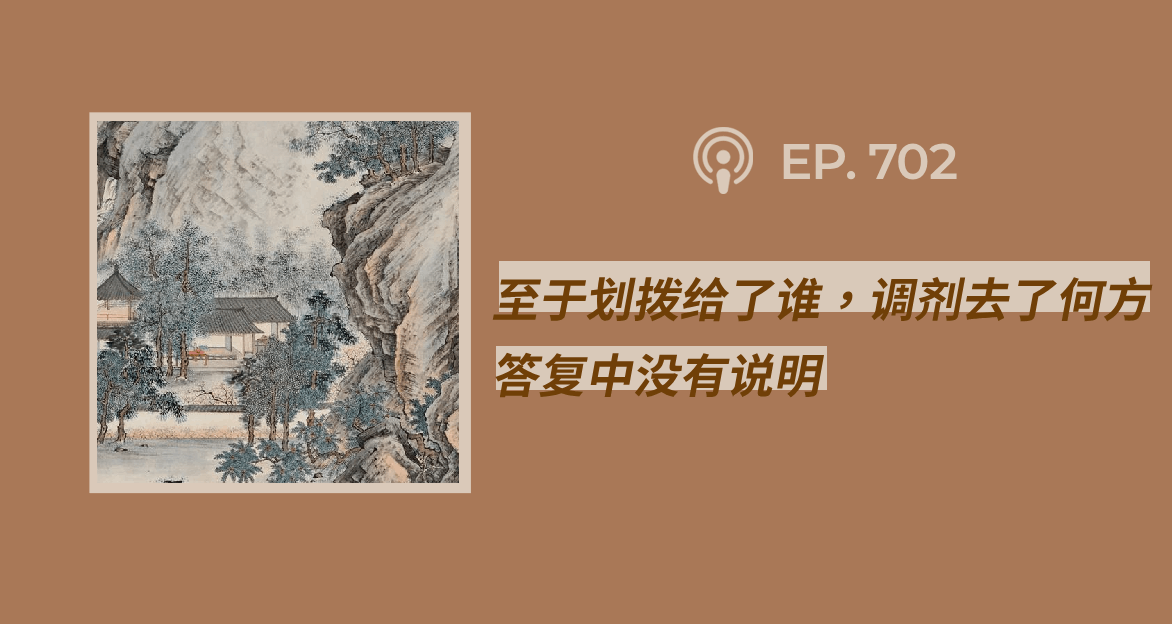彭晓芸 | 【伪理想主义】和【硬质疑】
怎样的质疑是合理质疑而不是有罪推断,更不是某些人危言耸听的什么“文革”,这一点,我希望有人愿意认真讨论,而不是趁机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场质疑,也无关什么偶像坍塌不坍塌,商业明星本来就是媒体和出版社制造,但是疯狂的粉丝则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中国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社会把严肃的公共问题寄托在明星身上,这点和成熟完善一点的社会,是相当地不同。在其他国家,也有商业明星,但是媒体和公众有能力区分什么是娱乐、插科打诨,什么是公共论辩,民主精神,什么是商业明星,什么是知识分子,他们在驾驭公共议题的时候,有能力把这种区隔领悟和运用得较好。 我为何讲“韩寒现象”是中国社会的“毒瘤”,在于中国扭曲的价值观和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任何一个领域,包括被包装得很动听的所谓理想主义,他们在兜售一种虚假繁荣,一种便捷而又不付出太多代价甚至获得超额利润的“伪理想主义”。 这会混淆公众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以为追求民主自由就是那么地轻便可人,闪闪发光,不需要经历困苦和煎熬,不需要经历挣扎和诚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就能把民主玩转了,这是极为危险的一种社会倾向了。因此,不能不说。 也是为了向那些真正付出代价、备受煎熬、有着真正的价值诉求的人们致敬,为了努力为公共舆论回到理性轨道做一点点努力。 目前为止,如果说我的“文学批评”属【软质疑】,那么,综合我此前微博陆续发过的和其他人的,总结一下【硬质疑】有哪几条(没想到的请补充): 1、新概念谁报名的? (父子说法不一致,这条至关重要,不是小问题,不是纠缠,而是关系韩寒的作家梦是如何被”引擎”的,父亲写书为何要刻意避嫌,说是韩寒想报名,家长正常的引导孩子本来不需要避讳。而韩寒对曹可凡面对面所讲,当是更为可信的,他说的是父亲帮他投的,这甚至可能推论到父亲有无自作主张拿自己的文章替韩寒投稿,因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2、三重门的写作时间、地点 (父子说法不一致,详见方舟子文章: “天才”韩寒创作《三重门》之谜:http://t.cn/z0s4NTi) 3、新概念复试,关于考场出题,杯中究竟何物,出现了多种说法。 (这个也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有无徇私舞弊,关系韩寒的成名有无原罪,虽然我很讨厌使用原罪这个词,但是,假设成名是有潜规则成分,韩氏父子应当像青少年读者道歉,这是一种不好的公众人物示范) 4、初选投稿被高度疑似成年人作品不予入选,本来已经淘汰了,此后是如何重新准予复试的? 这个过程,也没有见到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央视对话节目,那位“发现”韩寒的编辑所讲,说是有多位知名作家帮韩寒说话,建议给一个复试机会,那么,这些评委作家们,是怎么想的?这个过程,是否符合大赛的比赛规程?这个破格是否在大赛的公平原则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5、关于韩三篇的写作时间,韩寒本人接受采访的说法与文章内容涉及题材的实际情况、三篇前的博客《问我》出现自相矛盾,如何解释? 6、关于《书店》两篇, 纯“文学批评”的,或可表示不回应,但写作背景的自述,应当能够证明是韩寒本人所思所想,才能排除这两篇高度疑似成年人作品嫌疑,当然,这个书面作答恐怕不可信。且越迟回应这些问题,越有时间去准备如何自圆其说。 7、关于韩寒作品中大量使用英文并且还有考据癖,喜欢去考证英文单词的词义,这点韩寒如何解释? 因为他多次多次地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英文非常不好,诸如香港书展的视频中,只要有英文单词出现,韩寒即抗拒,并且告知自己英文非常不好。如果有那样的求知精神,按照常理推断,不太可能没法对付那么简单的应试。这个裂变如何产生的?韩寒对此有说法吗? 8、植入式广告? 根据韩寒的《通稿2003》这本随笔集当中一篇题为《自己的问题》自述,他对自己的书的后记不知情,是交给编辑做的,而且,这本《通稿2003》的后记也不是韩寒本人写的,韩寒自述:“作者不详,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但是原文居然是XX音响的广告”(此处是我略去,因不想帮人打广告,但韩寒的原文有),接着,韩寒用了不少篇幅详尽介绍了他的赛车车型,也有一堆具体的广告,见链接。那么,我想问的是,韩寒对自己的作品是不是非常随意和不珍惜?并且经常丢给书商去“策划、营销”乃至“植入式广告”? 公众对此有何看法?因为我是从这次“代笔门”之后才发现,韩寒的商业意识如此之强烈,譬如配合出版社删除博客以出版,这样的行为虽然说不上严重的欺诈行为,但的确是将商业价值物尽其用到一个极致了! 商业意识不是罪,姑且不予深究,但是,韩寒极力否认团队说,又是为何?明明连后记都交给人处理,甚至不知情,这还不是团队吗?任何一个商业明星,都不可能孤军奋战的,又不是冥思的哲学家。这点本来很正常,但韩寒对麦田、方舟子的回应文章,显得过于撇清这点,反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7916_19755.html 9、网民补充: @ 吴小厨 :应该加上这条:在《三重门》里引用了杜甫、曹植的诗句,又引用了《西厢记》和《红楼梦》情节和内容,他应该很熟悉这两本名著。在2007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吴虹飞采访时的对话却是:“人物周刊:据说你没有看过《红楼梦》。韩寒:对。我四大名著都没看过。”